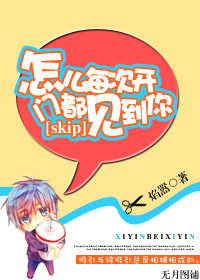琥珀的眼泪(大结局)-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女孩忙记起自己的职责:“我要的价已经很低了,你不要差太多哦!”
汤芙的脸憋得通红,羞耻心与占有欲打得热火朝天,终于冒着被对方扁死的决心报出底价:“我没有多少钱,回去还得坐车,八块行不?”忙又补上一句“我以后多多来买,把同学也领来。”这才有勇气看女孩气变形的脸。
不出所料女老板面容夸张地扭曲着,仿佛食人族吃人的前奏:“不行!你的价连本钱都不够。我知道学生没钱,这样吧,十五块,这是最低价了。”
汤芙一喜,暗叫有望!遂跨前一步再砍:“我加二块,十块钱,多一分我也拿不出了。”
“十二吧,你别再讲了。就这些车费都挣不出来。”
汤芙寻思了一会,跳过了“闪”招,直接耍赖道:“咱们都不让步,那就赌一赌吧。一拳定胜负。我赢了就十块;你赢就十二。”
女老板虽没有盘龙之癖,一时倒也想不出反驳的法子,一跺脚道:“好,就这么办!”
《琥珀的眼泪》二十一(2)
“一二三,出!”
汤芙以布包石头,喜得恨不能宣布自己是传说中的赌圣。抽出十元钱塞在她手里,安慰道:“今天算我运气!就占了您这点便宜啦。”
女孩倒也无话可说,暗骂自己道行不够,嘴里嘟嚷着:“这算什么事呢!”
汤芙晃着耳坠向门口走去,看着闪闪的戒指不由得浮想联翩。戒指不比别的手饰,得男人送的戴着才有味,她望着自己光秃秃的手指撇了撇嘴向校园走去。
《琥珀的眼泪》二十二
没同男人上过床的女人多半是纯为爱情而活着的,以为幻想着情人的脸便可以过一世;同男人上过床之后,女人的眼前便豁然开朗,原来爱情的乐趣不仅存在于爱情之中啊。便懂得了情到浓时归于性,更懂得了男人想女人的原动力在下面而不在上面。
对男人来说,他若得不到最想得到的女人他就有了玩弄其他女人的勇气。左搂右抱后也不忘故作悲痛地感叹命运不公;对女人来说,她若无法伴在最爱的男人身边她就会逃离其他
骚扰她的男人,顾影自怜后弄出个痨病,一命呜呼。当然这说的是还没活明白的保守的中国女人。在这一领域,外国女性堪为表率,代表首推十八世纪德国的布伏莱候爵夫人。自己生的快感生怕别人不知道,死后也要刻在墓碑上普天同乐:
在这深深地沉寂之下安息着,
这个虔心追求快感和欲望的女人,
为了使自己更加安全,
她把这个世界作为自己的天堂。
布伏莱候爵夫人是否如处天堂不得而知,倒勾得有心没胆的女人艳羡不已。
汤芙还没资格算成女人,充其量是个知道想男人的女孩儿,而且想得片面,根本猜不到男女关系包括精神和肉体二种,固执地认为白冰峰与白彦只是有机会多聊聊天罢了。而如今自己同他同桌而坐,不是比白彦更走运么!
她乐得心花怒放,眼见着自己的耳环够俏皮的了,只差衣装。穿什么才能俏上加俏呢?一低头见日历牌上的名言警句,念道:“女要俏,一身孝;男要俏,一身皂。”这“女要俏,一身孝”大概是说女的最俏丽的装扮莫过于一袭白衣;可下半句着实令人费解,只有洗澡后的男人才算俏,难道男人都脏到这个地步了么?汤芙摇头不解,乖乖地找出白裤,白毛衫。她是打定主意要俏上一俏。
来到教室,汤芙羞羞搭搭地挪到座位,见白冰峰端坐在身旁,正想甜甜一笑,李小丰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似地“喵”地一声叫开去:“我的天啊!都什么时代了还戴成这样!你也太老土了吧!”
汤芙的脑袋“嗡”地一热,手下意识地去捂耳朵,可张亦观的声音到底还是传了进来:“现在流行耳钉,偏你买个这么大的耳坠,I服了U了!”
“不过,”代西慈悲为怀道:“这也就是汤芙吧,换个人准得别扭死!”
汤芙被吓破了胆,把代西这句中性话也听成了贬义,恨不能把头埋进书堂里,两只手哆哆嗦嗦地去摘耳环,一种轻柔地好似天簌般的声音传入她的耳朵:“挺好看的。”
汤芙梦也似地扭过头去,是他么?是他在赞我么?挺好看的,是在说耳环,还是在说我?亦或两者都是?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巴巴地瞅着白冰峰的嘴唇,祈祷着仙乐再奏。白冰峰好似心灵解码器,轻轻地又道:“挺好看的,不用听她们的。”
汤芙嘴上淑女般地一笑,心里却仿佛开了个篝火晚会,一片通亮。恨不能说我谁的话也不听,就听你的。
代西为白彦呜不平:“你这么说话也不怕某个人心里犯酸!”
还没等白冰峰回嘴,犯酸的嫌疑犯白彦不打自招:“你别胡说八道,我哪有!”
“咦?”代西奇道;“我也没说你啊,某个人就是爱多想。”然后笑容可掬地欣赏白彦的脸由白萝卜转型为红萝卜。
白彦乖乖地闭了嘴,这么打嘴仗一点便宜也占不到,求救似地看着白冰峰。白冰峰硬着头皮上阵道;“少说两句行不行?谁也不会把你当哑巴。”
“哟!”李小丰奸笑道:“夫妻上阵啊,代西你还是聪明点儿吧,你有本事以一敌二么?”
这回轮到汤芙心里犯酸了。忿忿地想这不是胡诌么!哪里就成夫妻了!这比赵高指鹿为马还可恨。她突然厌烦了这的一切,觉得女人的嘴真是世间的一大祸害,一切的女人包括自己都是心口不一,使出百般手段掩饰自己的真心意。唱反串是女人天生的本领,哭着爱,笑着恨,仿佛只有这样生活才有滋味。友谊这东西别想从女人中找到,就像别指望从公牛身上挤出奶一样。其实,汤芙的觉悟晚了四百多年,早在十六世纪法国的思想家蒙田就已经悟出了这个道理,断言女人的灵魂不够笃定,不足以承载像友谊这样耐久的关系。
事实也确是如此。
《琥珀的眼泪》二十三
汤芙同白冰峰同坐了几日,像被润滑后的机器,全身零件无一处不滑腻的。语调柔媚得令公鸭嗓的周讯不好意思称自己是女人。一张小脸红扑扑地像浸入水中的一滴红酒,荡出醉人的红润。汤芙坚信已经把白冰峰迷得神魂乱窜了。她有理由这么想,他不是总害羞地扭过头不敢看自己么?他不是总主动地为自己排忧解难么?他对白彦的态度不是像主子对奴才似地呼来喝去么?如果说一个男人对女人温柔不一定意味着爱,那么不温柔就一定不是爱。汤芙想通了此节,又把刚才的华彩章节重温一遍:
是才在教室里,白彦走到白冰峰面前小声嘟囔了一句,汤芙没听清,以为她的声音是事先调拔好的,只许白冰峰一个人接收,恨得刚想扭过头去,却听白冰峰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火力向白彦吼道:“你大点声,我听不见!”唬得汤芙以为白彦的音量都转到他身上了,禁不住替白彦伤心。
“你好好说不行么?”白彦忍辱负重地引导,充分展现了中国女性无以伦比的忍功。
白冰峰沉默着,藏住不耐道:“你说吧。”
汤芙虽然想继续观看又觉得这样做人有失厚道,起身离开座位。不过心里难免像久旱逢甘霖一样地畅快,原来他们的关系好似美国工党与自由党一样对立多于合作;原来他们爱情的小粥已越熬越焦;原来自己还有梦可做———
文中子的《止学》中有这样一句话:谋身者恃其智,亦舍其智也。说白了就是要权衡智计得失,当用则用,不当用则不用。只可惜汤芙学而不能至用,如果她知道了男人对妻子态度的恶劣是因为他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人,而自家人又何必客气?她就不会把梦做得像圆规画出来这般圆。要知道男人费尽心机哄的总是还未追上手的女人,对到手的女人献殷勤那不是浪费生命么!力气当用在刀刃上。
可是爱情中的女人没有一个不是傻的,总以为自己是吸铁石,恰好套牢男人铁石般的心肠。汤芙的梦做得缠绵,又在“思冰小语”上留下浓情一页:
“沅有苣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多少个漫漫长夜萦绕在我心里的不就是这句话么!“思公子兮未敢言”,我不言你就真的不知道么?
在茫茫人海中我生怕你望不见平平的我,时时刻刻提醒你我的存在。我真的情愿开口一唱么?如不是你在身边,千万人亦不能使我从愿。雷雷掌声难动我心;你一人微笑我心足矣。
每每与你擦而过,欢快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却装做毫不在意。若换了旁人,先与之招呼又有何妨?可是因了是你便死也不肯先开口。知道为什么么?如我先招呼,即便你回应微笑,总有不得以而为之之嫌;如你先开口,定是心中所愿而现于言表了。偶有几次你低头思索,似未见我,匆匆而过。我心中失望之情难以抑制;或你微笑而来与我对视,我心便似风满帆船,神游苍穹。多少次,你的一个微笑竟成了我一天快乐的源泉了。
寒暑相替,日沉月起,但问:茫茫宇天,春事谁主?难道你我真的只有相识之缘而无相知之份么?说到相知,我不仅又要怅惆唏嘘:其实我比她更懂你。我懂你的如烟云般飘渺的愁思;懂你的如白雪般剔透的尊严;懂你的如我般痴的心境。而你却舍弃了知你的我,选择了与你隔如尘世的她!我不禁要问:你怕什么!是怕痴心如你般的我伤了痴心如我般的你么?唉,聪明如你,我又怎能伤你。
你亦是知我的。你若不知我,就不会在人影交错中不独望见我,且在我忧心恐疚时轻问一句:“你怎么了?”;你若不知我就不会在我烦你帮忙时轻轻一笑,那笑容却是从未向她展示过的;你若不知我,就不会在我叹息耳环的不适宜时轻补一句:“好看的。”狠心如你,为何不让我明了你是赞耳环呢?还是赞戴耳环的我?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固是人世间之惨事,然“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不更是惨中之惨么!善良如你,望你在心灵底处独为我留一份沉吟感怀之空间吧!
窗外夜暮正急,窗内愁云弥深。伤心至此已无言语表达。然我心中之情竟未能诉出万分之一,聪明如你,望你在我这零乱文字中揣度我“待不思量,怎不思量”的凄凄苦情吧!
公平的说,这最后一笔文思绮丽,堪称绝唱。却是她从某小说中背熟的句子,至于是源于何人之手她自己也忘记了。这同小偷偷走别人的钱而扔掉钱包是一个道理。没了睹物思过的机会,多少能减轻点儿负罪感。汤芙合上了日记本,似乎又有了走下去的理由。
《琥珀的眼泪》二十四
一周即将结束,按照惯例仍由抽签决定位次。汤芙觉得刚与白冰峰有些苗头就要分离,比猎人射中了猎物却无暇拾起还要惋惜。心里捉摸着以周长发《送别》中的诗句来证这段同桌之缘:临行一把相思泪,当作珍珠赠故人。相思有些露骨,应当斟酌,难得的是故人二字,何等意味深长而不露痕迹。就如同美国大片《SOMMERSBY》被译成《似是故人来》一样含蓄,如果改成似是夫君来就逊色多了。
与“故人”临坐的最后一天,汤芙早早地来到座位,望着白冰峰的位置发呆。不一会儿白冰峰竟也来了,空空地教室里只他们俩人。
“早啊。”汤芙抬起一张粉红的脸庞,甜甜一问。见白冰峰玉树临风地一站更是情深深意浓浓。
“你更早啊,”白冰峰侧头一笑,紫芝般的眉宇动人心魄。
汤芙中毒颇深,语无伦次地剖白:“最后一天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