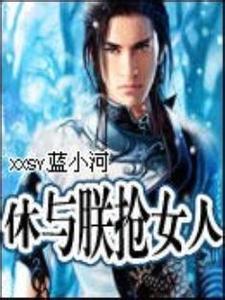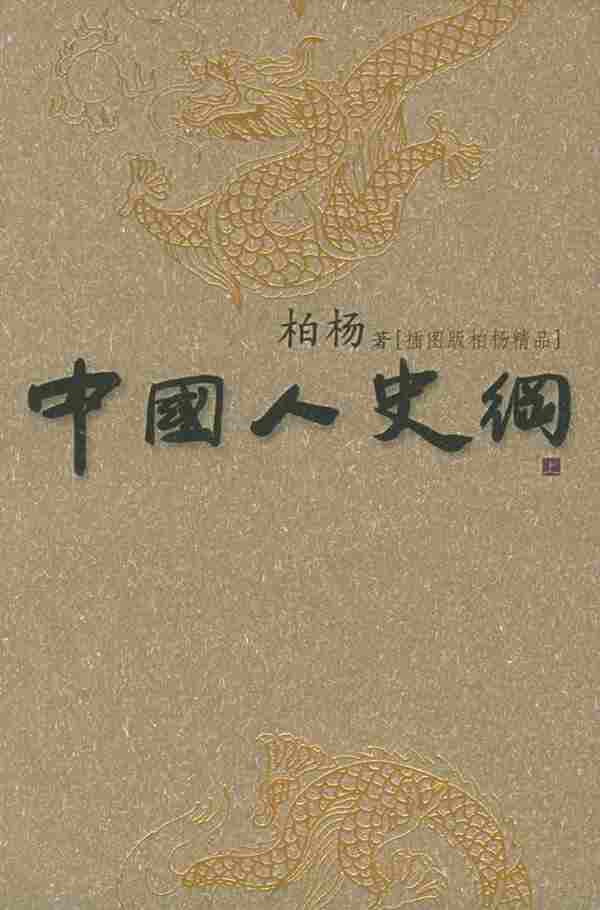中国女人因异族情爱身陷美国监狱:爱之罪-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得给我妈打电话了。”女孩儿抹抹眼睛,站起身,拉拉紧裹在身上的一件很短小的深紫色衬衫,不好意思地笑笑,然后向电话走去。这是个很丰满的女孩儿,身材匀称而富有弹性,男人看到她,一定会浮想联翩。
“妈,几点了……”她对着话筒说,身子左右晃着,好像撒娇的孩子。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女孩儿放下电话,又走过来,眼睛忽闪着,冲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好工作,可一进这儿,工作就没了。他妈的,真气死我了。”
“你做什么工作?”
“爱迪生煤气公司会计。”
“嗯,不错。”我点点头,确实,丢了让人可惜。
女孩儿看着我,目光有些游离,无奈而无助的样子。不知怎的,她讲她的故事,挺让我感慨。她说是她先打了那女人,这我完全相信。人活一口气,气上来了,想怎么都可能,谁会想后果?!但人毁也就在一旦间呀!那天,彼得一口气上来,一出气就出得这么长。如果他没有弃儿的经历,他的气会这么出吗?我会坐在这儿吗?
“他多大?”我问女孩儿。
“37。”她回答。
我看看她,简单不敢相信,她小那男人10岁,竟已跟了那男人10年。这样算来,她那时也就17岁,真是太年轻了!17岁的年纪,正是花季,除了梦想,能懂什么?!一朝失足终成恨,好在还不晚,她还年轻,生活的磨难会让她成长起来、成熟起来,我默默里为她祝福。彼得也摔了一跤,但他已过四十,一眨眼五十就到了,中年摔跤,还爬得起吗?唉,他诬陷我,加害我到如此地步,我却还暗地里替他惋惜,他想得到吗?他一定不会想到,他的心里充满了恨,他没准正咬牙切齿,杨眉,你等着瞧!
女孩儿的眼里现出泪花,一闪一闪。我不好问下去,便有一搭无一搭地转了话题,“你是多少保释金?”
“2。5万。”
什么?!顿时,我如挨了一刀。动手打人,有痕有疤,有凭有据,才2。5万保释金。一个不明不白的电话,却居然要我5万!美国也太市场经济了吧,连保释金的价格都是自己定。有鬼,有鬼,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感觉,圣博谷警察局有问题。一时间,我竟不再感觉彼得可恨,因为我不爱他;相反,我却开始恨圣博古的警察了,我不仅恨,而且还无可奈何地想笑。如果谁再说美国的系统是最好的,不管他说或她说,不管是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中国人、日本人,我一定都会淡然一笑。一个国家像一个人,人的脸上、屁股上都有疙瘩,十年前起过疙瘩,今天还会起疙瘩,昨天就保证不会起了吗?
我恨圣博古的警察,我会fight back!
“杨眉。”铁门边上的小喇叭叫起我的名字。我想该是我上法庭申辩的时刻了。
我走到铁门前,不一会儿,铁门自动拉开,一个两边有钢网的过道出现在眼前过道的尽头是一个铁门,穿过过道,在铁门前,我停下来,法警按下一个电钮,铁门开了,我走出来,告别了我所谓的罪恶。
“你自己出庭,还是要求律师?”法警问我。
“律师。”我答。
“人在哪儿?”法警又问。
“我还没通知他。”我说。
“来不及了,”法警看看表说,“不过,你可以请公共律师,法院有。”
“好吧。”我只好答应。
法警的手指顺着一个名单往下捋,捋到一个名字下,抬头对我说,“你的公共律师是阿利妲。”
阿利妲,一个女的,但名字不太像美国人。我琢磨着,希望能琢磨出什么,无论如何,对目前的我来说,她很关键。
“杨眉,2号窗口,”法警叫我,“阿利妲在2号窗口和你谈话。”
法警带我走进一间屋子,屋子分两部分,分水岭是8个连为一体的窗口。我站到2号窗口前,但窗口里没有人。阿利妲还没有来,我只好站在那里等。旁边的5号窗口,一个男公共律师正在和一个犯罪嫌疑人交谈,我立起耳朵,想听听他们在谈些什么,但却听不清。
“杨眉,我是阿利妲。”声音从5号窗口里传出来,我一怔,回过神来。
天呀,这就是阿利妲?!窗口里出现一个女人:一头乌黑蓬勃的头发高耸着,不难看出,头发是染的,早晨一定花了很多时间用在头发上;脸上涂着粉,很浓也很厚,如果跑起来,真担心会掉渣儿;两腮抹着胭脂,远处看,很是精神焕发;薄薄的两片嘴唇,涂着很艳的口红;上身着一件哆哆嗦嗦的深紫色仿丝绸衬衣,下身穿一条宝石蓝长裙……我有些发呆,一时竟手足无措起来。阿利妲,我亲爱的公共律师,简单就是个吉普赛女郎、一个城市化吉普赛女郎!
“你是杨眉,中国大陆出生,美国公民,早晨8点打电话给米娜女士,恐吓她……”阿利妲在朗读我的履历、我的“罪行”履历。
我打断她,“我是受害人,我前男友……”我陈述起来,希望她能尽快了解我的特殊案情。
阿利妲抬起眼,看着我,脸上毫无表情。
我接着说,“亚洲犯罪特别工作队的艾尔斯探警说,圣博谷警察局同意10点钟释放我。”
“哦?是吗?现在都下午2点了,我们什么通知都没收到啊。”一脸粉脸终于有了表情,冷嘲带热讽,似乎在说,到了这会儿,怎么还不老实!
“你认罪,还是不认罪?”她问。
我瞪大了眼,“什么认不认?我根本就没有罪!”
“很好。那就上法庭陈述吧。” 阿利妲耸耸肩,不再说话,低眼收拾文件,然后起身走了。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身子仿佛也失去了知觉。脑子一片空白,眼前也一片空白。法警说了些什么,又是怎么返回了大厅,我全然不觉。
“你是哪个律师?”一帮女孩子围上来。
我这才醒来,“阿利妲。”
“噢,我也是。”几个女孩儿叫起来。
“什么阿利妲、哈利达,都一样!”一个女孩儿说。
“我看,大家还要多多保重。”一个女孩子叫。
叽喳声中,我彻底清醒过来。什么公共律师,还不如自己为自己辩护!
《爱之罪》第八章7
“杨眉,过堂。”一个声音响起。
我被铐上手铐,带上了法庭。
法庭上已经坐了十几个犯罪嫌疑人,阿利妲似乎没来,我没有看到她,她去哪儿了?正当我猜测的时候,我的名字就叫到了。一个男人站了起来,我睁大了眼,转向身边的法警,看着他,他也看看我,蚊呐地说,“你的律师。”
我的律师?我的律师不是阿利妲吗?
看那男人的脸和那一身西装,让人觉得他是个律师,但看看他那头发,不免又产生困惑,这个世界怎么了?!那男人的头发留得很长,很随便地扎在脑后,好像50年代嬉皮士音乐家。不过,嬉皮士音乐家都是年轻人,即便长发扎起,也是粗粗的一团,但这个男人,已年近50,长发扎起来,就剩下细细的一缕,黄黄的,而且焦黄焦黄。这个法院真奇怪,怎么雇了这么一帮人做律师?!这儿可不是纽约的百老汇,也不是什么田纳西州的乡间乐团,这里是法院,美国最大的一个县的法院,洛杉矶县高级法院!
法官席上,法官威严正中地坐着,看上去倒挺像法官,一身黑袍衬着花白却不稀疏的头发,脸和眼睛都亮亮的,人比较瘦,大概是每天阅读判案太多,吃不下、睡不香累的。我的长头发律师站在被告席上,和法官一问一答。两人的语速都很快,声音像拍电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两人没说几句,我的长头发律师便转向了我,“你认罪还是不认?”
“Not guilty。 I am innocent。”我看都没看律师,冲着法官脱口而出。
我就是把英文全部忘记了,也会记住这句话:我无罪。我等待法官问话。
法官并没有理会,而是举起一个深褐色的木锤,往桌子上一敲,说:“送县监狱,保释金减为4万。”
我的审判结束了。这不是审判,这是赶羊!
下电梯时,押我的法警为我高兴,“不错,减成4万了!”
我没有哭,也没有笑,眼睛看着他。到了这个时候,我还能说什么?福尔摩特定我罪,值五万;阿利妲和长头发律师赚纳税人的钱,法官判的是钱——4万美元,法警替我高兴也因为钱。人人都在谈钱,正义呢?
《爱之罪》第八章8
在我最恐怖的那个夜晚,那个我孤独地躺在拘留所冰冷的长凳上哭泣的夜晚,彼得的感情攀登却达到了巅峰。中午的时候,米娜向他表功,警察已经把杨眉带走了!彼得听了,一下子跳起来,一肚子邪气似乎也一下子释放了出来,好像一个超重的人一夜之间脂肪突然消失了一样痛快。那个夜晚,他哪里也没去,什么电话也不接。他知道米娜又打来过好几次电话,而且每一次都留言请他打回去,但他没有打。此时此刻,他要独自一人体味人生。
他关掉了家里所有房间的灯,然后走进客厅,在窗前站了片刻,这才坐进面对大海的沙发里,开始凝视黑蓝色的大海。此时的大海与墨色的天空连在一起,没有了边际,只有几颗遥远的星星一闪一闪,似在提醒着人们,天空还存在,天堂还存在。彼得望着望着,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几十年来的怨气,对生母的、对詹妮的,以及对我的,似乎都在那一刻吐出来了。他把自己的不幸,都归结到了女人身上,他在心里呐喊,你们等着吧,给我不幸的女人们,我一定要把同样的不幸还给你们,一个一个,一定!这时候,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个他曾经最亲近的女人,他的两个母亲,他的曾经拥有过的女人,她们的声音,她们的轮廓,她们的面容,甚至她们的身体,一帧一帧,飞快地变换着,重叠着,一个浮出来,升上天空,一个又隐下去,没入大海。一个接着一个,他的大脑,如一个巨大的轮子,转啊转啊,女人们的灵魂似乎也在他的掌控中了,他让她们浮出,她们就浮出,他让她们隐没,她们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她们的生与死都在他的一念之间了。渐渐地,彼得的周身热起来,下体也强硬了。这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刺激,一种他所倾注的爱与他对他所爱的女人的报复混在一起的刺激。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喷发一切终于恢复了平静,除了依旧哗哗的水声。彼得关了龙头,围上浴巾走出浴室,重新坐回到沙发上,身体飘飘的,好像空了一样。过了一会儿,他才清醒了些,才分辨出哪里是墨色的大海与天空,但幻觉却没了,围着他不停闪现、并听任他操纵的女人们逃得无影无踪。他的心一下子空落起来,爱空了,恨也空了,刚刚还强烈无比的那种神奇的操动意识随之也消失了。无限的寂寞袭上来,他落泪了。
《爱之罪》第九章
《爱之罪》第九章1
一辆至少能载50人的大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车身上半部为黑色,下半部呈银灰色,黑色带居中写着一排醒目的大字——洛杉矶县监狱,黑色带上侧是一溜小窗,小窗被钢柱横着,每个窗口都直头直脑地坐着一个人,我也是其中一个。过去,不知有多少次,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狱车,都会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里面坐着些什么鬼东西?也不知干些什么鬼事!”现在,外面的自由人一定也在问:“这些鬼东西,都干了些什么?”
“地狱也需要好人。”我曾对传教士说,他嗤之以鼻,跑了。但是,不对吗?看看我现在,我就被一条粗铁链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