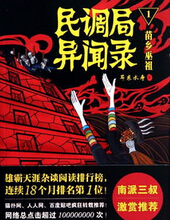难言的结局-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贫穷只是对贫苦的人才是灾难,而对富贵的人则是一种享受和乐趣。
风透过他单薄的衣服,直袭他的肌骨。
薄薄的雾淡了,但在他的想象中,淡去的雾却意味着另一种悲剧的命运等待。不知坐了多久,一辆货车从他身边飞过,扬起的尘土布了他全身,他愤懑地骂了一声翻车死的,起身向山上走去。
路两旁是整齐对针的枫树,经过整个秋风的洗礼后,在阳光的照射下,从枝叶间渗下斑驳倩影。时不时有枯黄的枫叶落下击着他,他拾起一片凝思了良久。
路的转弯处,一辆车翻了。雷如文走过去看,是他刚才咀骂的车。他心里很不自在,他随便骂一句,车就翻了,显得很灵。如果是乡下女孩,她会因此被人们说嘴巴不好,做什么事都不能让她看见,否则不小心被她说了,结果是好事不成坏事多。
车上是两个人。司机从挡风玻璃冲出去,头插在田里的稀泥巴,血淌了一大滩,早就没命了。另一个人从车窗甩出去,整个人窜进谷草堆里,露在外面的两条腿一蹬一蹬的。雷如文把他从谷草堆里搜出来,他的伤势很重。这个人就是一中程茂隆老师。
3
雷如文跟救护车进医院,医生问他是伤人的什么人,雷如文说他是以前的老师。雷如文一直在医院守着,他见程老师醒过来,很是激动。
“老师,你终于醒了。”
程老师是乡下进城的,已经和老婆离婚了多年,女儿还在外省读大学。在城里由于经济据洁,他不随众进歌厅,洗桑拿、打麻将、挖包、焖鸡等,所以熟人不多,很熟的人更不多。
“你怎么在这里?”
“是你报警救我的?”
“我看见有车子翻了,就报了警。”
“喔。”
“司机呢?”
“没了。”
虽然程老师在同事中并不是印象很好的人,但出了这么大的事,学校老师还是陆陆续续的来了,手里还拎着大包小包。他们都跟程老师说话,很亲热的样子。雷如文被凉在一边,心里很不舒服,特别是程老师问的那两句话,令他特别难受。更气人的是,这些和程老师说话时,还时不时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仿佛程老师的灾难是雷如文造成的,而又装做好人来守的。不过,从外表看,雷如文一点都不象好人。他的脸烫得发紫,心跳得特别厉害,仿佛要跳出胸廊似的。
他走出医院辖区,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
中午,来探望程老师的还有学生。王荣臣没有来,放学后,他到处找雷如文,但在马路上、在校园里、在大街上,仍然找不到雷如文。
王荣臣是个性急的人,只管大事不管小事的人。他如火如荼冲进李金钱家。李金钱家住在幸福小区,室内装修得金碧辉煌:木板壁,大理石地板,大音箱,电风扇,热水器,空调,电视机,录像机……
王荣臣到大楼楼梯口的铁门,按了一分多钟的门铃,才有人在家里给他开铁门。李金钱的父亲李玉堂,已经知道王荣臣来了,只有王荣臣才按他家门铃一按就一分多钟不松手。这是当官家孩子霸王的行为,无法无天不礼貌的坏习惯。
王荣臣脱掉沾满泥土的皮鞋放在五花八门的鞋架上,趿着拖鞋走进去,刚坐定憋不住的尿意就袭来。从卫生间出来,李玉堂问他,
“小雷是来补习的吗?”
“你见过他?”
“早上我见他,我叫他吃糯米饭,他说不吃。我看他的脸色不对,好象有什么心事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他来这里过吗?”
“没有,好象他知道小金钱去广州似的,要不他要来家找小金钱玩的。”李玉堂是个爱唠叨的人,只要有人搭话,就象决堤的洪水一样,堵也堵不住。王荣臣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向楼下走去。李玉堂斜着和身子,把王荣臣整落的沙发垫巾拣起,骂道:“这小杂种,一点礼貌都没有。”
4
李玉堂是话多,做事心细的人。他在窗前望着王荣臣远去的背影,呢喃着:“吃人嘴短,收人手短,能说什么?一个小娃娃,比自己老祖宗还得尊重。”
当年,李玉堂出了个官司,不大也不算小,差点进农场吃几年闲饭,幸好李金钱和王荣臣玩得铁,王荣臣年龄虽小鬼却大,开口就是这有啥难,回去跟多老爸说一声就是。星期六,王荣臣真的回去跟他老爸说,回来跟李玉堂说没事没事。李玉堂就这样轻轻松松免了牢狱之灾。很快,李玉堂给王荣臣父亲送去三千元感谢费。李玉堂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什么人也接触过,也算见世面的人,哪些关系不能丢,哪些关系不可多留。对于王荣臣父子,更不可能过河折桥,每当逢年过节,他都要去王荣臣家坐坐,表示意思意思。
王荣臣在街上毫无目的瞎转着,希望遇见雷如文。可是,雷如文哪里知道王荣臣到处在找他,心中还有他这位贫寒的朋友。雷如文在雅坐书屋看书,心里还很乱,在想程老师出的车祸是不是他说的那句话造成的。班上书謎张卫东正在这里选书,他看见王荣臣路过,就把王荣臣叫住。王荣臣说没有时间,他还在忙找雷如文。
雷如文听见,跑出来说你跑哪里去,我到处在找你。
书屋里书很多,主要是杂志和小画书,除此就只有几本外国名著。
“你怎么在这里?”
雷如文把发生的车祸省去一些细节告诉他。王荣臣为此既高兴又惋惜。他高兴不是程老师再也不能上他们课了,而感惋惜的是这位带着东北人的杂种人再也上不了讲台。程老师,据说是位东北知青来和本地农村女人结婚生的,一米八胖胖的身材,宽宽的脸上架着一副大大的眼镜,脸阴得让人不敢正视,说出的幽默话讽刺得你既想笑又想骂,但却不敢发作。他的知识和他的鼎腹搭配得十分和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谈古论今说神论鬼无所不通,但每次的幽默讽刺话都少不了王荣臣的份。
雷如文盯着王荣臣,心里话到嘴边多次都被他憋下。
“你怎么不来补习呢?”
他说,他的父亲因为生病去打针,打错了针成了瘫痪,家里没人找钱,读不成了。他本来期望寄托在两位好友身上的,李金钱可以支持他的钱,王荣臣托他的父亲可以帮找工作。细细一想,实际又不是那么简单,有时候唱的不得说的好听。
沉默。
很久王荣臣才说:“你何去向李叔借点钱?也许他能支持你读书。”
有时候沉默总比回答效果好,雷如文没有回答。有一点充分说明雷如文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王荣臣始终没有说他去跟他父亲商量,帮谋一份工作。
再僵持沉默,就会使双方都感到尴尬。但雷如文确实找不到什么好话来说,只问李金钱做了什么。王荣臣告诉他,去广州了。雷如文再也找不到什么话,没再说什么,久久的仰望长空。
5
有时候,接受别人的施舍是对自己灵魂的出卖,也是贬低自己的尊严。李玉堂知道雷如文的处境,是王荣臣告诉他的。李玉堂想起雷如文的故事,脑海里就渏涺起来,想起多年前的自己。他小的时候,新中国刚解放,从小他就没爸没妈,由一个堂叔拉扯大的。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就象大人一样不管严寒酷暑,赤着脚穿得破破烂烂的衣服在田间地头劳作。后来到处流行什么病疫,把他叔家人都吞噬了,他虽没在这场病疫中受难,但却不得不孤零零地背井离乡。有时候,苟且偷生下来也是一种错过、罪过,在以后艰难的日子令人不堪回想。
李玉堂在屋里踱来踱去,不停地吸着烟,自己对自己说:“可怜,怪可怜。”
王荣臣请雷如文看电影,雷如文没有和他说多少话,很快就睡着了。王荣臣心里很难受,他也想了许多许多,但他却无法把话跟雷如文说。没等电影放完,他就把雷如文摇醒,离开电影院。
明恍恍的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细长细长的。
“如文,创作是很找钱的。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才气,我一定努力去争当一个作家,不要工作。”
“是吗?”
漫漫的长夜终于敖过去了。
王荣臣送雷如文到车站。李玉堂在路上遇见雷如文,他象长辈般地握着雷如文的手,说:“可怜的孩子,这点钱拿回去给你老人买点东西。”
雷如文没有接钱,沉重地向车站走去。
第七章 叶落归根
现在想起来,我根本就不是吃文字这碗饭的料,顶多算作文学爱好者。当然,我写的小说就不能成气候,而我写的这个故事也没能完完全全写完。我写到周倩已经死,小欢最终跟雷如文回家时,就没能写下去,这主要是后面的事我一概无知,我已经东到沿海去刨金了,甚至改行了。请不要问我做了什么,说出来吓死你。起初,我也不想干,我知道是违法的,要判刑,坐牢的。但我不做也不行,我在广州三番五次被人抢被人偷,我心寒了,他们不怕死,我为什么要怕死。我在广州就凭两把宝剑,一口气砍三十多人,我身上中了两枪,但我的勇气逼我奋不顾身冲上去,在我剑下倒下去的人,就象决堤的洪水一样。最后,他们跪在地上,哭爹喊娘的,求我。我成了他们的主人,成了他们的老大,我不用动手,每个月都有人上供,我走到哪里,人们都要离得远远的,我多看哪个人一眼,这个人就会声音颤抖,赶紧逃开。我在异地他乡,“风风光光”过日子,但在家乡却成了臭名远扬的败家子,就连雷如文都把我写成了小说,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好象我与他过不去似的。当然我知道雷如文写我已经是过去多年了,幸亏也过去多年,要不然我一只手把他掰成两段。我知道树大招风,人大招殃这个道理的,我揽足钱,也想做些正经的事,这可能就人“性本善”的原因。我失踪了,永远地失踪了,再也没在地球上出现过。我去香港一年多,整容了,没有人认出我。后来,我到深圳发展事业,开一有私人侦探所。只要你给钱,我都会给你找到你要的资料,最解气的是:一个派出所副所长想搞掉他的上司,找到我所来,用不到一个月,就帮他找到所长八大罪证,最终所长被下放为平民,副所长因此位置摆正,新所长很感激我们,一口气就他妈的送我们六万元。当然钱不是他的钱,而是单位的,我们没点破,也没必要点破。后来,我和所长的关系就象亲兄弟一样,这又奠定我私探所前景。
雷如文认为我死了,或者逃到国外去了。我的朋友也这样认为。这也好,免得雷如文拿他的笔大写特写我,把我当成他赚钱的工具。
广州杀人不眨眼的老大没了,公安找一段时间没找到,就象人们轰轰烈烈议论外星人,在没有亲眼看见一样不了了之。我听到公安方面说我被比我更厉害的黑手杀死丢进大海去喂鱼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想笑,我哪里会死,我能死吗,我就在他们眼皮下生活,活得好好的,只是出乎他们意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居然会是同一个人。
有天,一个女人走进所里来,穿得富态,长如仙女一般,让人见了眼馋。样子上,她结过婚,嫁的是阔老,抑或自己能找到大钱,但不影响男人对她的欲望。那天,我没在所里,接待她的是我手下的小王,她对小王说想请我们帮她搞定一个男人,而且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她说只要我们帮她的忙,她给我们五万元,客家出这个价,在同类案子上是高价,高得离奇,帮一个女人搞定丈夫,对我们来说就如孙悟空翻几个跟斗,要一百个证据都行。可小王没有答应她,他说这事很难,而且他紧紧地盯着她,生怕她从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