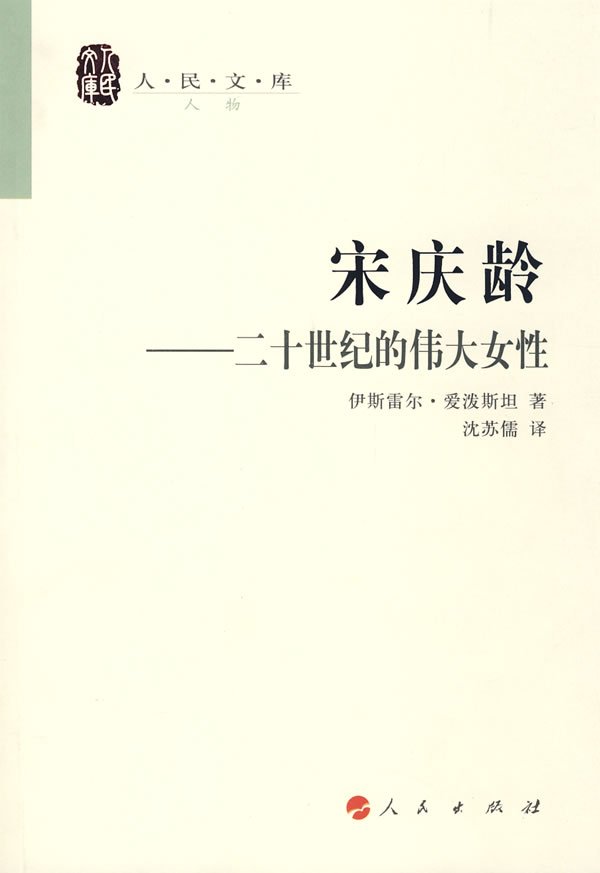世纪烟云-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担惊受怕是怎样过去的;民兵每天只给他一点吃的和喝的,他又渴又饿,喉咙干涩得发烧,但最难受的却是蚊虫叮咬。这些蚊虫不管白天黑夜都狠命的叮咬他,咬得他浑身肿烂,坐立不安。他头昏昏的觉得自己快支持不住了,模糊地祈求着天主保佑。不过,他清醒地知道,私藏武器这一件事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这一天吃饭后,有一个圆脸平头、说话象女人腔的人叫他走出禁闭室来对他说道:
“周老板,你私藏武器是人证物证俱在,必须好好交代。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给你两种选择:一是写好坦白交代书,把还有武器放在什么地方写出来;一是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你就写好遗书吧!”说完,从他鼻子里发出“吼、吼”的两声,他放下纸笔就昂着头走了。
他能写什么呢?他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阴谋。这个阴谋是要他死,这个人说的所谓“两种选择”都是死,是谋财害命!想到死,他心里一阵慌乱,突然感到可怕起来。他有那么多资产,有许多未竟的事业,有高堂慈母、娇妻爱子,他死了之后怎么办?这一切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这难道是天意么?这些天来,常听到有钱人的性命朝不保夕的一些消息,有的今天还活生生的,明天就死了。难道今天就轮到自己了吗?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啊!他想,也许是父亲在天上召他去了。他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流着眼泪轻声地祷告着,然后,颤抖着双手,写下了遗书。
那天的晚饭多了一点,还有点肉。他吃了一点,便坐在潮湿的泥地上一边想着这几十年来短暂的一生,一边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他今年才三十岁,二十岁起就跟着父亲做生意了。父亲在南洋过了大半生,抗战前曾在香港开织布业,香港沦陷后回家乡来办织布厂。家乡地处山区,日本鬼子打不到来。抗战时候有很多内地的人都逃难,举家往偏安的地方迁居,县城便迅速发展,生意也跟着兴旺发达起来。徐昌城一时竟有小南京之称。至解放前,父亲开办的信义布厂占了县城河背一条街,有二百多台机器,漂染和织布及管经营的就有三百多工人。从抗战胜利开始,布厂的生意已基本由他管理。他设计备料的“徐昌士林”是信义布厂的名牌,远销南洋海外。两年前,父亲又着手开了个金铺,生意一度看好;但后来红军白军战事频频,国民党的胡、谢部队两次光顾县城,福记金铺便不敢再开了。解放后,他本踌躇满志,想好了一套计划,准备在政府领导下,大兴民族工商业。但可没想到时不在我,他深深地为自己叹息,也为自己没有象某些商界朋友那样及时离家远走而后悔!
他又想到妻子。妻子陈兰英是他在县城高中读书时的同学,长得娇艳秀丽,十分漂亮,曾是学校的校花。她温柔顺和,他很爱她。她娘家也是从潮州地方迁来的,她与他结婚后,一直就在城里小学教书,这些时间来却都在家里担惊受怕。她和儿女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又在想多病的慈母。
忽然,东边的墙上发出了蟋蟋嗦嗦的声音。他惊疑的望着。不久墙上出现了一个小窗户那样大的洞口,微光从外面透了进来。
“快出来,快出来!”外面一个人在小声说话。
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心卜卜地跳起来了。墙洞开在齐腰高的位置上。那人把上半身探进来,伸手来拉他。他本能地把手伸给他,很快就爬了出去。
十月小阳春,外面正下着雨,天漆黑黑的,但常有电光闪闪,有几声闷雷。路很滑。那人也不打话,一手拿着一根棍棒,一手拉着他在前面走。他心里慌张,脚步空虚,打了几个趔趄却没有跌倒。他们朝岭那边的村外走去,拐了几个弯,便来到了叫伯公坳的乱葬岗边。那人停了下来,拿出一条绳子,三下两缠,就把周树和绑了起来。
“好汉要做什么?”他颤抖着问。
“告诉你,周老板,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你村里有人出钱要杀死你!你是地主份子,活着也受罪的,不如早日见阎王去吧!你还有啥话说?我要你死得瞑目。”
“轰!”突然,一道电光闪过,天空响了一声惊雷。周树和看到了那人咬牙寰眼的狰狞嘴脸。只见他迈开脚步,抡起棍棒,就要劈将落来。周树和吓得魂飞九窍,他两脚像筛糠般的打颤,只眼睁睁的看那棍棒朝自己的头顶劈来。
说时迟,那时快,随着“哎哟!”一声,棍子没打下来,却见那人跌倒下去,他跌到前面地上一个坭凹里去了。
依稀的电光下,只见斜刺里跳出来一个人,他拿起摔在一边的棍棒,对坭凹里那人喝道:
“吴日牛,谁要你谋杀好人,说出来饶你狗命!”
“是、是你们村、村的农、农会长易贝车要我杀他的!”吴日牛趴在地上结结巴巴地说道。
易凌胜在村间有一个雅号叫易贝车,贝是赌字的偏旁,车是输字的偏旁。他是赌输身家出了名的,故有人便给他起了个外号。许多本村或邻近的人不知道他的正名却只知道他的雅号。这吴日牛是邻村人,专干抬脚挖泥窿的营生,也是远近无人不识的。
“他怎么对你说?”
“他说这周树和是地主,私藏武器妄想变天,应该处死。杀死周树和后,他叫我把他埋了,并取下他的信物交给他,赏我两担米十吊钱。”
“天杀的,今天我把你们两个都剁了!”
“好汉饶命!”吴日牛爬了起来,浑身泥浆跪在地上说。
原来,救周树和的不是别人,正是铲头的父亲周金富。周金富年长周树和一岁,是周家村里的武打师傅。他父亲早丧,靠母亲做针线活和帮人打短工维持生计,从小受苦。后来母亲到周伯年家煮食,小金富便常出入福源楼,逐渐与念小学时的周树和相好相知。因老实听话又有礼貌,便备受周老太的关爱。稍长便叫他到城里去打工学做生意。但他生就一个好身材,长得虎臂猿腰,无心学做经营,却常到城里武馆去舞拳弄棍,练就一身武艺。后来,母亲生病,幸得周老太出钱请医生治好。母亲病愈后他回家来设馆授艺,也教出了不少徒弟,在一村八堡中颇有些名气。他的妻子是在福源楼打工的妹子,也是周老太撺掇的。所以,周伯年一家,实是周金富的恩人。
那一天吃晚饭时,他听铲头说,他和几个小朋友到茔下塘摸蚌摸到了许多枪和子弹,交给了农会,奖了五毛钱。铲头还把农会奖的钱买了一包香烟来孝敬老爸。他摸摸儿子的光头,夸了他几句,还没在意。可是,第二天又听说农会长叫他们几个小马骝到福源楼门前的玉泉池去摸,并且,竟然又摸到了子弹武器,他就心里犯疑。再后来听说农会捉周树和去审问,他便知道必然要出事了。这几日,他暗中密切注意起来。今夜天黑下雨,估计会有情况,他便在小学校旁边监视了半夜。刚要离开,忽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猫着腰在东边挖墙洞,后又见他带周树和出村,便一路跟着不离。当吴日牛举起棍棒要劈下去时,他在土墩后一个箭步跃上去,飞起一脚,咚的一声便将他踢到泥凹里去了。这一杀手锏叫飞鸿无影脚,正踢中了吴日牛的腰部,直疼得他起不了身,坐在泥凹里哎哟哎哟地呻吟起来。
周金富正要举棍劈打吴日牛时,周树和连忙拦住。
“放他一条命吧!”他说。
第二天,乱葬冈上多了一个新坟。据吴日牛说,这新坟里埋的就是地主周树和,但这事只有他和岭塘村农会长易贝车才知道。吴日牛交给易贝车一只怀表,一支派克钢笔,这是周树和身上的信物。易贝车查验信物后给了吴日牛两担大米,十吊钱。
周树和的家里被通知:农会怀疑周树和私藏武器,但他被传讯后畏罪潜逃,现正报告政府通缉。一时,家里无法打听他的下落。
铲头的爸爸出外做生意去了。走的时候他对铲头母子说,要好久才能回来。走后,他的家庭成份被划为中农。
不久,吴日牛病了。腰部积瘀,起不了床,又兼发冷发热,不到一个月便一命乌呼了。有人说他死前大叫“地主饶命!”大约是做了亏心事,被鬼谋死了。易凌胜听了,吓出了一身冷汗。再不久,他的痨病婆娘也死了。他夜晚一个人不敢出入,并且,每天晚上都要把一张刀放在床头镇邪,才能睡觉。
星星还是那样的晶亮,月亮还是那样的柔和,太阳还是那样的猛烈,村里的小溪流水还是那样的清幽,那岭上的榆林还是那样的静穆。可是岭塘村的一切人和事却在一两个月中全变了。
先是划为地主成份的十五户人家全都被扫地出屋。他们中,有老祖屋的被赶回祖屋;没有祖屋的,被赶到一些做过牛栏猪舍的棚屋去住。周伯年一家被迁到小易屋去。这易屋有五间瓦房,虽是土砖砌的,年久砖墙剥落,坭地又很潮湿,但不漏雨,毕竟比牛棚猪舍好多了。农会规定,这十五户人家中,如果年满十八岁以上又不是地主份子的,均可在原来居住的屋里分给一间半的房子;未满十八岁的子女和未嫁出去的女儿还要父母照顾故仍应与父母一齐居住,没有条件留分房屋。但家中不管是谁,大小男女离屋必须先搜身,除了可以带粮食及沙煲、锅、铲等物件外,任何东西不准带出去。这叫做扫地出屋。离开后农会便在地主的每一户门上贴上封条。
接着是分胜利果实。胜利果实都放在小学校里。地主家里的好东西可多了,都搬到学校里去分类编号摆放。大件的如床、柜等物件放在楼下礼堂里;桌、凳、藤椅还有红木桑枝的茶几沙发等东西摆放在礼堂左右两侧的两个教室里;衣服、布匹、鞋帽等细软物件放在楼上的一个教室里;棉被、毡子、蚊帐又放在另一个教室里。此外,还有一些铜壶炉、铁板盖、铝水煲等东西也放在一个教室里。这些东西分了三天。分了的东西都写上名字,贴上红纸条,放在另一边。学校里每天都好象赶集那样人山人海,闹闹嚷嚷。最穷的雇农先分,抽签后唱名,先唱先分。易凌胜是农会长,他理应照顾先分。先分大件的,他要了一张雕花镀金的大木床,一张龙凤贵妃沙发椅和配套茶几。民兵吴六要了一张弹簧床。只见他咚的一声跳起来坐到那床上去,立刻便被弹了起来。旁边的周七见了,讪他日后小心腰疼,说夜晚干那事时别叫婆娘蹦着压坏了腰骨,那快活的样子引得周围的人都笑了。
地主家里搜到的胜利果实中,也还有一些金银首饰及手表钢笔等物件。不过,那些东西另作登记,内部处理,贫雇农们是没有人去过问的。但也有个名叫“大将”的民兵,生得五大三粗。他负责胜利果实的放哨保卫工作。只见他头戴着五角帽子,身穿从胜利果实中拿来的略显得长阔一些的中山装,卷起衣袖的左右手各带着一只手表,胸前别着两支钢笔,威风凛凛的在楼上楼下走来走去。他还不会看钟点,但却不时抬手看表。倘若有人问他:“大将,几点钟啦?”他就会举起另一只手到你眼前神气地说:“你看!”。这种大干部的派头引来了许多大姑娘的羡慕的目光。
分完了胜利果实后就分房屋。贫雇农凡是缺屋住的,都可以分到房屋。缺得多的,住地主老财的新屋;缺得少的,分完地主的新屋后再调整。十五户地主的屋子都封出来,共有八座大新屋,两座中型的合面楼,还有一些老房屋,合起来共八百多个房间。全村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