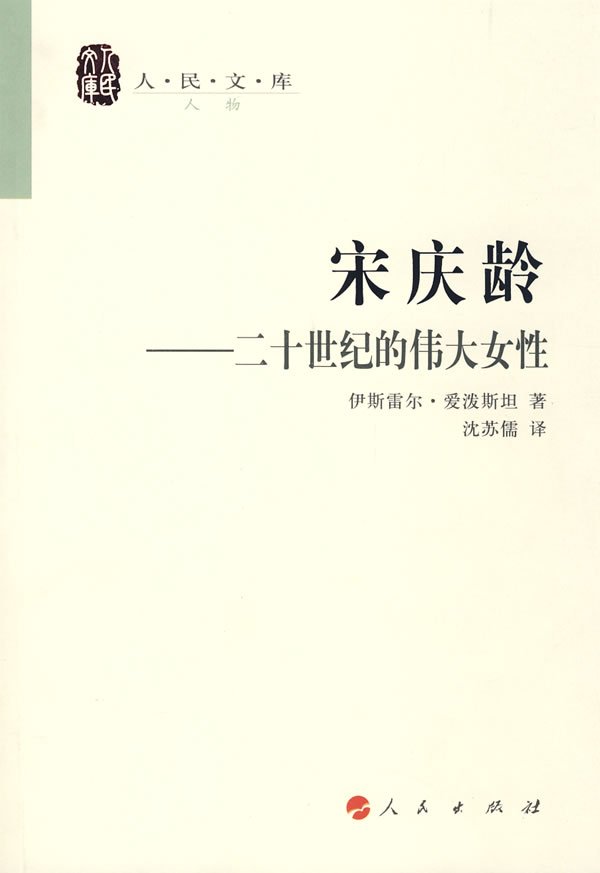世纪烟云-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龟弟,你做的好事!”
吼声响处,两支电筒从暗处前后照了过来,接物件的人被逮个正着,人赃俱获。原来易凌胜与人合谋偷老板的布匹。一个在楼上吊下来,一个在楼下接,出手后就两人均分。接赃的是隔离邻店煮食的伙计周友伦。易凌胜把几次分得的赃款都拿去赌了。当晚,周仕贵找人来见证,并要易凌胜立下赔偿字据。后来,易凌胜回家去把祖屋卖了才算完了此事。
这易凌胜到了此时,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没办法,只得向叔父借了间烂瓦屋栖身。叔父易天华是地道农民,靠包耕过日。易天禄发财的时候,他曾向他借钱买了两头水牛。现在看见侄儿破落,虽不知个中详情,却也知道他不守本分。便劝他不如暂且学叔父包耕,虽是辛苦,却能养活妻儿老小。自此,他把一头牛分给了易凌胜,便教他打起牛屁股来。易凌胜到了此时,儿子待哺,老婆生病,母亲又过世,生计无着,真是英雄气短。想到自己败家,如水漏堤崩,自是后悔不已。在叔父呵促下,终于卷起裤脚,拿起了牛鞭子,在泥田里吆喝起来。
这日子才过了没一年,忽然平地一声惊雷,世道变了。当许多人还在梦中的时候,易凌胜却醒得最早。那年,先是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演出《白毛女》,有许多人高呼“打倒地主阶级!”,他就知道早年在城里时听人说山那边斗地主分田地的日子快到了。不久,土改队进村了,有钱人发慌了。当土改队长侯叻在贫雇农代表会上口干舌燥地作完斗地主的动员讲话后,易凌胜第一个就站了起来。他先是通通鼻窍,习惯地把鼻子“吼吼”两下,然后尖声阴气的说道:
“今天穷人要翻身,就要打倒地主老财,不能让他们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侯队长讲的话句句在理。我们贫雇农要团结起来,大胆斗争地主。我先报名斗周仕贵。他逼我承认偷布,害我在老婆坐月子的时候卖屋弃家,弄得我老婆生病,母亲气死,真是家破人亡!”说到最后,易凌胜的声音也变得嘶哑起来,他伤心的样子令侯队长感到十分同情。侯队长也象演戏喊口号那样激动地站起来,举起右手:
“打倒地主阶级!”
接着便有几个人站起来的,都说了与那些有钱人的深仇大恨。有的是见死不救不肯借钱的,有的是放高息盘剥农民的,还有的是低价买穷人土地的,更有一些田界屋界纠纷中倚势欺人的等等,侯队长都一一记了下来。那天的贫雇农代表会议第一个任务是排查村里的斗争对象,划清阶级阵线。在易凌胜带头下,进行得十分顺利,侯队长对他十分赏识。接着便是选农会会长。这农会会长负责组织农民斗地主、分财产等大事,要有觉悟有胆识的人来担当。通过侯队长提议,大家举手表决,一致选举了易凌胜。
农会会长要在村上办公。就在岭脚下的文祠庙里,走进大门后转右弯,第一间耳房就是农会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张藤椅、几张凳子和一张办公台,台上放着一部手摇电话机。上级有什么指示,铃声一响,很快就能听到。农会办公室的隔壁就是土改队的办公室。侯队长要落乡,有电话时农会就派人通知。易凌胜被选为农会会长后,第二天就到农会办公室去上任。他戴着一顶五角星的帽子,坐在藤椅上,等待几个贫农组长来开会。现在这村里,除了土改队长,就要算他是话事的人了。村长是三代贫农易天华,是他的叔父,土改组长侯叻就住在他家里。叔父肚里没有墨水,开会讲话还要流口水,事事还得靠他。他们两人掌管着村上地主老财的生杀大权。那些往日神气十足的老爷们,现在见到他都点头哈腰起来了。真是三日河东,三日河西,想不到乞丐也会变大公的。他想,到那天见了周仕贵后,要告诉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我现在是水鬼子升做阎王爷啦!”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嘿嘿地笑了。
贫雇农组长开会研究了一天,第一批要划地主成分的就基本确定下来了。其中最大的老财是周伯年。他在城里又开铁机布厂,做布匹生意,还开金铺。仅这布匹中的“徐昌士林”,就以颜色耐新和布质坚固出了名,远销省内外。家里土地也有十多亩,常年雇请长工耕作。自土改风声一来,长工们都走了。现在偌大一座新屋只空荡荡他一家人住着。周伯年六十多岁了,有一妻三妾,生育共四女一男。大的两个女儿都嫁了,听说其中有一个还在念书时候就参加学生运动,后来不知到哪儿去了,现在在外面工作,一个小女儿还在读书。儿子周树和三十多岁,在城里管着许多生意,是行十万坐十万的人物。周伯年经商出身,早年在印尼开钨矿,后来钨矿生意卖给了美国人,改在香港经营布业,一向为人宽厚,村中没有得罪谁人,就是长工也没有谁肯出来揭发他什么的;周树和是城里商界头目,很少在家。但对乡梓教育却很关心,出资创办育才小学校,村里父老众口皆碑。贫雇农组长们讨论了一日,定了五个要斗争的地主,周伯年不属斗争的对象,可是,侯队长最后总结时说地主阶级的善良都是伪装的,本质就是剥削。大家之所以对某些地主还揭不出来是因为受了一些表面现象所蒙蔽,是阶级觉悟不高的表现。考虑到工作的逐步深入,第一批斗争时,大财主周伯年可以拉上去作陪斗,以后再搜集材料。他的身家大半还在城里,这样,还可以促他出钱赎罪,增加胜利果实。
易凌胜负责通知周伯年到那天不准外出,要到小学校操场去参加斗争大会。这天午饭后,他戴正了五角帽子,穿了一身干净衣服,到周伯年住的大新屋福源楼去。
砰砰!砰砰!
吆喝加敲门,里面传出了狗吠声。好大一阵后,才有人出来开门。
易凌胜本来有点恼火。今天我农会长驾临,还不早早开门,你地主阶级摆什么臭架子!他本想踢开门进去训他妈的几下子。但一会儿就门开了,随着“谁呀!”娇滴滴的声音,他看到了一个身穿唐装大红花绸旗袍梳长辫子的漂亮女人开门出来。便立即两个眼睛瞪大,嘴巴张开,一时竟不知要说什么了。
“干部同志,请问有什么事吗?”女人问。
“呵,有!我是农会会长,通、通知你家周伯年后天九点钟到、到小学校开、开斗争大会!”易会长醒过神来,记起了来这里的任务。但他竟口吃起来。讲完话后,鼻孔又象被两块鼻屎堵住了似的,他立即“吼吼”了两下鼻子。
“同志请到屋里坐吧。”
易凌胜身不由己踏进了这座大屋。这是中西结合的客家式洋楼。有两层回龙。三厅五进四翼。正中第三进后就是两层的水泥建筑的洋楼。洋楼后面是花园。易会长被带到洋楼的客厅里。那里有几个女人见有客来到,便马上站了起来。他象一个大干部光临那样,坐到大师椅上去,翘起二郎腿,对几个女人扫了一眼道:
“周伯年在吗?”
“他身体有点不舒服,这几天伤风咳嗽,躺在床上休息。请问同志有什么事吗?”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必恭必敬地说。
“你听着,后天要开斗争地主大会。我农会和土改队正式通知周伯年九点钟准时到会,不得有误!”易凌胜阴着嗓子呵斥般地说道。
这女人唯唯是听。屋里的几个婆娘,有拿烟的有敬茶的,恍如敬老爹似的。易凌胜看到这些如花似玉的女人们,心想,再过不久这些地主们就要扫地出屋,穷人们就是这里的主人,这些凤凰就都要变成乌鸡了。他有点可怜起她们来了;又想,我现在上无片瓦,下无锥地,又是农会长,必定要分到这屋子中最好的房子来,过一过神仙般的日子。想到这里,他不禁走出厅去,背着两手,踱着慢步观察起来。
左边厢,小花园的一块空地上,那个穿旗袍的女人正在晾晒衣服。那双玉手在晨曦下象两只小白兔般的上下跳跃,一条长长的辫子一直垂到浑圆的屁股上。只见她忽然拎转身来,掂起脚尖,两手往上攀拿着竹篙上的衣服,易凌胜站在一边看呆了。他看到了那出水芙蓉一般的脸蛋,看到那由于两手往上攀举而挺起来好象就要撑破衣衫的高耸的乳峰,竟下意识的“哇”了一声。冷不防一只大黄狗扑了过来,吓得他赶快后退,不小心脚下一滑,跌了个仰面朝天。幸得主人赶快把狗喝住了。他连忙爬起来,一边扑打衣服,一边悻悻地向外走去。周伯年一家连连赔不是。
回到农会办公室,易凌胜呆呆地把那女人想了一天。原来,这女人叫陈兰英,是周伯年的儿媳妇,周树和的妻子。她是县府财政局陈集宏的女儿,今年二十七八岁了,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却仍是十分美丽。玉白的肌肤,鹅蛋形的脸膛,丰满而高挑的身材,加上一条又长又大的辫子,浑身都透发着青春而又成熟的气息。她原是跟着丈夫住在城里的,但这些时间来,城里生意不好做,金铺关门,布厂也少了许多销路,家公周伯年又身体欠安,丈夫便叫她回家来多加关照。她虽是大家闺秀,但为人却很随和,现在家里的长工们都走了,便做些扫地洗衣服的事情,还要照管油盐柴米等许多家务。现在她见农会来人通知要老人家去开斗争地主大会,不禁十分担心起来。
“爹,你看是不是叫树和回来商量一下?”兰英问道。
“这老爹又是头晕又是心乱,前些天还有点发烧,万万去不得开斗争会!”太太担心地说。
“叫树和回来跟工作组讲讲情吧!”二妈说。
“不行!这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树和不能去讲情,讲了也无用,不能叫他回来。”周伯年心知躲不开这一场风暴,他坐在椅上显得有些激动。
“要不,我去跟他们说一说行吗?”兰英仍然担心地说。
“更加不行!你们不要瞎操心了,唉,没用的;这是世道变化!”周伯年坦然地说道。
“他们需要的是钱,听我兄弟说,隔邻新塘村的药铺老板钟启龙有病卧床,出了三千银免了一场斗。”二妈又说。
面对这世道的变化,有钱人家真是忧心忡忡。当灾难终于降临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听天由命,因为这是时代的车轮,是无法抗拒的,但却都希望有什么办法能使这种灾难尽量减轻一些。
“要不,找今天来的农会长说说情行吗?”三妈说。
“不熟不识,可怎样说情呢?”兰英问。
“有道是‘鸡腿打得牙窖软!’我们托三叔公送点东西去试一试吧”。
溺水的人在挣扎时候是没有选择的,哪怕是一根稻草,也会抓住。陈兰英她们几个女人没有出门,不知道外面的形势变得怎么样,只听到说斗地主时那些穷人对地主拳打脚踢,很是可怕,并且知道现在是农会话事,谁是地主并且哪个要斗是靠农会去定的,便拜托堂叔公周伯宏带点东西去农会长易凌胜处说说情。
易凌胜收下了周伯宏转交来的两瓶人参补酒,两盒中秋月饼,一块金砖,两只金戒指。他知道这次本来就不斗争周伯年的,便卖了个人情,对周伯宏道:
“我先答应你,不斗争周伯年可以,但有些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还得跟土改组研究研究。不过,我看土改组最少也得叫周伯年出来陪陪斗。”
“总之多靠胜大哥周旋一下,伯年的确有病,也愿意出钱!日后还会多谢你的。”
周伯宏是村里做中人的,易凌胜卖田卖屋的时候曾与他打过交道。但时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也。以前是我要托他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