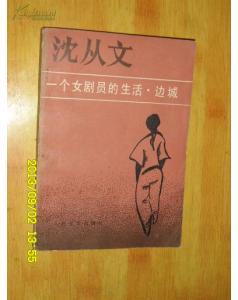特殊人群的生活方式-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立之后,我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因为没有人知道我过去的经历。
几个月后,北仑突然又新开起了一家专业洗衣店,店名叫“华蓉干洗店”,就在D娱乐城的旁边,老板就是我。自从和项华分手后,我就走出了娱乐城,除了边读书外,又用自己的积蓄,花了六万多元开起了这家干洗店,店的名字就是我特意用两个人的名字合起来的。因为我的心里始终没有放下他的影子:我常常独自骑车到十几里外,去他单位的门口,站在路的另一边的远处,久久地看着他进出于单位的大门,却不敢走近跟他说一句话。有时候我也借个车子久久地尾随在他下班的车子的后面,直到他回到家中。
店的地址也是我特意选在那里的,我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我是一个有出息的小姐。尽管这样,旁边的所有人还是不知道,我就是曾经在D舞厅上过班的坐台小姐。有时候人们会问我以前在哪个单位上班,我会刻意地告诉他说:“我曾是坐台的!”人家都会以为我在开玩笑而不信!从人们的眼光中,我看出他们对我能力和勤奋的认定。自从我在D娱乐城附近的洗衣店开起来后,舞厅里那些平时懒得像虫一样的小姐们都就近把自己的衣服全拿到了我的店里来洗。当看到我已经做了老板时,她们一个个都用羡慕的口气向我问这问那。我在耐心回答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劝姐妹们也要争取早日走出那个职业,用积蓄的钱去开创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就这样,很快就有一些小姐们学我的样子,离开了灯红酒绿的舞厅,作出了人生的另外选择,后来有一些居然也事业有成。一个人照顾店是忙不过来的,于是我又叫了一个帮手,并将自己的母亲从安徽接过来一起管店,这样我就有了多余的时间。我又去买了一辆二手小车自己开着跑生意。由于办不下来营运证,在稍微挣了些钱后我就把车子卖了。然后,我又寻思着去找一份另外的工作来充实自己的时间。这个时候,我要找一份工作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因为我已有了文凭,有了几年的驾驶证,有了电脑的中级证书,还在自学英语,所以我很快被一家大宾馆招去做客房部的管理工作。
这时已经是到了2001年了,我的店因为母亲身体吃不消而承包给了别人,一年只拿些现成的承包费,但不用自己费心管理。这些年,我弟弟的病也在慢慢往好的方向发展,虽然还得不时地吃些药,但毕竟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弟弟几千元一月的高额工资也能在应付药费后剩下些许。我自己的收入也相对稳定。我还是像以前一样,除了生活中必用的,我仍然不浪费一分钱。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给弟弟和自己洗衣做饭,再剩下的时间就是看看书。在情感上我一直是空白的,对于感情好像再也提不起兴趣。这样平静而安详的日子我们姐弟是相对知足的,尤其是在家乡人和父母亲眼里更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是一对很有出息的姐弟了。但我的内心深处,总觉得有种深深的压抑和孤独,我从不愿意和外人谈起自己的过去,因为我并不喜欢和人接触。那些外人所不知道的很多故事,在我的心里时时地浮现。尤其是在情感两次受挫后,我觉得自己之所以在人们眼里是个好女孩,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我的故事,不知道我曾被人卖过,不知道我是个有着9岁女儿的母亲,也不知道我做过小姐,更不知道我和有妇之夫有过瓜葛……我总是想,要是这一切都让他们知道了,那又是一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的内心深处,是多么想让人们了解自己,同时也能懂得自己啊!
渴望倾诉,我勇敢地走进《半边天》,电视里和现实中的我都在默默流泪
如果我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下去,也许我的生活又会是另一番情景。但是更好还是更坏呢?这谁也无法去肯定。
2001年3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我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一边漫无目的地用遥控器搜索着电视频道。忽然,中央电视台第一套的一个栏目锁住了我的目光———《半边天》!首先“半边天”这三个字本身对我就有吸引力,因为我一直都在以自身的遭遇和经历思索着当今女性这个问题,所以我把那个节目一直看完。可以说节目内的故事本身对我没有什么感染,因为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受害者单一的故事。不是我没有同情心,只是当时更在意那个主持人———张越!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电视上,我没有见过那么胖的女性,但是我觉得张越那张胖胖的脸上却有着一种真诚,那是一种自然的、毫不做作的真诚,一种对节目对职业的真诚,更是对女性的真诚!我特喜欢张越那种胖乎乎的真诚!人一旦有了真诚就会得到别人的信任,我就是对张越有了那种信任,才想打电话给她的,我只想在这个真诚的大姐面前倾诉自己的一切。
我拨通了《半边天》栏目组的电话,接电话的是节目组的策划人王峻,我直接就说找张越谈故事。王峻告诉我张越人在深圳,而且她最近非常忙,他问我是不是也可以跟他说说。我犹豫了片刻后告诉他:“我想和你们说说我一个女伴儿的故事!”说完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把自己的事说成是女伴儿的事了。也许因为对方是一个男性而让我有所顾虑吧?待到我断断续续很机械地讲完自己故事时,我听到电话那头一个很肯定的声音:“这不是你女伴的故事,这是你自己的故事!”我久久地沉默了,我除了吃惊于策划人的细心外,就是对自己说出后的后悔和担心,我不知道自己这样说出了好还是不好。后来王峻告诉我:我的故事对他们节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他还问我,是不是愿意上镜做成这个节目?对于上镜,我还没有考虑过,因为我最初的目的是想找个人倾诉,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经历会是《半边天》的极好题材。于是我请求策划人让我考虑一下再给他答复。经过了整整一天一夜的考虑,我终于下决心同意拍这个节目。我就这样以山里人特有的愚痴,以这种方式告诉所有认识我的人,告诉他们我是谁,我想知道人们有没有勇气接受生活的真相!我就这样为了解脱而这样说了!在张越她们到来之前,我把自己要做节目的事告诉了弟弟。弟弟一直以来,对于我要做的事都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他是最懂得尊重我的乖弟弟。可这次他却沉沉地叹了口气说:“日子总算安稳些了,你这样一来,又会掀起不大不小的风浪了!”我听了,很久都说不出话来。
张越的节目摄制组在最快的时间里赶到了宁波。开拍前,策划人还对我说:“以后节目播出了。对你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你可以有一些保护措施,比如假名、背对镜头、逆光拍摄等等。”我坦然地告诉他们不必,我将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这就是后来张越文章中的那个“忧郁而坚定”的我!片子的题目就叫《我这十年》,2001年5月30日,它在预期的时间里播出了,我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节目中的自己面对全国亿万观众缓缓地诉说着十年来的故事。电视里的我在掉泪,现实里的我也随着流泪!那个片子,我后来再也不愿意去看第二遍。
公开自己的过去何罪之有,现实生活中我为何左右碰壁 第二天,我在上班时,一个走进宾馆的客人看到了我,马上很惊讶地说:“你不是昨晚电视里的那个人吗?怎么?做过小姐的人还能来这里工作啊?你受得了吗?”那人的声音并不大,可是刺耳的语气却在我的耳里犹如声声炸雷,震得我差点晕过去。6月6日,老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明白的理由,最后就让我去领工资走人。面对老总的决定,我没有多说多问一句话,默默地离开了单位。六天,这就是节目播出后六天里的变化,六天里,有不少来自周围朋友和熟人的鄙夷的目光和言辞。我如此透明地把不可言说的过去,完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同时,也毁坏了旁人眼中那曾是“清纯可爱”的好女孩形象。当时曾追求我的几个男孩子发来邮件说:谁也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复杂的你!曾经热心为我做媒的熟人,也一个个无声地消失了。走在路上,时不时地有些长长的手指在点着我的脊背,说着我可想而知的话。这就是现实给我的打击。节目播出后,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来电几千个:有赞叹我勇气的,有鼓励我好好生活的,还有一些男士们是来向我表示爱慕的。更多的是一些同病相怜的女孩子挣扎在生命边缘,她们打来电话一次次地感谢我,说是我的精神鼓舞了她们,使她们有了信心去面对自己将来的生活,还说我是她们的榜样!还有一些作家和出版社来信要求写我的故事。与活生生的现实相比,这些多少能给我一点安慰。最让我挂念的是那些和我差不多经历但又处于迷茫中的女性们,她们大多和我差不多大的年纪,我一个个地回电话给她们,不惜长途话费认真地和她们倾心交谈着,对方往往都会在感激和敬佩中结束电话。但是现实又是严厉而残酷的:我的节目在央视播出后,我又被浙江、宁波等地的媒体争相采访并报道着,同时我这个人也被身边的每一个人在每天里议论着。我不敢出门,也不敢上网,只要一上到当地我平时常去的网上论坛时,就会看到熟悉的网友们在发些恶意的帖子摧残着我的灵魂:说为什么许芙蓉会为了出名而不惜把自己龌龊的一面展现给观众?以这样的方式去出名还不如去裸奔呢!……
没了工作,我苦苦地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给我带来的精神折磨!好不容易,宁波市一家网络公司的老总要我到他的公司去上班,可是当宁波市政府里的人知道后,竟然亲自出面阻止了。理由是简单的一句话:“这样的人不能要!”(因那个网络公司是市政府直属单位。)这更让到了崩溃边缘的我雪上加霜!我在家里昏昏沉沉地睡了几天,在一次醉蒙蒙中又一次拿起了自杀的小刀!在我将要划向手腕的那一刻,脑子里突然浮现了女儿可怜的小身影、病弱的弟弟、不再年轻的父母双亲,还有那些盼着继续和自己交流的同命运的姐妹们。耳边一个声音在响着:你这么懦弱,还用什么去给那些同命运的女性们以精神的抚慰?你这么去了,何以对得起你的亲人?
从绝望中醒来,我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父亲在电话中说:“女儿,我们能看到在外十几年中一个真实的你,这就足够了。我们除了心疼你,对你没有一点异议,以后的路还靠你自己走好!”绍兴那个孩子的父亲看到片子后也打来电话,仍是一贯实实在在的话:“无论你做什么事,我都不会取笑你的!”我又开始上网了,我用的网名分别是“叶落城市”和“宁静”。“叶落城市”意指自己有如一片飘在城市里的叶子,没有根,不知道将继续飘向哪里。
而“宁静”则表明自己宁静的心态。
我慢慢开始东奔西走为自己找工作,可是一直都不能落实,直到一年后的今年,我昔日的一位忘年交棋友找到了我。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总,他告诉我他公司里正缺人手,要我去他公司帮他做事。尽管他是我多年的朋友了,但是他并不知晓我以前的一切,而且从他的口气中,我看出他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