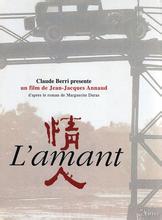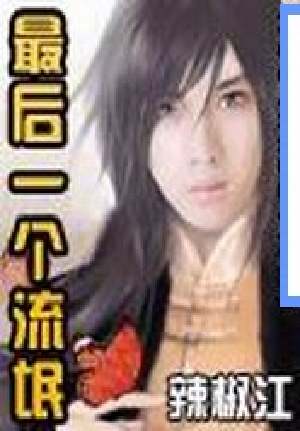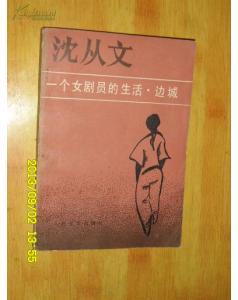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实,许多人记日记,并没有考虑得那么多,更不会都是为了成为作家。自己将来即使不能据此写出一部小说,一篇有意义的文章,还可以写些片断、琐记,写三言两语的话,虽断头缺尾,或拥肿,或干瘪,因为是真实的是心里掏出来的话,便是有用的,至少可以提供给别人去创作。总之,只要我不懈地努力,只要我比周围的人更艰苦地攀登,绝不会是白费劲的。我的行动本身就有意义,正如我曾经做过的种种追求理想的努力,虽是失败,并无后悔,还因为能顽强拼搏而感到心里踏实,感到活得有意义。
对未来我始终存有一线希望,想必会一年比一年好,这也是我感到没有虚度年华的原因。我一天天地写,就觉得自己在一步步走向理想。一个人能在末路中看到光明,时刻感到一种向上的生机,觉得自己将走更远更美好的路,那么无论眼前有多大的困难也能忍受,并愿意更高地要求自己,更有勇气和信心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无论什么困难都是暂时的,唯有光明是永久的。也许命运早就安排我要走这条路,使我不致于陷入贪图个人安逸的泥坑里。
翻阅我的日记,心里有无限感慨,里面除掉一些天真幼稚,却也完整地记载着我走过的路,我对生活的感受,对事物的看法,对未来的憧憬。也记录着我的心声和遭遇到的一道道坎坷,可以代表这社会如我这类人的经历和想法。这是一些宝贵而有用的素材,我要努力使它的作用不只限于子孙们。它应该走到社会去,对别人有所启发。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要把它们整理出来。同时满足自己一种创作欲望,不至于在无聊中感到人生的毫无价值。这是一个“逍遥派”当年所能找到的最有意义的工作。
我从最早的日记开始,按时间顺序选取那些有意义的,能体现我的思想,对别人有所启发的事,抄录下来,写成文稿。可是一着手,才发觉十几本日记,要从头细看一遍,已经不下于看几部长篇小说,何况还要抄写。我每天一早伏案忙碌,午休也没有睡好,差不多工作十个小时,天天如此,坚持了近半年时间,忘了外面在“风云变幻”。我得到鼓舞,也感到疑惑。“担心”总是时时伴随着我。我曾经遭受过幻想的破灭,我又总是把希望放在“将来”这个未知数上,以“将来”为唯一目标来设计我的时间和道路,仿佛已知的已使我感到无望,就尽量要用“将来”来支撑自己。虽然因此我增添了勇气,度过了难关,但它的存在于实际的可能又有多大的距离?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一位长者给我指明方向,启示真正的未来,让我的“将来”变为现实。我常常陷入茫然之中。所幸,不管我的思想怎样起伏,我的整理工作照样在进行下去,因为一旦我不从事这项工作,我就没有勇气在一些人的岐视中走过来。只要我一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没有在为日记绞尽脑汁,我便闲适起来,庸碌无为,脑子停止转动,变得空旷荒芜。于是,世俗的精虫活起来,便占据了这空出来的地盘,逐渐又孕育着自私和卑鄙。因此我坚持着这一提高精神力量的工作,就象空气和水在维持我的生命,没有它我就无法生存、无法拯救我自己。可我的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严重失眠,甚至整夜整夜睡不着。第二天写不上几段就头昏脑胀,眼花手颤,不得不停下休息一会儿,但往往没有等到脑力完全恢复,又拿起笔。到基本完成工作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垮了,不得不为看病吃药而忙碌着。一个“逍遥派”的日子就不再是轻松的了。
1968年10月,县革委会总算在吵吵嚷嚷中成立,人们期盼国家从此会安定下来,走上正轨,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而胜利者并不就此罢休,他们开始了对反对派的惩罚。我的邻居有一位青年工人,是一家工厂“红卫兵”的头头,属于不掌权的一派。一天,竟然有一队人马举着彩旗,鼓锣打鼓,热热闹闹来抄他的家。简直象一群明火执杖的强盗,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别人家中。我正在房里抄写文章。母亲惶恐地进来告诉我,“对面抄得可厉害了,连地下都挖翻,几个人逼他交出印章材料,他又硬说没有。听说下午还要来。你要小心点。”我心头一沉,难道母亲知道我在做可怕的“文字游戏”?
“文革”初破“四旧”在抄家风盛炽时候,母亲怕招惹是非,曾经叫来表弟,撬开我的箱子,把那些可能被当作“反动”的邮票,全撕下来烧掉,还把一些朋友的照片,只要是古怪一点的,或有点摩登的女孩子照片,全当“四旧”“处决”了。我回来后得知情况,为那些辛勤搜集的邮票感到万分可惜。其中有上海集邮家陈湘涛送我的一枚三分“大龙票”和一套“小龙票”,及其它一些珍爱的“国邮”,总数一千多枚。放到现在可是价值不菲,当时都付之一炬。但是我的日记本却全都安然无恙,母亲不知道那些是比邮票更危险的东西。为安全起见,当时我就把那些日记本装在一个铁箱里,偷偷埋在厨房间的地下,直到这次才拿出来。
母亲这一说,我忽然感到不安全。那些人会不会株连九族,抄起邻居的家?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万一日记本被查抄,连同抽屉里的文稿,都可能成为“反革命”的证据,连生命也难保。当年曾有一位十五岁的孩子,只因为书写一句对领袖不恭的标语,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徒刑。对无知的少年如此重罚,说明当时的司法如同孩子一样偏激,整个社会都缺乏冷静和思考。其实借助“恐惧”来制止犯罪,倒有可能使一些人因恐惧而不自觉地走向反面。向来罪犯未被揭露,还会胆小心虚,一旦败露,反而会疯狂起来,做出本来就害怕的事来。
但是,我又无论如何不能将日记本烧毁,那些是我的命根子,如同我亲生的儿子一样。为了这一事业,我忍受了无数次歧视和侮辱,付出的代价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怎能这样将它毁灭,把十几年的心血和理想一下烧去,还有这半年来的“煎熬”。考虑再三,我决定剔除日记本里含有政治色彩的内容,和文稿中明显带有政治气味的地方,以及富有刺激性的“含沙射影”,或在别人看来可能成为反动的东西,撕下来烧毁。只留下属于个人生活工作记载的文字,一旦被发现,顶多受一场批判。我相信自己是纯洁、诚实。有一点不满也是客观的,根本不属于“反动”。其实骂几声出气的不一定是死心塌地的反党人物,满口颂扬的才是更危险的家伙。可惜没人这样想,那些人头脑发热,只想听好话。
我急忙一边翻阅一边烧毁,把“政治的东西”匆匆挑出来,投进火炉里,不一会满屋里纸灰飞扬,我又赶紧扑杀纸灰,弄得满头大汗,浑身灰烬。最后把剩下的支离破碎的日记本,和残存的文稿重先埋入地下,至此才宽下心来。
回想起来,当年真有点象电影上看到的,地下党员在撤退前销毁文件的镜头。不过,电影往往一闪而过,我可是用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想不到一个“逍遥派”也有如此惊险的场面。至今还有点胆战心惊,也有点后悔,烧去的都是一些精辟的见解,有自己对社会对政治独到的观点和看法。我相信是有一定道理的,如今再也写不出来了。留下的仅仅是一具抽去灵魂的僵尸,毫无生气。
三、他们说我“里通外国”
我的文章里没有男女爱情故事,只有我自己对进步、光明和一切美的东西的追求。它带着痛苦、烦恼、不安同时来到我的生活里。在我身上交织着,使我不能超脱于“史无前例”之外。象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劫去了我所有的爱。
1968年在一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和“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呼声中,提出“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进一步深入和扩大,广大群众如同陷入战争年代的惊恐之中。全国各个城镇乡村、各个角落、街头巷尾都在流传着各种耸人听闻的“特务案”、“叛徒案”,还不时爆出冷门,诸如某某大人物被捕的“特大新闻”,令老实人摇头叹息,惊讶不已。似乎九州大地处处隐藏“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随时将破土而出。有时在不经意中,身边的某个人会一下子成为“特务”或“叛徒”,遭到批斗。有人因此公开提出“怀疑一切”,“不相信任何人”,“你可以怀疑我,我也可以怀疑你”,似乎连鸟儿从空中飞过也值得大家去怀疑。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自危不浅。
我那时因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失眠症还没有痊愈,一天睡不上三、四个小时,白天头疼心悸,全身乏力,对这场运动难免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畏惧和负担。无端害怕过去与海外通信交换邮票的事,会被当作“通敌罪”予以追查。那时只要跟“外面”稍有联系,事情就复杂了,麻烦也随之而来。我因此对周围人们的一举一动格外留神。只要稍有对我冷淡的态度,一束不信任的眼光,都令我不寒而慄。
六月初在公社搞“清队”时,倒也平安无事。目标都集中在那些“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即过去已“挂了号”的。况且我毕竟年轻,没有人想到要从我身上找碴儿。
九月份从公社又全部集中到县城里参加“清队学习班”的学习,对教师们进行封闭式的审查。我们是第二批来的,进“学习班”的当天晚上,就参加前一期“学习班”结束后召开的所谓“宽严大会”。即对“抗拒交代”的“从严”,对“坦白交代”的“从宽”。那天,当场宣布逮捕二人,另有一位中学教师骆某某上台“坦白”,说是因集邮而犯了“里通外国”的罪。我的神经一下紧张到极点,他交代的被称为“特务”的邮友中,有一名我好象跟他通过信,交换过邮票,我还仿佛记得跟这位“坦白的人”也有过邮票交换的往来。他会不会把我牵连进去?顿时我浑身颤抖不已,一颗心狂跳不止。我虽然清楚自己只是集邮,没干坏事,但一种可能被怀疑的恐惧深深扎入我的心房,使自己失去控制,失去理智。以为当场就会被押到台上去示众。那天会上就突然点了两个人的名字,说他们“隐瞒重大政历问题”,在众人的怒喝声中,被勒令上台“亮相”。我吓得差点晕了过去。
回到学习班,我食不甘味,睡不成寐,整夜翻来覆去,胡乱猜测着各种可能性,只听见心在怦怦地狂跳,手脚冷冰冰,全身没有一丝热气。但心里还是清楚这是一种病态,一种由神经衰弱引起的恐惧症,再不排除引起紧张的因素,发展下去可能变为神经分裂症。身体就彻底垮了。为了解脱自己,也为了自己的健康,我决定第二天在小组讨论会上把这件事讲清楚,不是说“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嘛!不外是那么一回事,领导常说“交代了还是好同志”,没什么可怕的。
不料,我在会上一公开。“学习班”的负责人立即重视起来,凑在一起分析道:“这是以攻为守,企图用支节的问题掩盖实质的东西,背后肯定大有文章”,“何海生在刺探我们是否掌握他的材料,没想到露出尾巴。”其实那些人都是“对敌斗争的能手”,阶级斗争的弦时刻绷得紧紧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有“敌人”,根本没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