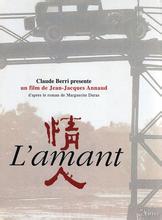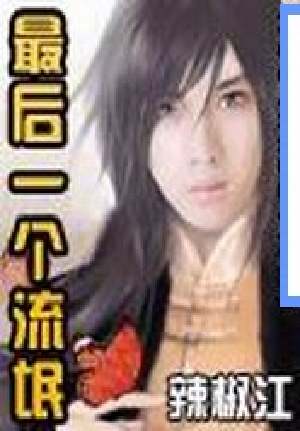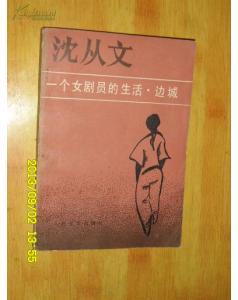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承认那时跟邻居的关系处理得不好。我这个人脾气躁,有理说理,不会拐弯抹角,更不会背后使坏。而有些人却不肯讲理,或故意不讲理,专用“泼”和“辣”来压人。我也曾想过忍耐退让,凡事有利有弊,这方面失去的,会在另一个地方得到补赏。瞎子虽看不见东西,耳朵却变得十分灵敏。世间的事原不必十分计较,暂时讨了便宜,不见得永远就好;受一点委屈,未必全部都坏。可是有时我又觉得不能太死心眼,如别人攻击的那样,是个“书呆子”,好让一些人来欺侮,不给予回击是不会叫她们住手的,还要得寸进尺,日益骄蛮起来。
可是只要我忍不住做出以牙还牙的举动,便落入她们的圈套。她们可以整天站在那里恶言秽语随意骂人,而不怕侵犯“人权”。我不能,有时态度生硬一点,象对待路中的顽石,企图一脚踢开了事,便落得个“土匪”的恶名声,还要老师长老师短地讥讽起来。两个人挤在院子里交头接耳,看见我就故意你一言我一语,跟说双簧一般,却句句冲着我。我很苦恼,生活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对她们毫无办法。一回到家里,她们便会象鬼蜮一般,在我脑子里或隐或现,我即使躲到房里去,也还听得见她们指桑骂槐的声音。
我知道,这些人每天吃饱了,没有正经的事可做,只好找些无聊的来发泄。她们除了料理家务抱孩子,一有闲空就串门,几个人聚在一起议论人家的短处。无论哪里出了新鲜事,都躲不过她们的耳朵,又特别喜欢别人的不幸,因为她们自身并不幸运,只好希望别人一样遭殃,以增强自己活下去的信心,满足内心的妒忌。企图将摆脱困境寄托在别人的灾祸上。只有到了别人一败涂地,一辈子翻不了身,才又大发“慈悲”,可怜和同情起来,说明她们不是坏心肠。这种人彼此间也常争斗,壮者一手撑腰板,一手拿指头朝对方的鼻梁数落着;矮者口角边唾沫四溅,双手如泼水般反复回敬。声调时而高亢,时而低泣。在大庭广众之下互相挖苦、取笑、辱骂、诬陷,把一切羞耻事都搬出来示众。这样的表演往往还没有在众人眼里消失,双方无须谈判言和,一方便又躲到另一方厨房里议论起他人的私事了。
目睹这一切,我实在不愿意用虚假的感情去同她们打交道。我总是默不作声高昂着头,从她们的夹缝中闯过去,有意借傲视来抬高自己的勇气或故意穿一件考究的外衣,并非为了打扮或炫耀富有,尤如穿一件救生衣,可以漂浮在世俗的浊流之上。要不,我将被她们的庸俗短见说得一文不值;或者和她们一样失去崇高的理想,放弃应做的努力;或者成为一个可怜虫,被她们不时拿来寻开心。我有时真象一只被囚禁的猛兽,被人戏弄着,挑逗着,除了怒吼几声,毫无办法。我只为母亲担心,她喜欢人家说好话,怕别人议论是非。她越是这样,越叫我放心不下,这是徒然叫自己心里不好过。我固然也感到人们眼里露出轻蔑的光,一颗逞强好胜的心全然失败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在那些人面前感到琐小。我表情忧郁,却更专心致志,想得更远。
我也明白,这远不是我应该去争斗的对象。只要事情一过去,我就把它忘却,赶紧去走自己的路,因为我的目标是那么长远。可是有的人却不肯善罢甘休,即使她已是胜利者也一样。只要在路上遇见,没等我打招呼,她便狠命往路边吐一口唾沫,以表示对我的憎恶。一般人会相应吐一口回敬,有时双方因此爆发一场“战争”。我不肯这样,虽然这一吐,可以令我感到不自在,以为自己是个坏蛋,浑身臭不可闻,值得人们来唾弃。又一想,这一吐于我的前程毫无障碍,倒是她口腔里唾液少了一点,要是整天这样吐下去,说不定会得胃病。也许当真她口里不舒服,要不时来排泄一点。总之,我不愿有任何反应,顶多在心里冷笑而已。她洋洋得意,以为将我侮辱一番又得不到报复。我也洋洋得意,没有被这一吐迫出自己的劣根性。我已知道暴怒是无益的,并将严重损伤自己的神经和健康,干扰我从事的努力。我其实有更深的憎恨,犹如地下的熔岩,不时喷发尚不可怕,还可供人观赏;唯有长年积蓄,一旦喷射,才叫人担心,毁灭性更大。她的胜利是容易的,我的胜利却不容易。
我曾想,假如有一个神经失常的人突然窜到我跟前,嘲笑我是“疯子”,那时我该怎么办?难道给他一巴掌,说他自己才是疯子。我以为这是无用的,应该写出一点感想来。吵架本身就有两种,一是用拳头和嘴巴,一是用笔和纸。用拳嘴十分痛快,能立即见效,不论输赢总是出了一口气。用笔纸有点象神仙在斗法宝,这里放出一个东西去,那边也亮出一个,于是两个怪物在空中打斗。七斗八斗,输家收起法宝逃遁,赢家收起法宝哈哈大笑。可惜我是笔尖对嘴巴,有点别扭,也不热闹。当然所有争吵,无论输赢都不会给社会带来益处。争这种闲人的气,本身就很可笑。任何指骂,死后也将同尸体一起腐烂,连子孙都不会去想念还有几分意义。只要不影响我的事业,我无需过分在意,否则便是自己胸无大志。那时离开了,倒可以省掉许多烦恼,失去的仅仅是天伦之乐罢了。看来我还应该庆幸这次调动。
汽车在东园镇停下,新校长已在那里等候,另有一位刚调入的老教师也到了,校长便带领我们出发,还要走十几里小路。
路上我提着两包行李感到有点吃力,就用绳子连结起来象一对褡裢,一前一后放在肩上,渐渐又觉得细绳子勒进肌肉里疼得难受,只好不时挪动,时而在左肩,时而换右肩,或用手托着,垫着,抱着,只要肩膀不受绳子的作孽,什么办法都用上,又都不能持久。新校长见我难受的样子,有意替我背一段路。我婉言谢绝,第一次绝不能在他们面前示弱,我相信自己能坚持到底。
路也真够长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过去,还不见校长停下来。直到前面出现一个三面临海的村庄,远远望去象一只大象鼻子撂在海面上,这下总该到了,再过去就是大海了。果然进了村子,转过几道弯,来到一间古老的祠堂面前。校长才停下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不禁倒抽一口气,亏县文教科想得出,这涯崎小学可真是“天边海角”呀!
休息片刻,路上的疲劳逐渐消失,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想到这里离家四十多华里,交通又不便,回去一趟不容易,加上没有电灯,没有影院,几个同事一张张都是陌生的脸,他们的内心更难捉摸。我对这次调动真的感到难过,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被发配到这荒凉的“边疆”来。尽管我工作一丝不苟,拼命干出成绩,只因为想报考大学,便遭如此报应,这就是现实呀!
两位教师见我闷闷不乐,热情地邀我到村里走走。村子不算大,有一条狭长的小街,两边开几爿杂货店和小饭馆。环境还清洁,男村民大多出海捕鱼和搞航海运输。只有妇女在家种田。但农业不是主要收入,许多人弃农经商到外乡当肩挑小贩。
第二天到附近的中心小学开会,听取传达上级对“教改”的指示。那些对我不成问题,“减轻学生负担,调动学习积极性,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场面”,早就是我所赞成的。传达者却列举种种思想顾虑,似乎教师都想不通,不愿意。下午是小组讨论,漫谈国内外形势。一些教师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形势大好,农民大倒”。大家反映增产不增放,一分工分几厘钱,社员对出工不感兴趣,经常聚在田头谈天说地,消磨时光。有的教师还举出不少具体例子。我看出这里有几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青人,业务水平不低。他们的话很中听,不象城里的老教师,每次政治学习都讲些客套话、时髦话、恭维话,以此表明自己安心守纪,不得罪政治,甚至讨好政治。我也以低沉的语调讲了几句,想不到还很不容易,当我准备发言,才发觉机会不是常有的,几次正要开口,已被别人抢先,我又不想在争论中发表意见,还想保持一种“城里人的矜持”。
第三天会议讨论如何“突出政治”就不那么热烈。这是大题目,众人敬而远之,一开始就互相观望。组长启发了几次,响应的只是几声冷落的咳嗽。后来一位自称“不懂”的人开了腔,他不着边际地谈了一通重要性,一点不接触实际。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组长再次“启发”,不知谁说了一声“墙上的标语字写得不错。”立即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起来。组长提醒大家“言归正传”,又都静了下去,直到休息的哨子响过,会场才又热闹起来。这样的讨论无疑在浪费时间。然而上级布置的任务,谁敢不执行?
大会结束前,党支书特地交代了晚婚节育的事,强调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对于“政治”,谁也不敢怠慢;不属“政治”便想松口气。领导大概已觉察到这种偏向,只好事事套上“政治”标签。尽管如此,大家心里明白,口上喊“政治”,行动仍当儿戏。这就是“突出政治”的后果。
开学几天,学生三三两两来到学校注册,他们随便闯进办公室,把假期作业和学生手册往我桌上一扔,说声“注册”就毫不客气地盯着我。有几个围在我背后,一边看我检查作业,一边大声议论。对这些热情而不懂礼貌的孩子,我感到很不习惯,但我尽量要做到初次见面就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后来我觉得这样围观闷得慌,提议到教室去。他们“轰”地一下跑开了,两位不愿走的老跟在我身边。
教室里几位学生正围坐在课桌上玩扑克。见我进来慌忙跑回自己的座位去。有一个仍坐在上面不动。我声称要点名,他只好下来了。我提醒大家点到名字的要站起来用普通话回答一声“到”。前面的都规规矩矩照办,后面有一位故意用本地话回答,引起一场哄笑。我不理会,又庄重地叫第二遍,他才改用普通话回答。女学生真怪,挤在一起,低着头不吱声,叫她们也不回应,一时拿她们没办法,比顽皮的男孩子更叫人纳闷。
正式上课,学生都到齐了,一共四十七位。他们对我没有戒心,这很好。但对我的讲课,好象总感到不够瘾。大概他们正对我抱着极大的期望,希望我会是他们理想中的一个。课堂上两位学生乘我在黑板上板书,竟然打起来。这可是我第一次碰到。下课后我严厉地叫他们来说明原由,其中一位非但不来,还扬言“老子就是不去”。我发了一点脾气,但没有用,我还没有在他们当中建立威信,他们并不理解我的话可能带给他们的好处。他们相信的还是我对他们的态度。看来,想教育他们首先必须使他们认识到我是他们的朋友。我感到有点难办,一开始就这么棘手,难道乡下的孩子不好教!
这里的学生对劳动很在行,也比较自觉。每逢劳动课我不用多指点,更不必强制,他们会干得很出色,只有在争吵时,才需要去调解。大自然的课堂比起令学生感到沉闷的教室,更有利师生关系的融洽。后来正是通过几次课外劳动,学生才对我亲热起来。
有一次搞勤工俭学去海边挖鸭嘴蛤(俗称,公玳)。一路上学生争着给我讲海里各种生物的名称,教我如何捕章鱼,捉蟹子要注意什么,哪儿可捉到青海鳗等等。还讲了不少从长辈那里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