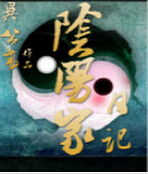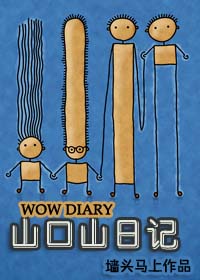莫非日记-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扑哧”笑了,看着他一脸严肃、痛苦的表情。“你是不是睡糊涂了?我们的儿子只是得了急症,住了院,你怎么咒他死呢?”
“没错,非非,我们儿子是得了急症,先天性心脏病!住了院,然后他就死了!懂吗?”他死死地看着我,就像是一条死鱼的眼睛那么鼓胀地看着我,好像在指责是我把他杀死的!
我觉得我真的要不高兴了!我坐了起来,拉开窗纱,月亮刚好挂在窗角。
我不喜欢他这么说话,好像我们在阳间说着阴间的事儿,黑乎乎的,时间也是静态的,这一瞬间也好像是永远似的。
他非要抱着我睡觉,我就让他抱了。后来,我听见他均匀的鼾声,就轻轻掰开了他的手指。然后,坐在窗前的藤椅上看月亮。
月亮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皎洁过,像聚光灯打出来的那种效果。灯光是从玉盘下面透射出来的,而且没有泄漏到玉盘以外的任何地方。我看见了那束灯光,日光灯颜色的,就是无色、透明状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到了华山上的月光。
那一年她十七岁,第一次登山,还是华山。
北峰上光秃秃的,除了稀稀落落的几棵松树结实地盘踞在山顶的巨石缝中之外,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没有旅馆,也没有商店。灰白色的岩壁在半山腰堆出一块四四方方的空地,就像是还没有盖完的房子,三面已矗立起石墙,独独正面没有墙,当然也没有顶。屋中央有一块巨石,不规则的形状,刚好可以坐两个人。那一晚,他和她就在这里坐着。
月亮在后半夜钻进深厚的云层睡觉去了,于是,整座山黑漆漆的。月华穿透厚重的云层,遗落了一点点的光亮,于是,她就看见了他的脸庞,像玉一样光洁的脸庞。远处,在山和山交叠的地方,闪烁着如星一般点点的、暖黄色的手电筒的光。想必有人在山道上不慌不忙地赶路,灯光是游动的。看来人不多,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处。也或许只有他们一行十五人,现在,少了两个,那么,只剩下十三个人了。恐怕这十三个人也不齐整,零零散散分了几处,但都是赶往东峰——那个日出的地方。而她,走不动了,真的走不动了。
不是她体力不支,而是一件意外阻挠了她。半道上,她来了例假,疼痛像蛇一样在她身体内胡冲乱撞,每迈出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山风好像夹着冰凌打在她的脸上,她却没有东西可以遮挡。她感觉自己的脸很热,但四肢冰凉。她尽量控制着自己不发抖,但根本没有希望。她就这么心不在焉、心慌意乱中看到他的脸,这是那个黑夜中惟一让她感觉到温暖的地方。然后,她就看到了他望向山脊的幽深目光,那种浑然忘我的忧伤。她觉察到有一道闪电在这一刻击中了她的身体,就像雷电击中了大树,折断抑或燃烧,最后只落得一身枯焦的骨节在天地之间的那片空旷中木然地惊惶。她闭上了眼睛,把脸转向黑魆魆的山梁。紫烟应该就在他望见的山脊上,或者在山脊背后的某个地方。
墨蓝色的天空,以及厚重的山这一刻突然失却了分量感,轻飘飘的,和她的心脏一样找不到任何可以依附的支点,连身体的疼痛也失去了感知的功能。心慌意乱,已不仅仅是心慌意乱。失重、悬浮、飘荡、坠落……爱情在诞生的瞬间即已被判定死亡。
他察觉到了她的颤抖,把外套脱下来给她披在身上。原本,他留下来就是为了照顾掉队的她的,而他却明知道或许他会因此而抱憾终生。紫烟或许会在凶险的山道上结伴韩风,而韩风和他一样在暗恋着紫烟。这样的夜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他却没得选择地留在了她的身旁,仅仅因为他是班长。在这梦幻的时刻,他洞悉着一切,清醒到近乎疯狂。他仅剩下一件衬衣,云影下,他的脸庞和他白色的衬衣一样有着凝重的玉色。她没有动,没有反对,也没有说话。
山风呼啸着掀起她内心千层浪,而他们却像山一样静默着,静默着。山风悠扬,松涛在远处传出巨响,而她的身体,抑或内心,却是那么令人羞耻地疼痛或是肮脏,那被撕裂的子宫抽搐着……直到今天。
第二部分:烟花烫噩梦独白
1996年8月1日 晴 噩梦独白
当毁灭的力量如同黑暗一般蔓延,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在黑暗中睁大双眼。白天里我坚强地面对阳光黑子,尽量表现出从容自在。晚上,我成夜成夜坐着,冰凉的啤酒为我壮行。我要去的是通向危险和黑暗的噩梦,我用生命中的一切作为代价,包括生命。其实,我们永远不能摆脱的只是生命。我终于看清了生命,从我儿子身上。或许他的生命是有用的,他却刻意终止了自己的生命,而我无用的生命却在无限延展着。五颜六色的生活带给人视觉冲撞后的欲望已远远超出人内心的欲望,身内之物、身外之物概念的混淆致使人类失明。失明的人类要光明何用?哦,还是有一点用的,可以节省取暖的能源,节省下来的能源可以晚上用,可以留给一样失明的子孙用,毕竟资源是有限的,“没有远虑,必有近忧”,老祖宗的遗训总是那么英明!
男人的坚强都是作秀,他们根本没他们自己期望的那么坚强,就像是只纸老虎,一戳就是一个洞。当然,他们也远没有他们自己期望的那么智能,那么伟大,那么崇高,不过是一堆浊物,却妄想统治地球。现在他们连这个愿望都没有了,他们只想统治尘世这些可见的幸福,一旦这些愿望也受挫,他们就委靡不振、怨天尤人、毁誉谤世,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了他的。儿子死了,当我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发现儿子的老子也死了,至少他的魂魄已经跟着儿子走了。
我很孤独,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况。王昊每天晚上都蹲在夜市上喝酒,每次也都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回来就折腾我,好像我是他惟一的发泄途径。我根本没办法让自己清醒地面对他,否则,闻见他一身的汗气、酒味儿、烟味儿混合在一起,看见他那双红通通的像斗牛一样的眼睛,我想我会呕吐,我会神经的,我不得不把自己也灌醉。
空调里的风吹着吸干人的蚂蟥的味道,我坐在木地板上,黑着灯。音响上红红绿绿跳动的超重低音音符像一群鬼魅在舞蹈,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热闹却很凄冷。月光总是从窗角斜洒进来,总不能悬挂在窗正中央的位置。腿放在地板上很冷,黑色丝质睡裙即使有蕾丝大面积的柔软,月光下仍显得很生硬。什么时候我把头发留长了呢?居然拖到了地板上,闪着金属的光泽,和酒红色的酒杯一样,好像是一种摄影效果。墙壁、地板反射着满屋子四面八方的、原本就缠绵悱恻的欧美怀旧老歌,反射之后就愈加缠绵悱恻了。是谁断言说“人生如歌”?充其量人生如一曲评弹,聒噪得分辨不清音律。那种荡气回肠,只属于武侠小说里的英雄豪杰,比如张无忌,比如黄药师,连那洪七公也都属于乱七八糟的种类,而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一个音符,连个过门儿都算不上。唉!人生如此,也算真的太让人绝望了,连幻想都没有了!
我只是在耗日子,没有在等王昊回家,但表面上看,怎么都是在等他。那就让他这么认为吧,至少他能因此得到一点安慰,并不是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但是他又怎么可能会这么认为呢?他的心里早就认定是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他了!他整个的心装的就是这个,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我没力气跟他争论这个问题,我也很累啊!况且,他也没真的提出这个问题来与我讨论,我说什么呢?说什么不算多事呢?我干吗那么多事?有必要吗?
只要他没有醉得半死,回来时他总会带些吃的,比如凉皮什么的。我是个很贪吃的女人,除了吃,我好像也没有别的什么嗜好了,我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他了解这就是我致命的弱点,所以他总是能很轻易地就让我笑逐颜开,忽略了自己本来是要发火的。我就是憋足了力气想等他回来吵上一架的!生活实在太无聊了,只可惜想跟人吵架都找不到对手。然而,一闻见那些香喷喷的吃食,不能原谅的也原谅了,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像一头真正的猪,仅仅因为那口吃食而对主人感恩戴德了。就是这样,吃饱了睡觉会很惬意,即使他再怎么糟糕也变得可以忍受了。
真实的生活从来就是如此,开心和不开心混淆在一起,过去和未来混淆在一起,白天和黑夜混淆在一起。当然,白天和黑夜是因为那些不眠的灯光和彻夜红火的夜市、卡拉OK、酒吧才混淆的,反正是混淆了,谁也分不清了。稀里糊涂就老了,走不动了,完了,死了,不存在了。有和无的界定也只是一百多斤的有机体转换成了零点零几立方米的无机物,从本质上说,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恐惧这样的转换,好像他们不知道质量守恒定律的真正来历似的。这个世界,人们太会伪装了,装作不明白就好像可以真的不明白了,以此来为自己的私心杂念做掩护。掩护来掩护去,私心杂念还是私心杂念,仍然是那么显而易见。是人类的智力不够呢,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原本就是为了彰显呢?这世界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太多了!也不知道是真的说不清道不明呢,还是为了说不清道不明而说不清道不明呢?反正没人在乎了。从另一方面讲,现代人变得大无畏了。表面上他们害怕死亡,害怕战争,实际上却相反。他们渴望死亡,渴望战争,哪怕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最好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平淡的生活令他们疯狂,只有战争才能真正让他们情绪激昂。他们甚至不想问为什么要战争,他们只是要战争。人类的英雄主义情结从来没有真的消亡过,只是被压抑了。从那一个力战群雄的精子开始,到一个个分裂长大的细胞,人类从来就不缺乏战争的勇气和力量。已彻底占领了地球、彻底改变了地球历史的人类,什么时候变成了谦谦君子,否认自己的战斗能力了呢?就像王昊,堂堂的七尺男儿,怎么可能会成为悲伤这样一种情绪的俘虏,甘心情愿把牢底坐穿了呢?不,他只是需要这悲伤,需要它成为他的盾牌,用来回击任何他想要回击的敌人罢了,比如无聊。算了吧!人们太会为自己找借口,用以掩盖自己想堕落的愿望,我也一样。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除了工作能缓解无聊,就只有吃才能暂时让我兴奋了。所以,我总是在吃,一直在吃,不停地吃。我觉得我是那种挺没良心的人,吃了那么多,竟然不长肉,还不如一头猪呢!
儿子在的时候,满屋子都塞满了似的,现在儿子走了,满屋子还是满的,塞的是冷清。可能是空调的缘故吧。可是,关了空调,冷清就像小虫子似的爬满了皮肤,把毛孔都堵塞了。满屋子都是躁动的冷清!
往下的日子该怎么过呢?我一筹莫展。
第二部分:烟花烫无事生非
1996年8月15日 晴 无事生非
王昊说我神经病,我也觉得我是神经病,我把他赶回他父母家住去了,我也会回我父母家住一段时间,因为我要装修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