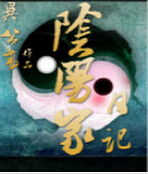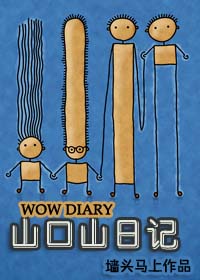莫非日记-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假的还是假的,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信任的时候,人类后悔都来不及了!这些又与我有何干呢?我都快要死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跟他说什么都是废话,他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那还说?不说了!
第一部分:割裂的子宫忧郁情人
1996年3月1日 晴 忧郁情人
所幸楼层不高,五楼,跳下去死不了,但必定残疾。这不是我想看到的。所以,每次走到窗口我就不得不抓紧点儿什么东西,因为我总是想跳下去。王昊断言:这就是忧郁症的典型症状,但我无能为力。
我总是做梦,老是梦见昆仑山口或者唐古拉山口,我不知道,我没去过,或许它们很相像,至少在梦里是这样。老是梦见山体崩塌,就像1987年夏天的华山一样,能听到黑云翻滚、山石倾泻的声音,却什么都看不见,伸出手连五指也看不见。李明清就在那堆浓雾中站着,一会儿又变成了王昊,一会儿又变成了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就这样变来变去,我根本看不清到底是谁。
阳光看起来很温暖,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很冷,冰冷。说是春天来了,但是春天并没有来,即使花开也不一定就代表着春天来了。春天应该是生机盎然的,没有生机的春天不是春天。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有一种反自然、反历史的现象正在出现,春天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还没能出现就到了夏天。就像一见钟情的人儿,突然爆发出巨大的热能,预热、慢热都不再成为这个时代的特点。就像火山,一旦爆发,就是一泻千里的熔岩。我很害怕这样的事情一再在眼前出现。我觉得我还没有进化好,还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事情,就像我比别人晚来的月经一样,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妄想跨越。所以,我等待春天,虽然春天很远,也或许,地球上再也不会有春天。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就是全部。我们只有无条件地接受全部的时间。这无限延展的时间在数学上有个符号:∝。只有在成功地跨越这个∝之后,我才能成为另外一个人。现在,我只是一个忧郁症患者。
我不想见任何人,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有我的忧郁症做伴,我不觉得孤单,相反,我很自在。我只是希望他们能让我和我的忧郁症单独做伴。她是我最忠实的情人,她了解我所有的心愿,包括我自己都不了解的心愿。她不会背弃我,那么,我也不可以背弃她,我们彼此坚贞。除了她,这个世上没有人更值得信任。
在我出生前的那个乐园,在永恒和轮回之间,在意识和潜意识的夹层,在自然的和谐中,我看到了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前世、我的来生,是那样安详地开放着,像既已消失的春天遗落的一朵山野草花,永生在时间的罅隙之间。
生命是艺术的共生体,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现?同样是泥土,有的能变成瓷器,有的能变成砖,有的是烂泥一团,有的变成了灰尘,本该是一抔黄土,怎就有了这许多不同呢?瓷器和瓷器也不相同,就像这本书绝对不是另外一本书的翻版。每个人用不同的语言符号记录自己的语言,表达一种梦幻,一种现实中因为不能实现而不得不去创造的梦幻。梦幻有多美,渴望就有多强,自焚其身的火焰就有多烈,图案就越精美。他们用生命编织借以超越生命的谎言。比如那块耐火砖:历经千锤百炼,你烈火焚烧若等闲,但是,你耐得住一滴水的侵袭吗?那一滴水,或许是你对爱情的期盼,或许是等待的烦乱。在放弃了紧张的成形之后,你是否也会,从肌肤到骨骼地化为灰粒?只有在土崩瓦解的刹那,你才肯承认内心的虚弱?
纷乱,纷乱,只有纷乱。人世间到处都是纷乱。只有我的忧郁症能让我摆脱这一切纷乱,带我走回母亲的子宫。我拒绝出生。
第一部分:割裂的子宫艺术经济
1996年3月27日 晴 艺术经济
我又开始去上班,像以前那样。我不得不集中起所有的注意力来对付这真实存在的、有关于生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些比创造更富有创造性的东西。它逼迫我更深地深入遐想,然后提取出有悖常理、超越常人想象力的新的创意,再公诸于众,成为人们必须接受、能够接受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把自己推进精神症病人的思维,抽出和要求相关的记录下来,然后再从这种病症中全身而退。这不仅需要一个人坚强的定力,更需要进入的迷醉。真正有创意的作品就是这样一种产物,迷醉状态下的病态的展现,艺术就是这样产生的。总是遇到太多不懂艺术的人在搞艺术,他们的作品就像“请认准××××商标,谨防假冒”一样拙劣,褒此贬彼好像就能够证明他们自己的珍贵。还有报刊上那些“软广告”,就像充了水的猪肉,泛滥市场。商家为自己的杰作得意,买家以为占了便宜得意。销售刺激了市场,市场又激活了经济,欲望的每个分子、每个原子都与我们结盟,鼓励我们前进,削弱实力扩张领域:绝不要把艺术看成艺术,绝不要把经济看成经济。艺术是经济的一部分,经济统治全世界!
我的创意是有标价的!创意的艺术成分和经济数字的多少有时候是成正比的,有时候成反比,这是由大众的理解力和商家的代表人物的认同程度决定的。
画出来的蝴蝶比真的蝴蝶更有价值。就是这样,在这个伟大的领域,艺术成为经济的婢女,靠主人的施舍勉强维持生计。人们愿意看画出来的蝴蝶,却恐惧旷野里的蝴蝶会落到自己身上,就像害怕耗子钻进自己的裤腿。
当艺术家的创作欲过去了,就只剩下表现欲。绚丽的色彩,娴熟的技法,大同小异的布局,千篇一律的主题。就像咬着自己的尾巴狂转圈儿的狗,好像这样就能证明自己是运动的、前进的、具有能量的。
总是能够顺利得到举手表决通过的我的奇思妙想,从另一方面来讲,是我神经质的异想天开为我一次又一次获得了经济利益,这一次,它又成功了。几乎不需要深思熟虑,也不需要费尽心机,只需要闭上眼睛就可以得到,轻而易举。只有像我这样不切实际的臆想症患者才能做到。经济就是这样和脱离经济的幻想挂了钩,达到了它合二为一的目的。完全虚幻的工作和完全真实的生活完美地契合在一起,就像一曲华彩的乐章,不和谐地拨奏出和谐的乐曲。
我从来不能一气呵成一页以上的文章,总是一句、一句不连贯地摆在那里,七零八落的。恰好策划正需要这样的七零八落、不合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成功地利用了自己混乱的思维、个人的弱点作为自己谋生的工具。从这一点上讲,我是成功的,也是伟大的,虽然我知道我不是伟人,我也从来不想为自己不是伟人辩解。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伟人。我也没有伟人那样一种神性物质的神性思维,更不会有伟人的伟大创举,我根本没那样的能力,甚至体力也不允许。偶尔也会赞扬自己伟大,那不过是为了安慰自己的平庸,实在没有什么深意。日记不应该被算做文章之列,无论从哪方面讲,日记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或不怎么真实但还算真实的生活的记录。但,即使是情绪的发泄,只有面对日记,我才能说出我想说的,它比我最好的朋友还要亲密。但是,我不愿引诱自己深想的、回忆的,我仍旧不会去深想、回忆、记录。有时候感觉自己是个收破烂专家,就像那些用旧的东西仍旧不舍得丢弃,装了箱存放在床底,沉了灰,蜘蛛结了网,仍在那里。我的日记就像是那些破烂儿,发生的、想到的,以及偶然的、必然的,统统堆在那里,乱糟糟一团,没有秩序。我的日记和我的性格高度统一,高度失序。窗外谁家小崽子在弹钢琴,弹得乱七八糟的,一个1 2 3 4 5 6 7也弹不整齐,调不成调,曲不成曲,跟我小时候一样没出息。长大后,想必也会和我一样,连日记也写不到一块儿的。
四个月没上班,他们说我还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变化。只有我自己知道,变化太大了!割裂了子宫,还几乎失忆。虽然这一切终于成为过去,毕竟在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加上过去的过去、即将过去的过去,一一运作起来,联手使生活日趋下沉,无法阻止地下沉下去。不管怎么说,我坚强的生命力总是能够抗拒死亡的诱惑,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生活还是生活,不可抗拒的究其根本还是生活。反抗有什么用呢?只要生命还存在着,只要构成生命的蛋白质还存在着,变革就根本不可能会发生。
第一部分:割裂的子宫愚人自愚
1996年4月1日 晴 愚人自愚
从早晨到现在接到的恶作剧一起连着一起,大到国家,小到天气,招招新鲜得出奇,可惜这些把戏都是我玩剩下的,总不至于要我蒙上眼睛去寻死。只有一个怎么说都算弱智的恶作剧达到了目的,比较而言,更具智慧,生活智慧。早晨还赖在床上不起的时候,王昊已经穿好了衣服,突然指着床说,“快看,蟑螂!”吓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
我们不害怕战争,不害怕瘟疫,但我们却害怕蟑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关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儿,我们总能做到义正词严,而一只蟑螂却能在一秒钟之内摧毁人们的意志,让人们变得歇斯底里。其实就是说,只要是与自己无关的,正义是理所应当的,只要是与自己有关的,一粒沙也是大问题。正义应当遵从人道,所谓人道就是要保证每个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打什么样的幌子自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保证自己的利益。战争就是利益分配引起争议、不可调和时,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甚至同阶级之间的械斗,小到人和人、人和自己,从人类诞始至今,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相互残杀。这种战争实际上根本无关乎什么正义或者真理,正义或真理只是一面幌子,一面旗,只要旗帜不倒,战争就得延续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人类娱乐自己、消遣自己的一种方式,用以证明生命不是太过空虚以至毫无意义。你想啊,在缺少战争的国家,和平年代里,平常人的生活即使大跌大宕也无非是工作不顺心,爱情不完满,如此而已。如果连这些也顺顺当当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生命了无牵绊,飘飘然却不知愉悦,忙忙碌碌又不知所以。饥荒居然是由丰盛引起的!糖分太浓居然是苦的!他们能怎么办呢?
突然很想念朋友们,那些不知道现在在何处谋生的同学们,快乐、真诚和自由的风曾经从我们紧靠的肩缝中穿过,我们曾经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那样亲密无间、不分彼此,而后来,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找到他们想要的幸福了吗?当然,我也想到了紫烟,还有韩风。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呢?自从去年“六一”见到紫烟之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或许大家都在回避,回避一些令大家尴尬的问题,甚至我连她家的电话号码也弄丢了,忘了。弗洛伊德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忘记,因为想忘记而忘记。不管怎么说,忘了就是忘了,她没找过我,我也没有找过她,就这样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