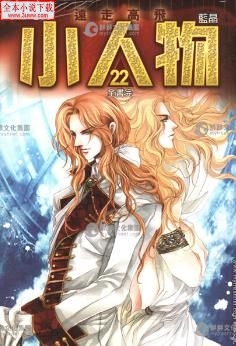小人书铺-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点钟观众上齐了,走道间卖萝卜、蹦豆的小贩和端着热毛巾的茶房穿梭来往。舞台上拉弦的开始调弄琴弦,这表明戏即将开场。小康打起精神,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因为“打泡儿”的通常是他朝思暮想的女人—;—;梅。
自打风雪之夜那意外相逢,小康像中了魔,暗暗恋慕着梅,那女人不光长得小巧玲珑,眉目清秀,一看便知道是南方女子;其次,梅从不唱落子、梆子或大戏,专唱越剧。那一口清丽婉转又字正腔圆的越剧,像汩汩泉溪滋润小康空荡荡的心田。
管弦齐鸣,戏总算开场了。司仪报戏名和演唱者,说,韵堂班的梅黛云演唱《黛玉葬花》一折。小康憋不住起劲鼓掌,可周围响应者寥寥无几。
梅出场了,一袭粉缎子旗袍箍住她窈窕的身材,娇唇微启,一曲委婉凄恻的越腔流淌而出。小康中魔了,那梅黛云的越剧声声入耳,似一股清爽之气自头顶贯入,辐射全身,顿时产生一种腾云驾雾的美妙感觉。梅唱到伤心处,他情不自禁地鼻子一酸,热乎乎的泪水滚下脸颊。
爷,擦把脸吗?身边陡然站立个打手巾把儿的茶房。
小康心里有些气,虽说他并不财迷掏小费,但这愣头儿青的茶房冲断了他的绝佳情致。
他抬起眼皮瞧瞧站身边不走的茶房,二十来岁的模样,留着青头皮,操着天津卫与山东的混合音。去去去,小康恼怒地推搡开捣乱的茶房。茶房悻悻地走开了,可小康的那股清爽之气也没了,关键是舞台上的梅唱完了,正躬身谢幕。小康赶紧鼓掌,旁若无人般地使劲拍巴掌,可惜,他的掌声被周围人们的说笑声淹没得无声无息。这之后再没有梅的戏,小康拧身站起来,朝场外走,嘴里嘟嘟囔囔骂着很难听的话,不知他骂那些观众,还是骂打手巾把儿的茶房。
走到出场口,有人替他撩帘子:爷,您慢走。小康一看是刚才被他轰走的茶房,心里头觉着有点对不住人家,谁不挣钱吃饭?哪顾得你听戏入迷不入迷。他便从口袋中摸索出金银券往茶房的手心里塞,茶房却推托着不要。小康挺纳闷,说:你嫌少?
茶房说:不是,您懂戏。爷,往后再来瞧梅黛云的玩意儿,我给您留座。
没想到,在这嘈杂的市井之地,小康竟碰到了一个知音,他也懂梅黛云的戏。小康不由得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个普通的茶房。在戏园子里呆长了,怎么也能熏出个票友来,小康想。
今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
第六章 茶房周得贵
第六章 茶房周得贵
那时戏园子的座位是一条条长板凳,没座没号,谁先到谁就占据靠前靠中间的座位。凡是茶房给熟悉的观众留座,要事先将茶碗倒扣在长凳上,那就算占好座了,等熟客一来,便坐在茶碗放的地方。
从那天后,愣头青茶房天天给小康留座,所以他就没必要每天早来,等差不多开场时,小康才慢条斯理地踱进戏园,见前三排中央的位置上倒放着一盏茶碗。
他拿起茶碗刚坐稳,愣头青茶房顺手往碗里斟满茶水,又递过手巾把,说:爷,擦把脸。
小康给他小费,他不要,说:您懂戏,俺乐意伺候您。
一来二去,小康跟这茶房混熟了,知道他叫周得贵,山东人,去年经亲戚介绍,在聚英戏园做茶房,他也挺喜欢梅的越剧。
小康有了知音,生活平添几许乐趣。他不愿欠人情,主动邀周得贵去他的小人书铺看小人书。周得贵不去,说:俺不识字,瞧不懂那玩艺儿。
小康说:不识字没关系,看画呀,小人书里头都是画。
周得贵摇摇头:您别费心了,俺在这儿白看戏多好,全是活人演的。
听他这么说,小康不再勉强。于是,他依旧天天来瞧戏,有人给他留座,义务为他服务。在这样惬意氛围中,小康天天能瞧见他暗慕的女人。
是小康娘强烈要求老康给儿子张罗说媳妇的。儿子康家会整天泡园子,听那些窑姐们唱戏,终有一天会学他爹,把家当赔给窑子,还惹一身脏病。小康娘越思越想越着急,好几宿都没合眼,老的是管不了了,再不能眼巴巴瞧着儿子遭罪。
清早起来,小康娘生着炉子,闷好火,用火筷子将门鼻儿一插,拐着小脚奔向小人书铺。
这光景正是小人书铺清闲的时候,屋子里几个孩子扎一堆看小人书,老康站屋外太阳底下望街景。冷不丁瞧见老婆一阵风似地跑了来,心中不免纳闷。
老康睥睨一眼比他矮一头的老伴说:“你撒呓挣?往小人书铺来干嘛?”
“干嘛?跟你商量正经事儿。”
“有嘛事回家再说呗。”
“你着家吗?天天离了小人书铺就往窑子里扎。要不就跟那帮狐朋狗友喝酒,家里人谁见着你的影儿。”
老康腻歪她揭自己的短,起火道:“有事说事,没事回家,少在这儿啰;嗦。”
“咱儿子的事儿,该给他说媳妇了。你没瞅他天天往落子馆跑?多会儿搞上个婊子,再后悔就晚三春了。”小康娘一本正经地说着。
今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
第七章 哪个也没看上
第七章 哪个也没看上
老康听完,不以为然地笑着,笑得声音很响:“老娘儿们说话就是悬,听两出戏就能娶家来一个窑姐?那还算福分哪。你当窑姐都是傻子,你以为咱家有钱有势,趁多少买卖?谁稀罕呢。”
小康娘挺倔,固执地说:“人家不稀罕我稀罕。再说啦,现在兵荒马乱的,共产党的军队把天津城围了个严严实实,还不知哪天得逃命。赶紧给儿子说个媳妇,我也塌了心。”
“行啊行啊,”老康有些不耐烦:“这事你做主,别在我这儿磨蹭。”
小康娘在家任何事都做不了主,今儿个终于有桩能做主的差事,心情便好了许多。
这时,小人书铺里乱成一团。
有个七八岁的孩子站门口,抹着眼泪冲老康申诉:“小狗儿非要跟我换小人书看,我不应。他把我的小人书给撕了。”
老康一听,跺脚奔进屋里。接着,里边便出现老康的吼叫和孩子的哭声。
小康娘叹口气,扭着小脚往家回。
对于父母这种拉郎配式的撮合,小康表现出超然无我的姿态。你让我见谁,我就去见,但最后一句话—;—;瞧不上眼。
一连几天,他娘请的媒婆给他说了好几个姑娘,有的是杂货铺的闺女,有的是百货店的千金,尽管媒婆将那些姑娘吹得天花乱坠,小康光给个耳朵—;—;穿皮不入内。
后来他娘拉着他硬是见了两位,在什锦斋饭庄吃了顿饭。小康竟连眼皮都不抬,带搭不理儿的,臊得人家姑娘差点没哭出来。
小康娘急了,逼问儿子看上哪位?小康挺干脆地说:哪个也没看上。
小康娘要问个究竟。小康告诉她某某是个麻子。小康娘辩解道:人家姑娘长得多标致,脸蛋就俩雀子(雀斑),哪有麻子?小康不紧不慢地说:雀子是嘛?不就是麻子吗。小康娘见小康死不吐口,就赶紧改了主意。这个不行,那个还不行吗?天底下好姑娘那么多,我就不信没有一个他看得上眼的。于是小康娘又提杂货铺掌柜的闺女:瞧人家多有钱,生出的姑娘多水灵?
小康说:哼,瘦得跟狼似的,和我凑一块儿,倒应了一句俗话:麻秆儿打狼—;—;两头害怕。说完,他瞟也不瞟他娘一眼,抬脚去了聚英戏园子。
小康娘边喊,边追出屋,早没了小康的人影。她腿一软,“噗通”一声蹲坐在马路上,顾不得站起来,眼泪簌簌往下落,心想:完啦,儿子家会算没救了。
今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
第八章 要打仗啦
第八章 要打仗啦
1948年残冬,天津卫战事紧张,解放军兵临城下,偶尔可以隐约听见郊外零星的枪炮声。市面上百业凋零人心惶惶。不少买卖家都歇了业,戏园子也因缺少观众关了门。
唯独妓院依旧艳帜高悬,生意兴隆,有钱人利用在这里发泄肉欲来冲淡内心的恐惧。聚英戏园子灯黑门闭,像关住了小康的魂儿,他整天无精打采,揣着双手,站在戏园门前,望着旧海报发呆。寒风凛冽,雪花乱飞,他不禁产生出一种幻听,仿佛门缝里断断续续飘出梅的唱曲。依然委婉凄恻,依然汩汩如泉流。伫立到黄昏,正是往时戏园散场时候,他才抱着一种满足感,拖着冻僵的身躯,踏着松软的积雪往家走。家里的饭多好,也吃不出滋味,强咽硬塞填饱肚子,闷头说声:妈,我出去遛个弯儿。便推门离开屋子。小康娘在后头喊:家会,早去早回,别遇上宵禁让当兵的抓了去。他答应一声,疾步匆匆走出大杂院。
冬日,天黑得早,大街已点上昏黄的路灯。慎益街两边摆摊卖东西的零零星星有几堆,有气无力的叫卖声在呼呼的北风尖啸里,显得时有时无。小康双手揣进棉袄的袖筒,低着头朝大兴里胡同那边走。胡同里有家“韵堂班”,“韵堂班”里有他朝思暮想的梅。这条胡同不知进进出出多少回,而“韵堂班”的门槛他一次都没敢迈进过。
铺满一层薄薄雪花的地面,已经被无数个脚印和洋车的车辙践踏得支离破碎,黝黑的胡同紧挨着一个个小院,院门前悬挂红灯的便是“窑子”,“韵堂班”的红灯又大又亮,他朝那个最亮最大的红灯奔过去。院门虚掩,淫声浪笑以及热烘烘的脂粉气一股脑儿涌出来,他刚刚探下头,便缩回脑袋,沿墙根蹲下来。
风依然无情肆虐,他竖起耳朵,力图从那些嘈杂的噪音里捕捉到梅的声音。后来他又陷入幻听,噪音逐渐消失,唯有梅在清唱……
不知过了多久,院门大开,身畔经过许多黑乎乎的影子,伴随虚情假意的寒暄,等到一切都静下来,他才站起身。他知道自己该回家了。又出来个人影,挺熟悉的。
“呦,这不是康爷吗?”
他仔细一端详,是聚英戏园的茶房周得贵:“你?”
“哦,康爷,戏园子关门了,俺没了事由,上这儿干点杂活儿。您不进去乐乐?”
“不不,我得赶紧回家。”他说着,撤身往胡同口退。“嗯……梅在里面?”
“原来康爷想见她?您来的不是时候,她这两天发烧没接客。”
他尴尬地笑笑,说:“噢噢,我顺便路过这儿。她唱得真好。”
周得贵也笑笑,说:“不光戏唱得好,人也好。对了,康爷,人家梅可总念叨您。”
他莫名其妙地连连点头:“是是,咱回头见。”然后,便逃似地奔出胡同。
今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
第九章 枉费一片好心
第九章 枉费一片好心
从周得贵嘴里知道梅发烧,小康像中了病,一宿没睡踏实。
转天一大早,他管他娘要钱,说买双棉布鞋。钱一到手,他就奔了大仁堂药铺,开上三剂清热解毒的中药,手里拎着,急慌慌奔大兴里胡同跑。
韵堂班的院门紧闭,送完嫖客的窑姐儿们正睡懒觉。小康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急得他在外面直转悠。
“吱呀”一声,院门开了,穿着黑粗布棉衣的妓院“茶壶”周得贵端着泔水桶走出来,瞧见小康愣了一下:“康爷,大清早您这是上哪儿?”
小康没开口,先臊红了脸:“我,我找你。”
周得贵不解地问:“您找我干啥?”
小康吞吞吐吐地说:“昨儿你说梅发烧,那不就把嗓子烧坏了?我顺便捎来点药,麻烦你带给她。”
周得贵躬身将泔水倒进地沟里,用棉袄袖子抹了下鼻涕,笑嘻嘻说:“康爷,您心真细,心真实,她不在……”小康赶紧追问道:“大清早的,她上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