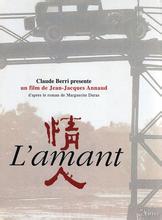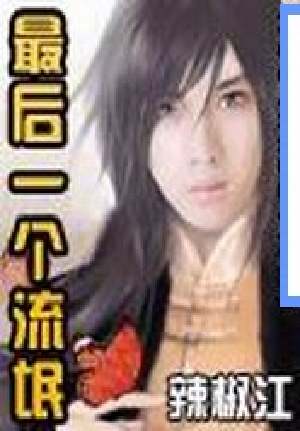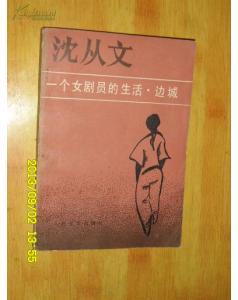一个被包养男人的沉浮史-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后他只是远远地张望,直到眼巴巴地看着那姑娘最终离去。
失去了“嫩嫩”的绿草坪变得黯然失色,他也心情黯然地往外走。出了高尔夫球场的大门,正要招手拦出租车,身上的手机忽然响了。那是钟文欣打来的,约他去富丽宾馆用晚餐,然后在那里陪她过夜。
唔,真是老天有眼,虽然拒绝了阮珊,今夜他却并没有落空。
钟文欣的梦湿漉漉的乱糟糟的,还带着一股下水道的气味儿。洪开源的哨牙和厚嘴唇就堵着她的嘴,那气味儿正从洪开源的嘴里汩汩地往外冒。钟文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似乎要窒息。
二十二岁的花瓶摆在洪开源的写字间里,二十二岁的钟文欣是公司里最漂亮的女孩儿。钟文欣刚刚被摆进总经理室的时候,总经理洪开源在她的眼里还是一个父亲般慈祥的小老头。钟文欣的任务除了接打电话收送文案什么的,再就是陪着洪开源去见见客人,吃吃饭说说话跳跳舞什么的。在此期间,洪开源并不曾对她动手动脚,至多不过是说句带点儿荤味儿的笑话,或者找个什么借口,给她额外多发几个红包罢了。
那一年的春节前夕,洪开源说是要到珠海的海花度假村与韩国的客商谈一桩生意,要钟文欣陪他同行。钟文欣有些犹豫,她原本打算春节回家与父母团聚的,再者她也有些预感,觉得此行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最终她还是去了。陪老板谈生意是公司的业务,她不应该推托。老板的计划虽然有些暧昧,不过只要自己把持得住,应该不至于出什么大格。
陪着洪开源飞到珠海,她才明白所谓生意只不过是和一位在珠海开公司的朋友见了见面吃了顿饭而已。第二天就是除夕,白天洪开源带着她转了转商场游了游景点,晚上两人就坐在露台上赏月观海。不知不觉地吃了很多瓜果喝了很多红酒,终于要睡觉了。洪开源却一把搂住她,又要把她当做零嘴儿吃。
看上去干干瘪瘪的小老头居然会有那么大的力气,他弯弯腰一挺身,就把钟文欣像布袋一样扛在了肩上。钟文欣叫喊着,求告着,洪开源仍然像得手的猎人一样兴冲冲地扛着她往大床那边走。
大床就是剥宰猎物的案台,钟文欣被甩上去,洪开源捋袖伸胳膊地动了手。
“不!不……”钟文欣尖厉地哀叫,拼命地挣扎。
那叫声就像冲锋的号角,让洪开源兴奋莫名。“哧”的一声,钟文欣的真丝T恤被撕开,露出了文胸。
洪开源的小眼珠里有灼热的亮光欣快地闪动。
钟文欣只是在事后很久才明白,这个男人要的就是女人的喊叫,要的就是女人的挣扎,要的就是那种在女人的抵抗中将其强暴的感觉。
当时她却来不及多想,她只是本能地伸出双手,在对方的脸上狠狠地抓了一把。几条殷红的血痕鼓起来,宛如充盈的活虫。
洪开源疯了,洪开源狂了,他风卷残云般撕光了钟文欣身上所有的披挂,用一种几近狰狞的凶恶扑压上来。
那一刻的感受是撕裂,钟文欣觉得她就像衣物一样被撕裂开来。她在洪开源的身下呻吟着,辗转着,痛楚和愉快奇怪地混杂在一起,就像调酒师勾兑出的一杯色泽斑驳的鸡尾酒。
那酒让她迷眩,让她沉醉,她徒费气力地拒绝着,她欲罢不能地畅饮着。她在半醒半醉之中与对方打斗不已,搏战不已。她撕抓着对方的前胸和后臀,让那些部位全都披了红挂了彩。
在搏战中,钟文欣的头被推到了床边,当她的脑袋顺着床沿坠下去的时候,洪开源亢奋到了极点。
“啊……”他大叫着,死死地扼住了钟文欣的脖子。
钟文欣几乎要窒息,天花板、吊灯、地毯、桌脚……全都在眼前倒置着,旋转着。这一刻,她沉沦到了极深处,也浮飘到了最高点。……
“喂,你醒醒,醒醒。怎么了,你怎么了?”钟文欣睁开眼,看到枕边的晓雄正晃着她。
“没什么,我做梦了。”钟文欣咽了咽唾沫,仿佛是要将残梦咽回,“我渴了,想喝水。”
“你躺着,我来。”晓雄体贴地下了床。
晓雄穿着一套都彭牌羊绒内衣,望上去柔软而熨帖,宛如闪着暗光的水獭皮。那是钟文欣为他买来的,颜色和质地与当初韩冰的那套内衣相似。嗯,这才够档次,钟文欣欣赏着眼前这个她亲手装修的男人,心底又痒痒酥酥地钻出了那种欲望。
晓雄端着水杯上了床,钟文欣没有伸手去接,只是努了努嘴。
唔,这个女人,她是要我喂她。晓雄笑了笑,由着女人靠上来,然后把水杯凑到女人唇边。
“嗯,不……”女人撒娇般地摇摇头,然后将努起的嘴“噢噢噢“地张开,做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
妈的,耍嗲呢,晓雄心里骂,脸上却乖巧着,含了一口水,嘴对嘴地喂给钟文欣喝。女人闭上眼睛,陶醉地吞咽着,脸上露出一副动情的样子。
晓雄心里又厌又腻,身子又困又乏。方才他睡得正香,却被身边这个女人闹醒了。看得出女人在做梦,嚷嚷叫叫地说着梦话,手脚也不闲着,搔搔抓抓踢踢打打。晓雄看看表,刚刚凌晨四点钟,正是睡黎明觉的好时候。于是他就伸出手,不轻不重地拍打女人的脸。原本不过是要让女人从梦里松脱一下不再弄出动静,好接着睡大觉,却不料女人睁开了眼,醒出许多麻烦来。
女人一只手将他搂定,另一只手颤颤地抚着他。不一会儿晓雄就明白了,女人是想要他加班工作。
晓雄没有露出丝毫不情愿的样子,昨晚洗澡的时候,女人给他送了那套都彭内衣。他听说过都彭这个法国牌子,他懂得女人这样做是因为喜欢他。其实喜欢不喜欢让他看来都是无所谓的事,喜欢他的女人很多。他注重的是职业道德,他是一个敬业的人,满足客户的要求是他的工作准则。
他打起精神,尽心尽力地服务。女人无疑是在渴望着需求着,然而行动起来却推推拒拒,闪闪躲躲,在床上不停地磨转,让他额外地消耗了许多气力。他渐渐躁起来,猛然着力,女人就像雪橇一样滑向床边,脑袋垂落而下,散披的头发在地毯上扫拂不已。
“掐我,掐我!”女人迫不及待地呼喊。
晓雄的双手就恶狠狠地掐卡下去。身下的女人痉挛般地挣扎,忽地翻出眼白,晓雄下意识地松了手。
女人急促地喘着气,晓雄这才觉得心里怯了,他怔怔地盯着女人的脖子。那一带白的皮肤上赫然地留着卡掐的红痕,看上去着实有些惊心动魄。他担心女人会生气,女人却在他的耳边喃喃地说,“真好,真好……”
钟文欣真的是以此方式达至了满足。洪开源是她的入门师傅,她是在挣扎中在受虐中初享快感的,以后便相沿成习了。
躺在晓雄的臂弯里,钟文欣让自己由亢奋状态慢慢地转为平静。是这个男人让她如此快乐的,她的心里溢着惬意,也溢着对身边这个男人的依恋。她的手不停地抚摸着晓雄的脊背,那情形就像出足了风头的舞女,在爱抚自己的红舞鞋。
晨光早已升起,密闭的窗外隐约地传来汽车的声响。虽然还恋着床,但是钟文欣不能不起身了。九点钟还要会见几位大客户,那是已经约好的事情。
钟文欣一边穿衣一边对晓雄说,“对不起,我真想留在这儿,可是今天上午,还有一单生意要谈。”
“真的,我也想留在这儿,可是今天上午我还有课。”晓雄说。
洗漱完了收拾好了,两人一起离开客房。钟文欣心里忽然有些依依不舍,于是说道,“走,找个地方,咱们一起喝牛奶吃比萨好不好?”
晓雄点点头,女人买单请吃早点,这等好事晓雄就却之不恭了。
汀州市有一家“佛罗伦萨”西饼屋,那里的西点颇有名。钟文欣带着晓雄,开车去了那里。看得出这家店的生意不错,店前的泊车位几乎是满的,钟文欣好不容易才找了个空位置,插进去把车泊住了。晓雄从车里出来,正要跟着女人往店门那边走,忽然有什么东西一晃,让他即刻收住了脚。
是那辆宝石蓝的“威姿”车。“嫩嫩”在店里!陪着这么个老女人在“嫩嫩”面前用餐,那可真是有病了。
“喂,晓雄,快进去呀。”钟文欣在店门前回身催促他。
“对不起,我这才想起来,讲义没有拿,等会儿上课就麻烦了。”
“吃了东西再去。”
“来不及,来不及了。”
晓雄忙不迭地摆摆手,转身就走,仿佛担心动作慢了,会被人拖进去一样。
钟文欣也就招手道了再见,然后独自进了店门。
“佛罗伦萨”西饼屋的店堂挺大,店里的味道十分诱人。那是由蛋糕和面包的鲜奶油味儿,比萨饼的洋葱烤肠味儿和现磨现煮的咖啡什么的混合而成的气息。靠墙那边的货架上陈列着蛋糕和各式西点,烤比萨的电炉就摆在收款台旁边,在那里做着现烤现卖的表演。临街的那排玻璃窗下摆着桌子和厢式座椅,供用餐的客人落座。
晓雄既然没来,钟文欣也就不想去买什么比萨,她打算来杯热奶和一小块蛋糕,就这样把早饭打发了。
钟文欣排到收款台前,忽然看到女儿钟蕾站在柜台里边,正和一个领班模样的人谈着什么。钟文欣叫了声“蕾蕾……”,钟蕾转过身看到母亲,神色竟有些慌乱。她匆匆地离开那人,然后向母亲这边走来。
钟文欣说,“蕾蕾,你在跟人谈什么呀?”
钟蕾说,“没,没谈什么。”
女儿大了,很多事都不会给妈妈说的。钟文欣叹口气,随便地问一句,“是来这儿吃早点呀?”
“对,对,吃早点。”
钟文欣觉得奇怪,“梅姨在家没有给你做早饭?”
“不,做了。是我自己出来,想,换换口味儿。”
钟文欣又叹口气,女儿这是执意要瞒着她了。钟文欣不再追问,只是说,“你想吃什么?”
“和妈妈一样吧。”于是,钟文欣就买了两杯鲜奶,两块巧克力蛋糕。
昨晚折腾了一夜,钟文欣是饿了。不一会儿,面前的巧克力蛋糕就进了肚,牛奶也喝下了多半杯。钟蕾的那块蛋糕却还在碟子里,碰也没有碰。其实从家里出来之前,钟蕾已经用过了早点,自然没胃口。
钟文欣说,“蕾蕾,你怎么不吃呀?”
钟蕾搪塞道,“不想吃,减肥。”
“肥不肥没关系,重要的是健康,”钟文欣把女儿面前的蛋糕又吃下一半去,然后自嘲地抚抚肚腩说,“你瞧妈妈,身体多好。”
两人都要上班去,也就不再耽搁。出了门,钟文欣发动了“凌志”车,钟蕾开上她的小“威姿”,母女俩就此分道扬镳了。
拿个狗屁讲义,上个狗屁的课。
晓雄离开“佛罗伦萨”饼屋,立刻打“的士”回了出租屋。身子一挨床,就觉得累了,眼皮坠坠的,要睡觉。晓雄的生物钟已经适应了他的活动规律:白天睡觉,黄昏之后出去“工作”。
被子刚蒙住脑袋,房东太太就在外面敲门。“喂,‘石大川’是不是你呀?这儿有‘石大川’的信。”
他赶忙从床上跳下来,打开了门。他上个月刚刚换了出租屋,这位房东太太还没有代他收过信。
白色的信封捏在房东太太手里,那女人狐疑地盯着他问,“你不是叫晓雄吗?怎么又叫个‘石大川’呢?”
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晓雄是我的笔名。”
“笔名?”
“对,是我写文章时用的名字。”
“噢……”房东太太似乎恍然大悟,她从头到脚将晓雄重新打量了一番,“你是个自由撰稿人吧?什么时候把你发表的文章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