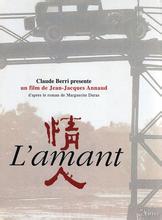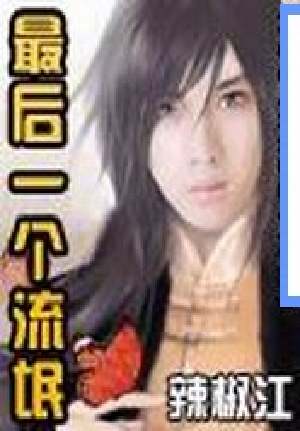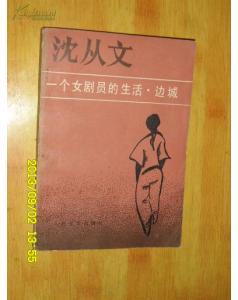一个被包养男人的沉浮史-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钟文欣听了愈发生气,她把那个手抄曲谱本高高地扬起来说,“好啊好啊,你有权利,我尊重你。那么也请你尊重我,这是我的本子,你没有权利动我的东西!”
伍伯正在帮助梅姨收拾餐桌摆碗筷,听到母女俩吵架,便过来劝道:“蕾,蕾,你就别,别惹你妈,生,气了。”
钟蕾瞥了伍伯一眼,分辩道,“不是我惹她,是她惹我。”
钟文欣莫名地伤心起来,她摊摊手大声抱怨着,“你们瞧,你们瞧,她这是长大了,真是长大了呀……”
梅姨赶忙上前安慰钟文欣,“吃饭啦,吃饭啦,别说了,别说了。”
等到一家人在餐桌前坐下,钟文欣的心情也渐渐平静下来。她这才觉得方才自己的情绪有些失控,说话行事都有些无理。钟文欣如此这般自省自责了之后,再与女儿面对就不免有些愧意。
就在钟文欣觉得无趣的时候,阮珊打来了电话,说是麻将桌已经摆好,要她快来参战。阮珊在电话里用的是那种若无其事的语气,似乎她们两人之间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
钟文欣将这个电话视做善意的求和。本来嘛,姐姐妹妹的,关系亲得很,之所以会闹出些不快,还不就是因为当中插进了一个晓雄?钟文欣既然已经下了决心,与晓雄一刀两断,也就不必再因为这么个男人伤了姊妹和气。
于是,钟文欣就找了个托辞,中途离开餐桌,去了阮珊那儿。餐桌前只剩下钟蕾和伍伯梅姨。钟蕾没有什么胃口,随便扒拉了几下,便放下碗筷站了起来。
梅姨说,“蕾蕾,再吃点儿吧。”
钟蕾摇摇头,她径直来到钢琴前,拉开琴凳坐下,弹出了一串音符。
“蕾蕾,吃,饱了再,弹,”伍伯跟过来,担心地劝着她,“吃饱饭,才,才能身体好。”是那种婆婆妈妈的语调。眼神呢,软得像是在求告。这些都让钟蕾觉得受不了。
钟蕾重重地敲击琴键,让钢琴像跌瀑一样轰鸣。
伍伯说,“蕾,蕾,别,别这样。”
钟蕾知道不应该这样,然而十个手指却仍旧固执地在琴键上重重地敲,那情形就像手指虽然属于她,而她却属于别人一样。伍伯只好叹着气摇着头离开。
没有人干扰她了,钟蕾要认认真真地练一练那首《爱的罗曼斯》。她得看着曲谱弹,可是那个手抄的曲谱本呢,它在哪儿?
那个厚厚的丝绒包还在,包里依旧裹着许多钢琴练习曲,惟一不见了的就是那个手抄本。
它被放在什么地方了?钟蕾吃力地回想着,她的脑袋开始发胀开始发箍,在那胀和箍的感觉就要爆炸之前,钟蕾的眼帘上终于出现了曾经发生过的情景:母亲怒气冲冲地扬起那本曲谱,把它像面小旗一样摇来摇去。
钟蕾就上楼去开母亲房间的门。门把手扭不动。离开房间就锁门,那是钟文欣的习惯。
钟蕾“喀啦喀啦”地扭着门把手,然后又用脚把门踢得“咚咚”响。伍伯听到声音,就在下面结结巴巴地喊,“锁……,着呢,锁……着呢。”钟蕾知道门是锁着的,然而她的手和脚仍旧不停地扭着踢着。梅姨上来开门了。
看着梅姨手里的那串钥匙,钟蕾怔忡地想:梅姨不识字,母亲锁门不是锁梅姨的,锁的是钟蕾。
进了屋,钟蕾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手抄本的曲谱,它就放在床头柜上。钟蕾伸手去拿,梅姨说,“蕾蕾,你妈不让你动的东西,还是不动为好。”
钟蕾身体里的另一个人说,就要动,就要动。于是,钟蕾的手就痉挛般地抖起来。那本曲谱像被狂风吹着一样,被她翻得哗哗啦啦响。
翻着翻着,钟蕾就翻出了门道。手抄本上那些汉字和五线谱符号一笔一画,显得那么清秀,那么俊逸,看着那些笔画就让人仿佛看到了一个站立在那儿的男人。他洁净而斯文,清瘦而灵动。
他是谁?手抄本上留的有名字:韩冰。
钟蕾心中豁然一亮,脱口就说,“韩冰是什么人?”梅姨茫然地摇摇头。
钟蕾就拿着那手抄本下了楼。
“伍伯,我有一个问题,请你务必真实地告诉我:韩冰是什么人?”
伍伯就像冷不防被人闷了一棍。他翻着眼皮,急巴巴地说,“蕾,蕾,你你,你怎么想到问这个人?你,你可,可别乱,乱想啊!”
钟蕾冷冷地笑了笑,“我知道,韩冰是我妈妈当年的钢琴老师。”
伍伯长长地叹口气,无奈地说,“是,是谁,给,给你说的?”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钟蕾闭上了眼睛。她仰起头,喃喃地像是在对天发问,“告诉我,他在哪里?他是做什么的?”
“蕾蕾,别,别这样……”看着钟蕾失神的样子,伍伯劝解似的说,“韩,韩,冰是幼儿师,范学校的老,师,那都是很,很久以前的事,事了……”
一个被包养男人的沉浮史
3。 用想象来置换
汀州市的长途汽车总站看上去很宏伟,它的大厅和附属建筑都是当代欧美风格,可以归于那种简单明快的几何图形。然而,它们的脑袋上却戴着庙宇式的大顶盖,这种中西合璧的风格就像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头上扣着满清的顶戴花翎。或许,这也可以算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筑吧,它们其实和这里出出入入的各色人等自有一种谐调和默契,乘坐长途汽车的旅客以乡下人居多,汀州的长途汽车总站就有了城乡结合的风格。
魏彩彩乘坐的那趟箕山县到汀州的长途车是在二十分钟之前抵达的,从站里推推拥拥地向出口处挤过去的时候,魏彩彩就不停地踮着脚向外张望,期盼能够看到石大川那张熟悉的脸。一起出站的人都走了,站口已经空了,只剩下魏彩彩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就像是收过的庄稼地里留着一根漏割的麦秆。
箕山县城到汀州市每天只发一趟班车,发车时间是清早八点。魏彩彩五点多钟就起了床,约摸走了二十分钟,才从魏庙村到了公路边。还好,七点不到,就搭上了一辆去县城的四轮拖拉机。拖拉机的拖厢是装过煤的,幸而扫得还干净。魏彩彩把两个大提包放在拖厢板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在了提包上。魏彩彩脚上套着八成新的单皮鞋,是那种松糕底样式的,前两年挺流行。她下身配的是一条法兰绒彩格裤,那是压箱底的宝贝,每年只是过春节的几天里翻出来露露脸。裤腰瘦了一点儿,套不上毛裤,套的是一条薄秋裤。上身穿的是从县城百货大楼新买的棉衣,大红色的风雨绸面料,背后还吊着个风雪帽。这套行头已经是魏彩彩能拿得出来的顶级的豪华配置了。虽然已经过了春分,乡间的清晨仍旧冷得很。魏彩彩蜷在不高的车厢护板后面,尽量用胳膊拢着膝盖和小腿。她的脸是埋在两个膝盖中间的,她怕脸皮被寒风吹皴了,到汀州见了石大川难看。
在县城赶上了发汀州的班车,坐进大客车里冷倒是不冷了,只是窝在座位上久了,那条法兰绒裤子皱得厉害,拉也拉不直。长途汽车不像火车,没有准确的时刻表,预计是在下午四点至四点半到达的,谁知道三点半钟就到了。头天在电话里说好了石大川在出站口接,一下子见不到他的人影,魏彩彩顿时慌了神儿。
魏彩彩仅仅到过箕山县城,省城汀州还是头一次来。车站的楼高得很哩,比县政府的办公楼还气派,车站前面的广场比魏庙村最大的畈田还要大。大畈田清静得很哩,这大广场上的人却比鸡场里圈得鸡还稠。市声喧哗,车来人往,让魏彩彩听得耳噪,看得眼晕。
魏彩彩想给石大川打个电话,百十米开外的地方就有一排IC卡电话亭,旁边有小卖部,可以买到话卡。可是,魏彩彩守着出站口不敢走,她怕就在她买卡打电话的工夫石大川来了找不到她,那样她就会像漏口袋里的钥匙一样给弄丢了!
站在那里翘首等待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煎熬,魏彩彩就蹲下身收拾带来的东西。她爱惜地拍打着大旅行袋,然后扯扯拉拉,让它重新鼓起来。大旅行袋里装着换季的衣物,那是女人的全部细软。小一些的旅行袋却比大的那个更沉更重,里边装的是杂物。袋子的一角看上去有些潮湿,魏彩彩打开看了,不禁“啊”了一声。是那个腌菜罐子裂开了,还在淌着汁水。那些汁水沾在旁边装干辣椒的塑料袋子上,看上去湿漉漉的。魏彩彩顾不得多想,急忙伸出双手将腌菜罐捧出来,然后又掂起了那袋干辣椒。
在魏彩彩的记忆里,石大川最喜欢这两样东西。晒干的红辣椒在锅里用油炝乌了,再放进腌萝卜干一块儿炒,吃起来特别下饭。萝卜是魏彩彩一个一个挑选出来的,切成条晒得半干,才精心地腌进小罐子里。辣椒是从自家菜地里摘的,把那些最大最尖最红的用线串起来挂在屋檐下,一天天看着它们变得轻盈,人的心也就跟着飘飘荡荡……
“彩彩……”一个声音在唤她,听起来悠悠的,像是梦。
蹲在地上的魏彩彩往前看,看到的是一双锃亮亮的黑皮靴。它们矜持地立在那儿,显得既威武又气派。
顺着黑皮靴往上看,就看到了毛料风衣那精致的长摆,它既密实又柔软,别具一种飘逸的悬垂感。毛料风衣是颀长的,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主人的身材。风衣的领子刻意地竖了起来,犹如骑士那坚挺的金属护颈。在领口处有真丝领带恰如其分地若隐若现着,点缀出一片斯文与优雅。
“彩彩,对不起,我来晚了。”石大川向她伸出手。
他是石大川吗?魏彩彩疑惑地站起来,身子不由得向后退了退。她怯生生地望着面前这个都市男人,心里满是自惭形秽的感觉。
其实,从她形影相吊地立在出站口的那一刻起,她就自惭形秽了,她发现她穿的那条法兰绒裤子皱得像是一团被人揉过的纸巾,大红色的新棉衣也变得灰头灰脑,上面沾着那辆拖拉机后厢里残留的煤灰。面对着都市广场的这派繁华这番陌生,她不能不心生敬畏。
“大,川哥……”魏彩彩生涩地叫着,像客人似的握了握对方的手。就在那一瞬间,她意识到她将腌萝卜的汁水沾到了石大川的手上。她慌忙松开自己的手,拿出手绢递过去。
石大川只是轻轻皱了皱眉,然后便宽容地笑了。他没有接魏彩彩的手绢,他掏出纸手帕揩了揩手,然后指着地上的腌菜罐说,“有没有搞错,带这种东西来?扔了,扔了吧。”
仿佛天上的老鹰要下来捉鸡娃,魏彩彩像母鸡护仔似的护住了那小菜罐。她用塑料袋将裂了缝的菜罐套住,然后重新放回了旅行袋里。石大川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
坐在出租车里,魏彩彩不住地向外张望。她好奇而专注地观察着车窗外掠过的景物和人群,她要熟悉它们,她要记住它们。从今后,这就是她的城市,这就是她和石大川的城市了!
出租车驶过繁华的汀东大街,忽然向左一转,就拐进了被叫做“都市村庄”的齐寨。齐寨中街是一条笔直的柏油马路,虽然不宽,但还过得了汽车。再往枝枝杈杈的分道上走,就有些困难了,出租车在岔道口上停住,魏彩彩就随着石大川下了车。
七拐八拐地转到了那座小楼前,顺着楼外另修的水泥楼梯往四楼爬。三楼和四楼都是后来在两层的楼顶上补接的,层高矮了一点儿,水泥楼梯也修得窄显得陡。石大川一边抬脚往上走,一边提醒,“当心,楼梯陡啊。”语调是关心的,似乎还有些歉意。“不碍,不碍。”魏彩彩心满意足地回答。陡了正好可以拉着他,窄了正好可以偎着他。
开门进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