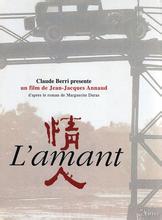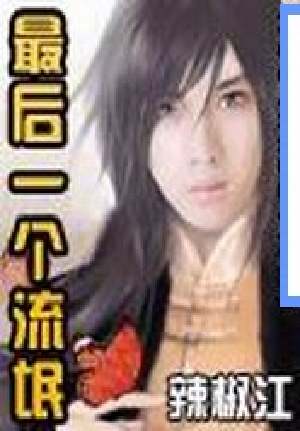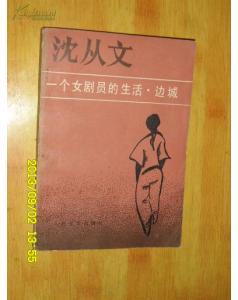一个被包养男人的沉浮史-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能请,就是不能请家庭教师,你听到没有!”钟文欣一扬手,将茶杯摔在了地上。那表情和动作看上去都有些神经质。
钟蕾觉得委屈极了,她“砰”的一声合上琴盖,转身跑到了院子里。
这幢别墅小楼的院子里植了草坪,围了矮矮的冬青树墙,伍伯正拿着花剪修整着冬青枝。他先是看到钟蕾郁郁不乐地跑出来,接着又看到钟文欣气急败坏地追出来,嘴里还嚷嚷着,“真是长大了,真是长大了……”
钟文欣这样嚷嚷的时候,伍伯就停下手,站在冬青树墙边向她张望。被伍伯这么一看,钟文欣就噤了声,转身回去了。
伍伯这才走到钟蕾身边,憨憨地笑着说,“蕾,蕾,惹……妈妈生,气了?”
“不是我惹她生气,是她让人生气。我不就是说了要请个钢琴教师嘛,也值得发那么大的火?”
伍伯的小眼睛里有亮光闪了闪,“唔,妈妈说不,请钢琴老……师,总有不,请的理由。”
“什么理由呀?这也不痛快,那也不高兴,谁还看不出来嘛,还不就是不想让我动她的钢琴!”
伍伯顺着钟蕾的话说,“对,谁,稀罕她,的旧琴。赶明儿咱,们蕾,蕾自己买一个。”
“就是。”钟蕾笑了。
从小到大,伍伯就在钟蕾的身边,虽说是男佣,却也是长辈。有时候也觉得他的话多了点儿,有时候也觉得他的事儿多了点儿,但是钟蕾却也习惯了和这个慈眉善目的长辈聊天。两人聊了一会儿,不悦的情绪也就渐渐地散淡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钟蕾看到桌上摆了她最爱吃的油烹竹节虾。钟文欣满脸慈爱,亲自动手为女儿夹着菜。“吃啊蕾蕾,这是我让梅姨专门到海鲜市场给你买的。”
钟蕾淡淡地说,“谢谢,我自己来。”
母亲显然想与女儿修好,她面带歉意地说,“蕾蕾,对不起,妈妈不该对你发脾气。”钟蕾却只顾低头扒着米饭,似乎没有听见。
钟文欣叹口气,又说道,“想学钢琴,其实也不是不可以找教师,回头妈替你找一个合适的。”
钟蕾回了句“谢谢妈妈”,神情似乎有点儿心不在焉。
钟文欣当然无从得知,此时钟蕾的心思已经不在弹钢琴和找老师上了。钟蕾方才从外面的草坪和花园回到小楼里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情景犹如电光石火般地点亮了她:别墅式小楼是新的,房间的装饰是新的,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是新的,唯有这架钢琴是旧的!生活中的这处陈迹意味着什么呢?
钟蕾的心在胸腔里莫名地激跳起来,那情形就像是在林高石乱雾霭弥漫的深山里找到了进入秘密山洞的石门。钟蕾满脑袋都是有关那些秘密的想象,母亲在饭桌上又说了些什么,她几乎一点也没有听进去。
用完了午饭,钟文欣回房间小憩。钟蕾就迫不及待地动手查看那架钢琴。直觉告诉她,有关这架钢琴身世的材料应该在琴身附带的小屉里。
果然,身份证就装在随身的口袋里呢,那是小牛皮一样光滑厚实的产品卡,上面印着一串串别致的拉丁文字。那些勾勾拐拐的拉丁文刻意制作成鹅毛笔书写的风格,望上去古朴典雅。相形之下,那张购买钢琴的单据就显得很流俗,薄薄的一张纸,上面有圆珠笔写的价目和一些汉字。“汀州市宏亮琴行”!
她知道宏亮琴行,那是汀州市最老最大的一家乐器商行,就坐落在汀州市最繁华的五福大道上。没有片刻的犹豫,钟蕾带好那些东西,就出门开车直奔琴行而去。
大约是因为人们喜欢利用午后这段时光小憩的缘故,偌大的琴行里显得有些空寂。店堂内几乎看不到什么顾客,只有一架架样品钢琴在静静地打盹儿。看到钟蕾走进来,一位店员模样的年轻小伙子挂起笑脸说,“小姐,你买琴?”
“不,我是想问问,这架钢琴是你们这儿卖的吗?”钟蕾把那架钢琴的有关单据拿了出来。年轻店员将那些泛黄的纸片看了又看,搔搔脑袋说,“这是我们店出的货吗?好像是吧,唔,这可早得很呐。”
“什么事啊?”店堂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那声音陈旧而洪亮,听上去犹如调音师在拨弄着一架品质出众的老钢琴。接着,钟蕾就看到一位老人从侧旁的玻璃门踱了出来。
老人自我介绍,他就是这个店的老板楚宏亮,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钟蕾说:“我看中了一架钢琴,是二手货。当然了,不摸底儿,不怎么放心。所以想来打听一下,这琴当年是不是从你们店里购进的。”
老人架起老花镜,将钟蕾带来的东西看了,便开心地笑起来。“哈哈哈,‘克利斯多佛利’!是,是我的货。我记得,记得!不是所有的琴行都有‘克利斯多佛利’钢琴的,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卖出‘克利斯多佛利’的。那是意大利产的名牌钢琴,宏亮琴行从开张到现在也不过仅仅卖出过两架这个牌子的意大利钢琴。”
“是开源电脑公司的老总洪先生来买的货,呵呵呵,洪开源!他可是最早到汀州来的那批台商,那个小矮子,那个干老头,呵呵呵,他出手可是大方得很。”
钟蕾疑惑地问,“小矮子,干老头?他,他会弹钢琴?”
店老板摇摇秃脑袋,“洪开源弹什么钢琴呐,他是给女人买的,给他的女人。”
“他的女人?”钟蕾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是啊是啊,”店老板健谈得近乎饶舌,他津津有味地讲下去,“嗬,他的女人那叫年轻啊,他的女人那叫漂亮啊。个头有这么高吧,腿有这么长,模特儿,模特儿呀。”
店老板用一双眯起来的小眼儿向店堂的中央凝望着,仿佛此刻洪开源的女人还站在那儿。钟蕾也怔住了,她情不自禁地陷入了对母亲的想象里。
“‘克利斯多佛利’是我这里最好最贵的钢琴了,那女人婀婀娜娜地来到‘克利斯多佛利’面前伸手一指说,‘就要这一架’。没什么说的,洪开源就给她买了。呵呵呵,千金买一笑啊!”店老板啧啧地赞叹着,分不清是赞叹那女人,还是赞叹他的钢琴。
“……”
店老板那陈旧而洪亮的声音在钟蕾的身边不停地回响,店老板在给这个乏味的午后添加着趣味。可是那声音已经无法进入钟蕾的身体了。她的身体里装满了故事,洪开源和母亲的故事。
钟蕾其实并不想了解那些东西,洪开源早已不在母亲的生活里了,那不过都是些过去的事罢了。此刻,让钟蕾心绪烦乱的只有一个念头:洪开源是不是她的父亲?
钟蕾想离开这儿了,她想怀揣着这个疑问去寻一处僻静的角落来独自拆解它。于是,钟蕾彬彬有礼地告辞道:“谢谢,谢谢,我已经知道‘克利斯多佛利’的来历了,我已经明白了它的价值。”
“哦哦哦,你这就走啊,”失去了听众,店老板似乎有些遗憾,他把客人送到门外,还意犹未尽地问,“你是要从洪开源的女人手里买‘克利斯多佛利’吗?”
钟蕾只是淡淡地一笑,然后拉开了车门。店老板向她招手道别,“哦,姑娘,你尽管放心买吧。你不会上当的,那可是一架好钢琴。”
钟蕾离开宏亮琴行的时候,钟文欣也离开家去了文欣公司。
钟文欣其实没有必要在星期天到公司去,之所以到公司去转转是因为无聊。星期天的那份无聊通常是在阮珊的麻将桌上打发的,可是这个星期天却没有阮珊了。阮珊前两天给她打了个电话,说是要去厦门孩子他二姨家住个十天半月的,这段时间就不要联系了。
人到公司,就进入了角色。在大班台前一坐,便不由自主地要联系业务打电话。真是没事找事啊,客户来了,产品啦价格啦,几个人凑在一起聊啊聊的,就聊到用晚餐的时候了。吃饭吃饭,喝酒喝酒,对方抢着要做东,大家就开车去了“老爹火锅城”。
正值隆冬季节,“老爹火锅城”生意火得很,包间要提前一天订,钟文欣他们这个时候去只能在大堂里找散座。偌大的鸳鸯锅,半边红汤半边白汤,浓汁腾腾地沸起来,涮螃蟹、涮大虾、涮牛肚、涮羊腰、涮宽粉、涮生菜……大家各行其是地涮着,人人各得其所地喝着。热热闹闹之中,钟文欣却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
她觉得有人在看她,是谁?
钟文欣四下张望,周围那些散座上的食客们都在吆五喝六,吃得专注而投入,似乎没有什么人在向她这边留意。钟文欣已经打算转回头了,忽然间,一对熟悉的目光在大堂的最远处与她的目光相遇,她下意识地笑了,那是阮珊的老公朱卫和。
该去打个招呼吧,该去碰碰杯,寒暄寒暄。阮珊端起酒杯向对方那边走,对方也端着酒杯起身迎过来。两人就在狭窄的过道上会面了,对方的眼神里似乎有一种不期而遇的困惑。
“你怎么在这儿?”老朱灌下一口啤酒,用肥手掌抹了抹嘴。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钟文欣觉得对方问得奇怪。
“你不是和阮珊一起跟团去了新马泰?”老朱的眼睛锐利地盯着她。
“唔,是去,新马泰吗?”钟文欣似乎明白了什么,“嘻嘻,我临时有事,对,没有去成。”
老朱沉吟道,“阮珊说,是跟你一起去的。”
那目光那语气都有些异样,钟文欣察觉自己可能失言了,赶紧掩饰说,“阮珊是换了别的朋友吧,是不是邢锦霞呀?”
“嗯。”老朱的嘴角挂出一个老到的微笑。
钟文欣不想恋战,指指身后说,“对不起,我是跟客户一起来的。”
“好好好,你去忙。”两人又碰了杯,便各自分开。
钟文欣回到座位上,再与那些客户们应酬的时候就有些分心。这个阮珊,自己悄悄出国旅游就旅游吧,干吗还要编个谎话说是去了厦门孩子他二姨家。就这么唬朋友,也太不够意思了。这头骗着朋友还不算,那头还要骗老公,说是跟我一起去的。怪不得交代我别往家里打电话,怪不得叮嘱我这段时间就不要联系了,原来是怕穿帮啊。
阮珊这样做,想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吧,莫非她是跟着情人幽会去了?她那个模样的女人,也会有情人吗?钟文欣想到这儿,就仿佛看到一个黑黑胖胖的半老徐娘,挽着男人的胳膊肘儿,依依偎偎做小女儿态的样子,钟文欣忍俊不禁地笑出了声。
……
酒足饭饱,大家热热闹闹地在饭馆门前分手。等客人们散去之后,钟文欣独自坐进了汽车。她打着火暖着车,静静地等着起步。雪落得很厚,将车身裹成了白白的一团,钟文欣就觉得寂寞和空虚也像雪壳一样裹着她,让她透不出气。
她忽然想起了晓雄。在这样的雪夜,有晓雄在卧榻边做伴,心里也会充实一些,快乐一些吧。钟文欣拿出手机与晓雄联络,一连挂了几回,对方的手机都关着。钟文欣怅然了,她不禁想起晓雄每次陪她的时候,都毫无例外地要关上手机。哦,有生意了,不接电话了……钟文欣刻薄地咬了咬嘴唇,将汽车油门狠狠地一踏,便轰然上路。
都市的雪夜有一种冷艳的美,强烈的灯光将冰镶雪裹的街道映得一片皓白,望上去犹如浓妆的女人涂了太多的脂粉。这亮晶晶的冷美人看上去清高傲慢,然而再往深里瞧瞧,就能看出在那熠熠的白光里透出的自怜自伤的孤独。
钟文欣神情茫然地坐在车里,那情形仿佛不是她在驾车而是车在驾着她走。走着走着,前方出现了熟悉的富丽宾馆,她即刻将目光转过去,投向了富丽宾馆对面的西海湖。湖边的“秋月舫”灯火通明,裹着白雪的画舫是晶莹的,挂着冰凌的岸柳是剔透的,远远地望去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