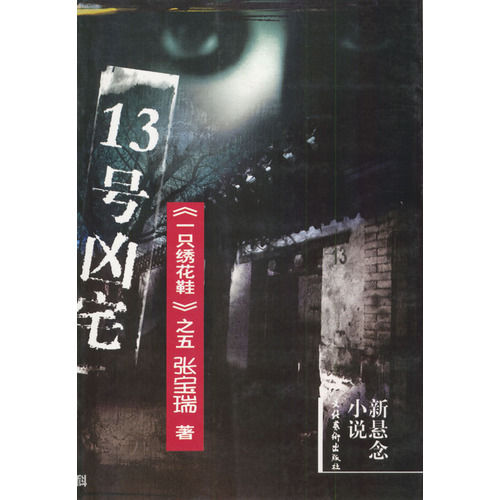状元娘子1323-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名的次第,即是经排列的顺序。这就是士林中艳称的“五经魁首”,简称为“五经魁”。
从乾隆五十三年以后,各占一经的规例取消,士子必须通五经方有中式的希望。但“五经魁”的名目,实亡而名存,仍旧照相沿的规矩,到最后方始揭晓。其时总在三更天,闱中执事杂役,以及内外帘官带入闱的家丁,都准到“至公堂”前观看,每人手中一对红烛,照得霞光潋滟,绮丽非凡,名为“闹五魁”。手中那对燃过吹熄的残烛,据说为蒙童点来读书,可长智慧;又说在产房燃点,对催生有奇效。所以出闱以后用来送人,还是一样颇为珍贵的礼物。
“候榜的滋味,算是领略到了。”到了十点钟,洪钧有些沉不住气了,苦笑着念了蒲松龄的一段文章,“‘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猿。忽然而飞骑传入— ’”
下文尚未出口,只听锣声当当,自远而近;不由得噤口侧耳,屏息静听。锣声自低而高,复由高而低,之后越过客栈,报到别家去了。
“‘报条无我;此时神情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饣甘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洪钧解嘲似地问:“清卿,我总还不致于如此不堪吧?”
在细玩一通新出土残碑拓片的吴大澄,表面平静,内心却比洪钧还要紧张。因为他不但自许必中,而且自信名次会中得很高,如果已有七八十名揭晓,尚无消息,看来凶多吉少。因此,答话的声音便有些不大自然,“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他念了两句杜诗,摇摇头没有再说一句。
锣声又响了!这次是清清楚楚听明白,止于招贤客栈,由大门响进他们所住的院落。两家的听差,不约而同地奔了出去,同声问道:“是哪家?是哪家?”
“洪三老爷— ”
洪钧不能再听见别的声音。这四个字入耳如雷,震得他心跳不止;不自觉地一手按胸,一手扶桌,才能站住。
这一来,吴大澄反而先要照料洪钧了。第一件事是开发报房的赏钱。而不论出手如何豪阔,永不能一下就满足此辈的贪餍,在不断“请高升”的要求之下,由四两银子加到二十四两,方能打发。
接下来还是开发赏钱。不过打发客栈里的伙计,不会争多论少;但一拨又一拨,也费了好些功夫。加上来贺喜、来打听消息的同乡举子,川流不息;吴大澄少不得也要帮着应付,口中说着冠冕堂皇的应酬话,心里却是毛焦火辣,恨不得插翅飞入贡院“至公堂”,抓住主考喝问一声:到底吴大澄中与不中?立刻拆所有卷子的弥封来看!
这时洪钧已踌躇满志,神闲气静了。毕竟同乡好友,而且是结伴来应试的,休戚相关之情,与众不同。看看时将午夜,尚无吴大澄的消息,便即高声说道:“清卿是一定得意的!看样子不是抡元,亦必在经魁之列。雨雪已停,我们不如到‘龙门’去候佳章。”
屋中还有四个同乡,两个已中,两个还在未定之天。中了的与洪钧的心情相同,未中的是泥菩萨怕过江,沉默着表示不愿凑这份热闹。
“清卿!”有人催吴大澄,“走吧!”
“不啰!”吴大澄强笑着,有些告饶的意味,“我还是在这里等。”
他的心境,不难了解,等着了好消息,自无话说;一旦落空,在稠人广众之下,会更觉难堪。因此,洪钧便说:“也罢,让清卿兄养养神。回头贺客盈门,着实要费一番精神呢。”
于是,洪钧和另外那两个簇簇新的新科举人,相偕出了招贤客栈。但见秦淮两岸,灯火万点,人影幢幢,一路走,一路听人谈论,所谈的无一不是“某人中了,某人可惜”之类的话。刚到贡院,但见人潮突然前涌,仿佛争着要抢夺什么好东西,又仿佛出了什么乱子,要看个究竟似地。
“怎么回事?”洪钧有些心慌,站住了脚。
“大概是五魁揭晓了!”
果然,闱中在“闹五魁”了。仍然是逆数着拆封;第五名、第四名,都不是吴大澄;第三名说是姓吴,苏州人。
“这大概是了。”洪钧很高兴地说,“我们快回去吧!”
“索性等一等,打听打听确实。苏州姓吴的,不止清卿一个。”
“马上全部揭晓了!”另一个也说,“倒看一看是谁领解?”
解元姓江,扬州人,这不比姓吴的苏州人;洪钧和他的同伴都知道,扬州有个姓江的名士,单名一个壁字。果真解元是姓江的扬州人,正为江壁。
“好了,走吧!”洪钧拉一拉他的同伴,“第三名一定是吴清卿。”他极有把握地说,“江壁领解,足见这一科不易侥幸,文章有价,以清卿的闱作,当然应该在经魁之中。”
果然,归途中远远就听见招贤客栈门口鞭炮大作;走近一看,店家特为竖起一扇门板,上贴好大一张深红报条,泥金楷书,写的是:“捷报苏州府的吴老爷印大澄,应本科江南乡试,高中第三名举人。”下面署名是:“报喜人连三元”。
报条旁边,站着招贤栈的掌柜,满面飞金、高拱双手,倒像是他的什么人中了举,在向贺客答礼似地,一见洪钧,高声说道:“洪老爷,恭喜###!”
“托福、托福。”洪钧顺口回答。
“是托诸位新贵人的福。”掌柜很兴奋地说,“小店的风水转了。这一科,我们招贤栈就中了十三名,哪一家都比不上我们。而且还出了吴老爷这位经魁。快请进去吧,吴老爷高兴得手忙脚乱,支使不开了。”
听这一说,洪钧便加紧了脚步。踏进所住的院落,就听见吴大澄拉长了嗓子,在念自己中轻魁的文章。一唱三叹,抑扬过分,听去如念祭文,是得意得有些忘形了。
洪钧与吴大澄几乎一夜未睡,拂晓方得上床#睡不多久,又为听差唤醒,该料理出门,去赴“鹿呜宴”了。
向来“鹿鸣宴”只是一种形式。筵席用的倒是银台面,不过能看不能吃,鸡鱼鸭肉,无一不是泥土捏成,涂以彩色。曾国藩讨厌这种陋习,特地关照,要用真材实料,不必讲究,但要新鲜。因此,这一科“鹿呜宴”,便非虚应故事,坐一坐即散;而是揖让雍容,杯酒言欢,颇有个谈头了。
首先是主司率领新贵人望阙谢恩;然后按照身份名次,顺序入座。首席当然以正主考刘琨为主,曾国藩亲陪。刘琨是道光二十一年的翰林,比曾国藩晚一科,因而以“前辈”相称;曾国藩比较客气,称他“年兄”。
“恭喜刘年兄,功德圆满。”曾国藩说,“‘桂树冬荣’,数百年不遇的佳话,叫你我遇上了,实在难得。”
“托前辈的福,总算一切顺利,可以复命了。”刘琨放下酒杯,很得意地说,“揭晓之时,细舷想去,这一科实可称佳话。解元江壁者,以‘江’南完‘壁’归朝廷也!第三名吴大澄字清卿者,三吴澄清之谓也!这都是前辈不世的勋业。”
想想果然。这“三吴澄清”比“江”南完“壁”的解释更妙。曾国藩不由得也有些得意,举杯相敬,连答说:“谬奖!托庇朝廷,岂敢冒天之功?”
正副主考入闱之前,照例“封门”,关防严密;虽本省大员,亦不能私下相会。所以刘琨跟曾国藩还是第一次有畅谈的机会,少不得问起克复当时的经过,曾国藩也不免提到京中的情形。这都是极长的话题。加上簪花、举乐、唱诗等等繁文褥节,使得这一场“鹿鸣宴”,直到薄暮,方始散席。
这以后几天,新科举人还有许多人情应酬,第一件大事是拜老师。主考称为“座师”,本房的考官,称为“房师”——主考不能直接阅卷,决定取舍;必得由房考推荐,谓之“荐卷”。有时主考与房考的眼光不同,或者这位房考所荐的卷子已经满额,主考皆有权拒绝。而如房考力荐,得以取中,像这样的房师便是“恩师”,做门生的执礼特恭,“蛰敬”当然亦格外从丰。
贽敬一共要三份,大致自二两至十六两。洪钧不丰不俭,适得乎中,送正主考八两,副主考六两;房师的情分总要厚些,是十二两。吴大澄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房师荐卷,固然应该感激;主考将他取中经魁,则是刻骨铭心的文字知己,所以座师的贽敬各为十六两,送房师的数目与洪钧相同。
第二件大事是会同年,商量公宴老师。此外也少不得慰问下第的失意人。这一阵酬醉终了,已经腊月二十了,洪钧归心如箭,连照例应得的二十两牌坊银子都顾不得领,雇了一只“无锡快”,连夜赶回苏州。
他的两位老兄,已经在码头上接了三天了;还雇了一班清音堂名,备了一匹白马,一路吹创打打,将洪钧由阊门经闹市观前街,送到娄门圆峤巷。头簪金花,揽辔徐行的洪钧又窘又得意;心里在想,若是状元游街,又不知是何滋味?
一到家,首先入眼的自是高贴在门口的那张报条。得到消息来道贺兼看热闹的至亲好友,左邻右舍,老老少少,已经满屋盈庭。洪钧亦无法招呼,只含笑拱手,从人丛中昂然直入;先到祖宗牌位前行了礼,然后应酬亲族长辈;有那体恤的便说:“进去见老太太吧!不必招呼我们。”这样,洪钧才得到后面去见老母。
后面只得一明两暗三间屋子,也是挤满了女眷,一见洪钧,让出洪老太太面前数尺之地,好容他磕头。做娘的打叠了千言万语,却不知先说哪一句好。挑来挑去挑出一句话:“你吃了中饭没有?”
“我不饿!”
“你瘦了!”这句话也不是洪老太太预先打算好的,而是见了儿子的面,自然而然的关切,“瘦得很厉害。”
“怎么不要瘦?”洪钧答说,“从出闱到上船,一天没有睡过三个时辰。”
“这怎么支持得住?”洪老太太问道:“潘道台送你的那支参呢?”
那支参,洪钧打算在会试之时,备不时之需;而此时却这样答说:“我舍不得吃,想留着给娘当补药。”
这是何等的孝思?在场的亲友女眷,莫不交口称赞。洪老太太当然也是高兴非凡,自道是“苦出头了”。接着便提往事,当年如何抚孤守节;这几年如何受尽流离之苦。又自夸“老三”有出息是早就看准了的。一面谈,一面笑——笑中有泪;有泪还笑。
日暮客辞,合家团聚,所谈的还都是有趣味的事。其实,人人都知道,家运是要转了,但眼前却还有一段更艰难的日子。设宴开贺,上京会试,着实要大把银子花下去,从何而来?
家宴到二更天方罢;洪太太料理家务,诸事完毕,回卧房时已经三更都过了。
从洪钧回家,直到此刻夫妇方能单独相处。灯下执手,四目凝视,洪钧不免有愧歉之意:分别不付一个多月,妻子竟有了数茎白发,可以想见操持家务的辛苦。
“总算中了!”洪钧仿佛心有余悸,“倘或不中,就真不知道这以后的日子,怎么才能过得下去?”
原有许多苦楚待诉的洪太太,听得丈夫这话,将要说的话都咽了下去,反而很豁达地说:“你又不是笔底下不如人家;万一不中,是运气不到,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不是说羞于见人,是说我家的境况。这趟到江宁,总算山东带来的钱,还勉强够用。可是过年呢?”洪钧平心静气地说:“也不要说人家势利!锦上添花,热热闹闹,雪中送炭,冷冷清清,人总是好热闹的。倘或名落孙山,伸手跟人借钱,则我自己先就张不开口。”
“现在——”洪太太说了这两个字,突然咽住,觉得自己近乎过虑,可以暂且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