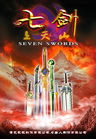站在院墙下-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端起酒杯大声说:“祝国家繁荣昌盛,祝槟哥生意兴隆,祝各位兄弟姐妹天天开心。”
我喝完第三杯,走到槟哥面前问:“程昕呢?”“不晓得死哪去了?”“那我出去high去了。”他点点头,我拉着阿sa回到了舞池。
DJ从未谋面,我走了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槟哥叫我过来放歌。”他用普通话大声地说:“什么?”“槟槟叫我点歌。”“哪个槟槟?”“你们槟总!”
“韩国的,朴志胤的……要原声,不嗨!”他听后,用力地点点头。
我拉着她到了舞池中央,对她说:“看屏幕……”
画面开始了。
她注视着画面,目不转睛。我猜得出,她此时和我的感受一样。
我就在那节奏里,从她的那块肉痣,吻到了嘴。
全场爆发出狂烈的欢呼声。
她伸出了舌头,感受着我发自内心的吻。
歌后,DJ将音乐降低,开始带我们进入狂欢时刻:“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bingbing……大舞厅……”
这时她问:“你对我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毫不忧郁地说:“小孩一个,未成人。”
她似乎有些不悦,继续问:“什么才叫长大了?”
“对于我来说,吃饭的时候想到的不再是小时候渴望的汽水,而是酒……听清了吗?”
她用力地点点头,而点头,不代表她能懂。
“老婆,你叫什么名字?”“何文彬,文质彬彬的文,文质彬彬的彬。”“阿娇呢?”“何文静,文静的文,文静的静。”
真看不出她是个文质彬彬的人,妹妹的确文静。
“我可不可咬你一口?”我认为她咬一口不会很疼,于是点头。我的惨叫声被音响炮淹没。她的声音却突然在我耳旁响起:“我不准米珍咬你,我讨厌她……”声音是那么的大!
我伸手去抚摸她稚嫩的肉痣,再也说不出话来。
第十三章 将爱情进行到底
国庆后,月经考试就来了。我再怎么努力也不过四百五。
纹身一事让我悲痛万分,当阿sa再次对我说:“刻了纹身不能参加高考,你以后找工作也不好找。”就为此,很郁闷。
在阿sa的安排下,我决定去洗纹身。至于那六百块钱的手术费,等以后有钱了再还给她。
星期六下午,她领着我到一家纹身店,老板说洗纹身比刻纹身时要疼些,叫我忍住。我问:“洗了后是什么样子的?”他转身叫来了一个伙计,说了几句,于是伙计把手臂伸了出来,指着那块白色的印记说:“洗了之后就变白了。”我凑过去仔细看了看,我认为那是一块白色的污点。
还记得以前学校叫我们填写档案时,老师一再强调不要有涂改痕迹,但我小脑还是不听大脑的指挥,写错了一个字,迫不得已将错字涂成黑色。于是,我的档案便有了“污点”。
我脱去衣服站在镜子前,以前很少仔细看胸口的纹身,也从未给阿sa看过。那朵玫瑰仍是那么的刻骨铭心,还有那个父字。我默然良久,最后穿上衣服一声不吭得走了。
阿sa追了过来,很气愤地对我说:“你妈的,耍个狗屁性格,给老子站住!”
我停了下来,蹲在大厦门口旁点上了一根烟。
“你到底还想不想考大学……”她迎了过来很用力地拽着我。
“算了吧,我想试试看刻了纹身可不可以考。”
“那我可以说,你没救了,你现在就可以去死了,别浪费国家粮食!”
她说得很坚决,我站了起来,拦下一辆摩托车,转头叫到:“走不走?”可她转身向背而去,无奈之下,竟自一人回家。
我无语地拦下一辆的士,回过头看见她蹲在商厦门口不肯走。
我急躁地喊:“走不走?”她没有回答,板着一副苦瓜脸。我钻进了车,弃她一人,竟自回家。就为此,她几天来板着个脸,不与我说话。我仍像往常一样负责接送她姐妹俩上学放学,只是没了语言。我向来不懂得安慰,即使想去安慰,但不知怎么开口。
十月中旬,天渐渐冷了起来,我的背又开始疼了。这是一年前就有的毛病,不用看大夫就知道是烟抽多了的原故,我靠在椅子上,顶着疼痛坚持上课。
晚上,冷风越吹越大,我终于忍不住开口说:“彬,帮我捶捶背好不?我特难受。”她停住了脚步,耷拉着脸走了过来。我取下挎包,弯着手指了指:“这里。”她紧握着拳头,重重地敲打着我本不粗犷的背,虽然有点疼,但还是舒服了很多。
五分钟左右,她终于开了口,说:“好了没?”我点点头,然后她又一声不发地走上了楼。我仰着头朝楼幢里喊:“明天早点起来,多穿点衣服。”她没回应,应该听见了。
第二天,我比闹钟早起两分钟,洗漱后踢了踢茜柏坡他俩的门,直到他们发出悠长的懒腰声。
对于我来说,早上能即使醒来,仔细地刷个牙,挽着女朋友的手走到学校,然后睡一节早自习,醒来后抽根烟,这是一天最顺心的事情。
阿sa顺着小路迎面走来,还戴上了眼睛,怕我只顾着往她楼下跑,没注意到街上的她。
脸色看上去有点慌张,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文静昨天没回来。”我接过她的书包扛在手上说:“这家伙肯定是泡网吧去了。”“我昨天晚上给她打了电话,她不接!后来她关机了。”
我拉着她的手说:“我们到网吧看看。”
来到他们常去的“有间网吧”。不见阿娇却看到了猩猩。他神情麻木地看着屏幕,一脸苍白,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洗了脸。
我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玩通宵啊?”“是你啊,快……有烟没,我招架不住了。”我整盒烟拿给她后说:“要上课了,我们先走咯!”“回见。”
见她没吭声,我说:“你妹妹现在肯定回学校睡觉去了。”学校对门的点心店站满了人。我说:“你走吧,下课后我拿给你。”她塞了几张零钱,然后走了。我等了很久,终于把钱给那个收营员了。按照以前的脾气,早就提着点心走人了。
回到教室后,猩猩已经吃完东西准备睡觉了。我端起书,度过这最煎熬的二十分钟的晨读课。
我睡得正甜时,阿sa来到我的教室将我拍醒,说:“文静今天没来上课,我给她打了电话,她关机了。”我半梦半醒地看着她,搪塞着说:“你先把早餐吃了,我帮你想办法。”她提着早餐闷闷不乐地离开教室。
第二节课后,她懒地上来,简单地一条短信说:“她还没上课。”我看了一眼,继续睡觉。
中午放学楼口相见,她一脸惨白,我冷冷地问:“电话还是停机?”她回:“我问了她同学,说她一上午都没来。”“大概是躲哪睡觉去了吧。”“不会,她几个好朋友都说昨天晚上没和她在一起。”我实在难以忍受饥饿之苦,于是又搪塞着说:“你回去吧,她可能回去了。”她走后,我快步来到学校食堂,惟恐饭菜一扫而空。
我一到食堂就看见肖茜站在那等柏森从拥挤的“高三专用窗口”端出两个饭盒。那嗷嗷待哺的样子,让我终于看到她做为女强人的脆弱一面了。
我走了过去明知故问:“柏森呢?”她指了指。我看见他被人群夹着那可怜的样子,不得不感叹他爱得如此深,如此艰辛。
柏森终于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端着两盘装满猪食的餐具走了出来。
我转身端起一个餐具往“高三三班绿色走廊”走去。
三班的住校生很多,因此,我们伟大的蜡烛——况江老师,专门为我们高三三班学生另开一灶,即使这样,还不及窗口那边方便。
我很羡慕那些住校生,第一是他们的成绩,在班里,成绩好的都出自与住校生;第二是他们腰包里的钱,因为住校生出去花钱的时间少,而且不怕贼偷,会将学业上的所得来冲淡遗失后百感交集的烦躁。
中国有句俗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样的思想让宿舍那股不正之风更加的猖獗。我之所以不住校就是因为第一,不喜欢闻别人的脚丑,对自己的味道情有独钟;第二,家里穷,买不起那些日常用品。
吃过饭,一个人在教室里抽着烟。教室难得如此静谧,显得有些孤寂。我取出小枕头准备睡觉,阿sa来电称妹妹没回家,我只得出校陪她去找。
我一边往她家楼下赶去,一边听她说:“文静从家里拿了两千多块钱……”
忙了一中午,走边了这个区域所有的网吧,不见其人。
凌晨,出于做姐夫的压力,我猩猩那伙在网吧上网,主要目的是蹲点而不是玩传奇!两点后,不见人,也不见QQ上线,于是发去消息及时报告,然后睡觉!天未明,我还是准时醒来了,在她楼下等了很久她都没下来,眼看就要迟到了。我硬着头皮给她家的座机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男的,从声音可以听出此时他老人家的情绪很激动。我颤栗地说:“叔叔好,何文彬起来了没有?”他嘶哑地说:“正要出门。”我还想说声“谢谢”或“打扰您了”或“麻烦您了”,他却不给我表现的机会,把电话挂了。
她一见我就哭了,我将烟甩去搂着她眼看着就要迟到了,却不知该往哪走。她执意要去网吧用Q和阿娇留言,我只能给艾叶打电话,叫她晨读课的时候坐我那个位子。当她又要给我做思想教育的时候,我不给她表现的机会。
阿sa只是简单地留下一句,“你在哪?早点回去,妈妈很着急。”
然后她起身打开一个叫泡泡堂而并非泡泡糖的游戏界面,在一个消息筐上打了个/who**,回车后弹出一个资料,说她已经断开连接。她叹了口气,结帐后走出了网吧。
“你和她一般都去哪玩?”“网吧,KTV,酒吧。文静很少一个人出去玩,基本上都是和我在一起的。”她说的地方,除网吧外,都是关的。而且以QQ和泡泡堂可以排除此时她在网吧的可能性。
“我说别找了,你看你眼睛都黑了。你到我那睡一会,我喊人帮你找。”
她喝了一瓶牛奶,躺在床上没多久就睡了。我刚一站在阳台想叹口气,雨就下在地上。我摸出手机按了按,于是想起了程昕。
“程昕,是我。”“哦,你呀。”“我找你有事。”“下来吧,我在盥洗室的。”“我没在学校。”“什么,你又旷课啊?”她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十几分贝,或许她担心我在外边又惹事了。“我高一的一个妹妹离家出走了,我找了一天都没找到。”“你哪里又钻出个妹妹来了?”“表妹,她有可能跟外面的人跑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下?”
她换了种语气说:“有困难找警察……喂,我哥现在在睡觉,这样!我给你叫一个人,让他帮你找。我先挂了!”
十几分钟后,她打了过来,说:“他叫二黑,小灵通是***,他叫你九点钟到槟槟吧门口等他。但是他不一定能帮你找到人,你最好还是去报警!”
离九点还有一个小时,我回到卧室,她躺在床上睡得很深,眉毛好像在抵触着什么,皱得很紧。
离九点还差半个小时,我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件外套,举着伞往槟槟吧走去。
槟槟吧的门是开着的,大概二黑哥在里面。我走了进去,先是叫了声槟哥,有人走了出来。细一看,那人就是二黑。我叫了声:“二黑哥,我是程昕的朋友。”
在昏暗中他划燃打火机照了照,打开了一盏等。“来了啊,过来坐。”
我坐在弹簧圆椅上,面对着他。他看了看手机说:“把你那件事情说一下。”
我拿出一包烟,递了过去,他指着喉咙说:“刚醒来,喉咙不舒服。”
“是这样,前天我妹妹从家里拿了两千多块钱离家出走了。昨天我找了她一天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