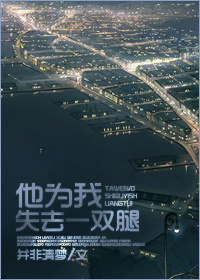西班牙别为我哭泣-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帝吗?又是那些虚无缥缈、玄之又玄的东西!为什么总是那些东西在主导我的生活和悲喜?
我跟他们有仇吗?为什么当日他们要那样耍我,先给我诸多的好消息,每件事都是那样美好的开端,最后又统统给我那样残酷的结局不,岂是一句残酷了得,是毁灭。每个大结局都足以毁灭我的生活,它们也的确做到了,那一天之后,我的生活变成了一片废墟,四面坍塌,十面哀歌。
第十四章:一个婚礼与两个葬礼
天开始大亮了,从窗外望出去,不得不说,荷兰的确是个漂亮的国度,有漂亮的房子,也有漂亮的风景,还有漂亮的河,漂亮的天空。在这个早晨,在这个圣诞节的早晨,一切显得宁静而美好。我已经开始帮二宝屋里屋外试婚纱,试鞋子,一会还有专业的化妆师来给她化妆,其实无论化妆与否,二宝就像荷兰这个国家一样漂亮而风情万种,她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她该嫁得好,嫁得美满的,想不到却是这样。
他们的婚礼二宝甚至没有知会父母,她说以后再说,免得多生枝节,她要顺顺利利地嫁,不想有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差错。她说,“人生最怕的就是错过,这个错是错不得的。”
这样,请的嘉宾也都是男方的朋友,我竟是唯一的女方的宾客。种种的事宜我都有些替二宝不值,但是看得出一切表面的东西对于二宝都不重要,她唯一看重的只是茱笛洛这个人。我只有心中碎碎念:二宝你可不要后悔啊,你可永远不要后悔啊。
化妆师来的时候,茱笛洛陪着二宝在房里,他们倒真的做戏做全套,眼光之间露着甜蜜的神色,我识趣儿离开,去厅里坐,这样,厅里就剩下了我和茱笛洛的男朋友,我也是第一次打量他二宝的情敌,的确是个很漂亮的男人,长发,俊美,身材略魁梧,最迷人的是有一双深邃的蓝眼睛。
我绷着脸问他:“可以说英语吗?”
他腼腆地点头。
“我叫乔竹。你可以叫我乔。”
他也自抱家门:“杰蕊。”
我问,“看过《亚历山大大帝》吗?”那是好莱坞的一部同性恋电影,说的是亚历山大王与好友赫费斯提翁之间的暧昧关系,由于内容敏感,曾引得很多历史学家的不满,甚至把电影公司告上法庭。
他点头,恍惚明白了我在说什么。
“那你怎么看待里面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呢?”我有些针锋相对地问,语气也有些不善。
他想了想说,“记得里面有段台词,好象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他说如果男人出于性欲而同床共枕,那是对情感的屈服,对我们没有好处。其他所有放肆的行为也是如此,他们彼此之间只有嫉妒;但如果同床共枕的男人之间,交流的是知识和美德,那就是纯洁的,高尚的,他们为了追求卓越而竞争,这对双方都是最好的,正是这种男人之间的爱,能够建立城邦,使我们脱离坐井观天的境地。”
他的话大出我的意料,他这样侃侃说来,我反而不知说什么了,只能用蔑然的口吻道:“你似乎觉得同性之间的爱很伟大?”
“谈不上伟大,但也绝不卑微,绝不龌龊。”他也针锋相对地看着我:“很多时候我觉得,同性之间的沟通更为深刻,因为同样的身体构造,原谅我不会用更柔和的语言,使得他们有同样的思考方式,理解对方的想法。嗯,嗯……”他蹩着眉寻找了一下需要的单词,最后总结性地说:“他们理解对方,这种理解不是异性间的支持,而是感同深受,他们的爱是有意义而不会动摇的。”
我笑言:“爱?不会动摇?亚历山大最后还是娶了别的女人,而不是赫费斯提翁!”
他显然被我的话说得难过了一下,但还是不认输地说:“亚历山大给赫菲斯提昂的是感情的忠诚,不是身体的忠诚。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欲望、金钱、名誉、责任,有太多东西诱惑着我们,束缚着我们,作为人,能做到忠于自己的感情已是不易。”
我想二宝遇上了一个厉害的对手,婚后,感情的PK台上,她要怎么打败这个外柔内刚的男人呢?
我忽然伸出手,握住了杰蕊的手,我几乎想求他,求他退出这场三角恋,看得出他与茱笛洛感情极为深,不是都会人的放纵,或所谓成年人的游戏。二宝说,他们是自小认识的,茱笛洛的父亲就是球队的医生,而杰蕊是十几岁入少年队,直到成年队,踢职业联赛,两人认识已有十余年头。我颤抖着说,“我想,只有你肯离开茱笛洛,茱笛洛才能好好爱她的妻子,好好对待房里的女人。你不觉得你们对她不公平吗?”但就是这个时候,电光火石之间,我忽然听见房里有玻璃破碎的声音,接着传来二宝隐隐的哭声,我来不及再对杰蕊说什么,冲入房内。
二宝正对着电脑掉眼泪,茱笛洛无措地站在二宝身边,二宝的头靠在他的腰间,面如土色。我走过去问二宝怎么了?我并不知道继二宝的荒唐婚姻之后,又将面临今天的第二个悲剧。当时当日的我更不知道悲剧的特性与特质:当悲剧来临,上天总是喜欢把悲剧乘以二,或是干脆二次方。悲剧是绵绵不绝的,每每来临就一次性伤人于底,不留余地。
二宝在哭,视频那边的小四也在哭,我意识到是我们中的一个人出事了。
“二宝,二宝,怎么了,啊?怎么了?说话啊!”我大吼。
二宝哭着道,“是小三。”
“她,她怎么了?”
“她,出了车祸!”
“怎么可能…”我话一出口方想得,荷兰是早晨,中国现在是后半夜才对,小三和他的雪山王子确实说过夜里开车去小四家…那么…,我拿起耳麦,我大声问小四,“到底怎么了?说明白啊!”
小四已哭得不成样子,她老公也被哭起来了,正在安慰她,可小四还是痛哭不止,泣不成声:“她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说是有三辆车追尾,报的车牌号码正有她们那辆车…”
“你从哪里知道的消息?多久之前的事?”
“我正在听一个电台点歌,是交通电台报的,有半个小时了。”
我的头嗡地一下,但很快恢复清醒,冲小四喊道:“那你还愣着干吗?哭有什么用啊,你快顺着路去出事现场啊。小四,我们保持联络,你去看看情况如何,严不严重,随时来电话,我们等你电话,好不好?啊?”
小四这才缓过神,拉着老公就往外跑,电脑也没有关,留下房内一片凿凿灯火。深更半夜的,好在他们有车,可以开车去。好在他们离得不算远,好在他们在一个国家,好在他们在一个省,好在,好在……我默默地坐在地板上,脑里全是乱七八糟的影子,乱七八糟的假设,再多的好在有什么用,最坏的事已经发生,再多的好在也只是安慰自己。
屋里刚刚乱作一团,我来时拿入屋里的牛奶杯子碎了一地,这会儿,茱笛洛正在打扫,杰蕊也跟着帮忙,之后两个男人就为我们关上门,退了出去。他们也知道是我们的姐妹出事了。
坐了一会,我觉得心跳得没有那么乱了,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7点20了,我问二宝,“一会儿还去教堂吗?还举行婚礼吗?”
二宝倏地站起来,重新打开门,她的脸难看得就像被刷花的白灰墙,还有泪水留下的泪痕,好几道印在双颊。她阴冷着脸,阴冷地重新叫化妆师进来,然后转回头阴冷地对我说:“今天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叫我不举行婚礼。”
她这样说,她居然这样说……我什么都没有再说,继续坐在地上。我觉得我的身体从里到外的沉重,几乎要用尽所有的意志才能站得起来。
我目睹着二宝的脸渐渐有了血色,渐渐从惨白变得滋润,头发一点一点被分为几绺,用卡子卡为小波浪状,之后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小妇人。只是再多的粉底打下去,还是盖不住她眼睛下的凝重,那就像是一股阴冷的风,从眼睛内吹出,然后吹遍整张脸。在这份凝重下,二宝的美丽就像是胭脂沾染了灰,再无法做到晶莹剔透,白壁无暇。当然,这份凝重也只有我看得出、看得见。她把自己掩饰得太好了。
她已经学会了掩饰,并且已决意后半生都掩饰着做人,掩饰着为人妻了。我想我是不该责怪她的,她心里是难过的,只是这场婚礼对她太重要了,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是生命中渴望承受之重!
我终于站起来,上前装模做样端详了二宝一番,然后故作惊艳状,惊呼:“you are so beautiful!”之后轻轻地说,“8点了,我们该走了。”
走到厅里,新郎自然又赞赏了一番新娘的美丽,杰蕊也夸二宝是他见过的最美的新娘。我和他对望一眼,我这个伴娘和他这个伴郎各怀各的心事,却在这一瞬间,两个陌生人之间突然好象有了某种理解,我们都说着言不由衷的话,都做着不由自主的事,生活就像一场糟糕的演出,我们都是不合格的演员。
开车去教堂只要15分钟,一路上晨光闪亮,风光乍泄,还有漂亮的阳光,及动人的湖光,谁也看不见无限风光背后藏着的暗涌,谁也猜不出上帝之手此刻正伸向哪里,谁又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圣诞之夜会变成这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车里我点了一根烟,是很劣质、很粗糙、很辣的那种。我不常吸烟,但包里却永远放着一盒烟和一个打火机,我也说不清自己什么时候就需要它,比如今天,比如此时此刻。茱笛洛对我的举动大吃一惊,他说:“本来以为东方女孩子是不抽烟的。”
我便吓唬他说,“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别以为东方女孩子都是温温顺顺的小绵羊,告诉你,东方女子是欺负不得的!”
其实我是不会吸烟的,抽的过程自己也被自己呛了好几次。杰蕊嘴角带着若有似无的笑看着我,我看不出他是仅仅觉得好笑还是有嘲笑的味道,我躲开他的笑容,因为我已知道谁都不会笑一辈子的。
教堂在城市的东面,是个典型的哥特式建筑,是那种一见了就让人想喊圣母玛瑞亚的大教堂,二宝他们是今天的第一对,可是牧师还没有来,我们就在教堂外等待。不少来观礼的亲戚朋友已经到了,包括二宝未来的公公婆婆,都是很优雅的人。
我不停地看手机,不停地来回踱步。我承认我已经比以前冷静多了,但此刻还是静不下来。甚至,我当时还做了一个外人看来有点滑稽的举动,我先行一人跑入教堂,跪在大殿下方,开始祈祷:“圣母玛瑞亚,上帝,耶稣:我,乔竹,是不信教的。但现在我跪在这里请求你们一家,请你们保佑小三和她男朋友没事。小三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心没有恶意的人,请你们让她继续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她不会做恶的,你们永远都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永远都不会后悔拯救这个人。神啊,请怜悯她!神啊,请救救她……”
我正说着,手机响了,我祈祷是神有了心感,听见了我的呼唤与求救。作为人类,号称万物之灵,可有时我们是这么无助与无力,太多事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
“喂,小四吗?三儿怎么样了?”我迫不及待地问。
“是妈妈,小竹,是妈妈。”
“妈,怎么是你?哦,今天是圣诞,妈,小三出车祸了……”我带着哭腔说。
“小竹,你听妈妈说话好不好?”
我心里一直想着小三的事,直至此时,我才觉出妈妈的口吻不同于平常、不同于任何时候,“妈,你怎么了?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啊?”
“小竹,我觉得你已经长大了,无论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