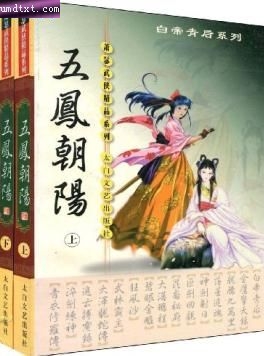金鸡朝阳-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老家在厦门,这两年每逢他的祭日我都会上厦门给他送束花,所以那天很巧遇上你。”她说。
我点点头,很想和她谈点什么,那种很深很有蕴涵的东西,可是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是莫名其妙的指了指桌上的花。她起身去阳台取了个花瓶,边说:“我有送他的遗体去火葬场,那火化的场面我见识了,好恐怖。”
“我们老家还兴土葬,不知你见识过那场面没有?”我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她摇了摇头,我继续道:“用口棺材把死人装了,再到山上寻块地方刨个坑,埋进去。过个三年五载的,棺材受地下潮气所侵,慢慢腐坏,那些老鼠和蛇什么的便钻了进去……”我和她就这样有一茬没一茬的聊到半夜。
我起身要走,她送我到门口,送我一本书,是钱钟书的《围城》。下楼时,我轻轻问了一声:“你明天去报社吗?”她没有回答,我便走了。
我一夜没睡,读完了围城,那不知道读过多少遍的小说。里面满是令人捧腹的东西,我却没有一丝笑容,每每读到后头倒颇有荡气回肠的感受。我现在总算明白了吴副总编会对她有那样的评价,她不正是孤独的被困于她死去的男朋友的围城里而苦痛挣扎,渐显忧郁。要想走出围城,是艰难的,不难于围城,而难在于该怎么走,不然,走字下面也不会是两个人。所以,人需要人。
第五章 围城 (上节)
5
6月11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待我赶到亚兰姐家的时候,吴副总编已经做好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我打趣道:“你还有这般手艺,当真是男人中的楷模,却愁找不到爱人。”他解了围裙,递给我一双筷子,说:“你先尝尝,看看味道如何?能打多少分?”我正要下筷,亚兰姐回来了,吴副总编忙上前迎接,嘘寒问暖。亚兰姐在我旁边坐下,笑说:“偷吃啊!”我指了指吴副总编,说:“老吴怕他技艺不精湛,让我先点评一下。”
“怎么样?”她也下了筷子,一边从包里取出一瓶香格里拉。
我在楼下超市里也买了一箱啤酒,正弯下腰去开箱,亚兰姐忽然拍了一下我肩膀,说:“听阿吴讲你最近恋上了社里的刘琪儿,真的假的?”我从箱里取了两瓶啤酒上桌,还没开口,吴副总编就跳上来道:“简直是失魂落魄,相思成狂啊!兰子你没在社里不知道,他整一失心疯,可惜的是,他上班的第一天起那刘琪儿就没来过。”
“别听老吴在这瞎说。”我笑着给她倒了杯酒。
他埋怨说:“社里面谁不叫我小吴,就你一个喊老吴,男人三十一朵花,何况我还没三十,正植含苞待放呢!”
亚兰姐笑的前俯后仰,吴副总编也跟着嘿嘿的傻笑,我自然也笑了,开心的笑,为吴副总编那少有的一份烂漫,为亚兰姐的开心,看的出,现在的亚兰姐是幸福的。在这开心的笑里面我内心油然而生一种寂寂的落寞和一丝隐隐的伤痛,因为我感受不到我的幸福快乐。记得我曾跟阿亚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对社会还有用的人才会感到幸福。”我相信我这句话是对的,但我不敢肯定这是对幸福真正的诠释。我仔细回味,自己似乎没有过真正出自内心可以奔放驰骋的快乐和没有终点只有永远的幸福,就如同我现在的笑,开心的笑,也只是为别人的开心而开心,这让我错愕了,无奈了,脸上开心的笑渐渐变的僵硬了。我怕他们发现我这虚伪的笑,忙拿了筷子,说:“开始吧,一会菜凉了。”
“亚云还没来呢,再等等。”吴副总编说。
我复又搁下筷子,说:“还有人呐?”
“我妹妹,程亚云。”亚兰姐看了看表,说:“也该到了。”
我一脸欢喜,知道这个程亚云就是我最亲密无间的网友——金鸡。认识这么久,也很想一睹她的庐山真面目。
“让你们久等了。”门被人推开了。
我惊鄂万状,这使得我从坐着的椅子上站了起来,我的瞳孔以光的速度迅速扩张到极限来证明浩瀚的空间真的有渺小的时候。她站在门口僵住了,而她脸上的表情却不断的在我的瞳仁里变化,从一开始的惊讶发现到错愕茫然,转而瞬间的无限喜悦,再而顾忌所生的忧心仲仲,到最后的的恐慌。她竟然是阿亚!程亚云就是阿亚!金鸡就是阿亚!
我被她的恐慌激的动了一下,我明白她的恐慌,同样也恐慌于她的恐慌。我忙蹲下身到桌底下取啤酒来掩饰我的恐慌、我的惊鄂万状,我不能让亚兰姐知道她这位白领妹妹金鸡就是北京城里地地道道的‘鸡’,一个靠出卖肉体出卖灵魂来换取一切的女人。
亚兰姐正在开启那瓶香格里拉,阿亚故作镇定的坐到了我的右首。我刚放了啤酒上桌,只感腿上传来一阵剧痛,她猛的在掐我,我手指一弹,打中她的腕关节,她痛的松了手,不敢作声。我脚尖一挑敲扣她的足裸关节,她坐在椅上反射性的一个前扑,额头碰在桌面上撞的生响。亚兰姐吓了一跳,忙询问道:“怎么了?”她揉着额头,摇了摇手,说:“脚抽筋。”亚兰姐又是一番不停的嘱咐。她听的烦了,装作一脸陌生的看了看我,问吴副总编:“他谁呀?蜈蚣。”
吴副总编回答:“同事兼好友,你姐认的干弟弟,社里副刊的编辑。”
亚兰姐开了酒,我放下筷子,说:“我去取几个杯子来。”便起身去了厨房。阿亚也跟了进来,我不作声,取了四个杯子要出去,她一把将我拽住推堵在墙角里,说:“我现在暂不管你和我姐是怎么认识的,你要是敢在她面前乱说,我——”
我猛的一把将她搂住,吻住了她的唇。本想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安定她恐慌的心,没想吻下去之后心里却激动的厉害,在这样的场合我居然可以做到忘乎所以,如此的投入。她的双唇很丰盈,很性感,上面有玫瑰花唇膏的香味,这样的香味是热情奔放惹人情迷的,她双手慢慢缠住了我的腰,开始迎合我强烈的吻,柔滑细腻的鼻尖在我鼻子上肆意摩挲,那呼出的暖暖气流喷散在我的脸颊上,强烈刺激着我迷茫的神经。她的舌技是高超的,两行贝齿轻咬着我的下唇上下拉扯,再而上唇左右牵移,我迫切的想得到更多,亢奋的张开了嘴,她的舌头蛇一样的滑了进来,舌尖在抵触到我舌头的时候,迅速的蜷曲,灵活的添舐,强而有力的吸吮。我能做的只是将她抱的更紧,融合她高耸的胸脯和剧烈的心跳所带来的无限美妙。
“啊——”一声尖叫。
吴副总编的突然出现让我俩的激情冲散的支离破碎。我一把将他拉到面前,他忙解释:“我见你们这么久没拿杯子出去,进来帮忙的,我什么也没看见啊。”我笑:“你不会暗地里跟亚兰姐告密吧?”他一手攀上我的肩膀,笑道:“我们是新社双龙,人生目标便是进攻程氏姐妹花。不瞒你说,我还预备明天给你修栈道,没想你今天就暗渡‘程’仓了,好!”阿亚轻啐了一口:“死蜈蚣。”便出去了。
晚上,我睡吴副总编家。
“喂,我告诉你,刚才下楼的时候我跟兰子她求婚了。”他兴奋的在床上乱颤,说:“我趁她不备吻了她一口,你知道这可是我的初吻,那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你猜她什么反应?”他看着我稍微顿了一下,开心道:“她笑了!”
“很贼。”我笑,“不宣而吻是为偷心,你个偷心的贼。”
“五年了,才这么蜻蜓点水一下,你和阿亚才刚认识,就是狂轰烂炸式的。”他对我又是佩服又是羡慕,得意道:“不过今天的表现在这五年里是最突出的一次,这还多亏了你那狂轰烂炸式的鼓舞。我自认还有待学习,你多指教啊!”
“我看你是得努力了,往日老吴今日吴公(蜈蚣)。”
“我一花样美男……”
我背过了身去,他便转发牢骚:“你老是打击我,是不是想单飞,想解体啊?我们可是双龙,要团结,要为我们的人生目标而奋斗,知道‘团结就是力量’怎么唱吗……”
我就这样在他的牢骚中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还听他在发牢骚,我厌烦的踹了他一脚,没动静,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他竟然是在梦呓。
“蜈蚣,蜈蚣啊!”是阿亚在楼下喊。
我下了楼,亚兰姐便问:“阿吴呢?怎么没一起下来?”
“兰子……兰子……亲爱的……哦……兰……”我憋着嗓子扮吴副总编的声音。
亚兰姐一脸桃红。阿亚一边扮鬼脸,说:“看不出死蜈蚣他还有这么肉麻。”
“谁在数落我?”吴副总编提着公文包,匆匆忙忙的赶下楼来。
我摇头叹气,一脸担忧道:“亚兰姐她嫌你昨晚上那个戒指太小,套不到指头里去,你那点美事想必要告吹了。”吴副总编诚惶诚恐,搔耳挠腮道:“我马上就去再买一个,兰子你千万——”亚兰姐向她摆了摆手,早上和熙温馨的阳光让她指间那枚炫耀夺目的戒指更加璀璨。他紧张的脸色迅速舒缓下来,叫喊着要拿我试问,叫阿亚瞪了两眼,跟个痿焉了的黄花一样立马软了下去。
第五章 围城 (中节)
一到报社,我眼睛一亮:刘琪儿来了。她戴了一顶鸭舌帽,正冲我微笑,我跑上前,本想热情的打个招呼,站到她面前却大吃一惊,看不到了她乌黑的鬓角和肩后美丽的长发。她保持着微笑,从容的摘下了头上的帽子。天啊!她竟然理了个光头。我能很清晰的听见周围同事的窃窃私语和投来的异样目光。
“是不是得白血病了?”
“染爱滋了也不一定。”
“变本加厉了,邪!”
……
虽然,她的美丽依然,但乌黑靓丽的发丝不覆存在让我对她感到些许的陌生,那份心底里的为之可惜为之动容不知道她明不明白?可同时我又不得不佩服于她的勇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纵然再怪再不合群再怎样前卫大胆也不能牺牲自己的美,尤其是一个女人,为之更甚的是一个女人的头发。她却这么做了。
她朱唇轻启,声音很低,似乎只是要告诉我一个人:“我准备这一刻起,重新开始,从‘头’做起。”这是我听的她说的最为坚定的一句话,低微的声音里所爆发出来的铿锵有力让我不得不折服,她这才是真正的勇气。我从她手中拿过帽子,给她戴上了,微笑道:“你终于从围城里走出来了。”她的回答让我很讶异:“我又掉入了另一个围城。”我迫切的问:“为什么?”她平静的说:“其实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围城里,就算你穷其一生不惜一切的走出你的围城,那也只是更快的进入另一个围城,就这样在不同的围城里进进出出,便形成了所谓的人生。人生的坎坷在于对自己的围城所不满和不安,人生的希望便变成了在围城里渴望进入外面的另一个围城,从每个人出世的那一刻起。就算死亡,也是掉入了地狱的围城或是飞升到了天堂的围城。”这就是她的逻辑?她的思维似乎与众不同,我感觉自己在听一个神话一样的论证,可又寻不出她说的哪里不对哪里牵强。
我和她并肩出了报社,躺在了外面一个小公园的草地上。她斜斜的躺在我身边,气息恬静。我望着天,阳光很刺眼,照在身上却不那么热辣,我的呼吸也很平静。好久,我几乎要睡着了,她问我:“在你心里,你的围城呢?”我一时茫然,还真没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可我回答的很干脆:“我没有。”按照她的逻辑,我的围城是铁定有的,这样我就不知道我的回答是不是欺骗。
“你有的。”她很执着。
我无法回答了,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