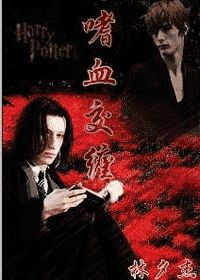大外交-第1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与社会状况已败象显著。1991年他黯然下台时,苏联军队宣布支持其政敌叶利钦,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自从彼得大帝以来历代俄罗斯统治者血腥征服组建的帝国已四分五裂。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被选为苏共总书记时,若有人谈到苏联崩溃,一定被视为荒诞想法。戈尔巴乔夫和他之前历任苏联首脑一样,令人惊惧,也给人希望。惊惧,是因为他是一个谜样的超级大国的领袖;希望,是期待这位新任总书记或许引导大家走向期待已久的和平之路。戈尔巴乔夫的每句话都被拿来分析,检验是否有缓和紧张关系的迹象;情感上,民主国家期待能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发现新时代的曙光,也正如他们对斯大林之后历任苏联领导人的期待一样。
这一次,西方国家的希望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戈尔巴乔夫是另一代人,与受到斯大林威吓的苏联领导人不同。他缺乏前人的强悍作风。非常聪明又温文尔雅的他,像是19世纪俄国小说中的抽象人物——既见过大世面,又不脱乡村气息;聪明绝顶,但不专精一技;有远见,但见不到眼前的主要两难困境。
外界几乎松了一口气。期待已久的、难以捉摸的苏联意识形态之转型,似乎终于到来。直到1991年以前,华府一直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建立世界新秩序不可缺少的伙伴——布什总统甚至选择乌克兰国会这一个让人料想不到的地点,发表演说,称颂这位苏联领袖,并且倡言维持苏联完整不分裂的重要。支持戈尔巴乔夫在位,成为西方决策领袖的主要目标,他们认为换了别人当家,都不好打交道。1991年8月显然是针对戈尔巴乔夫而爆发了一场奇怪的政变,所有民主国家领袖都站在“法统”这一边,支持把戈尔巴乔夫拥立出来的共产主义宪法。
但是,高层政治绝对不能容许有软弱的情形——即使失败者本身不是软弱的主因。戈尔巴乔夫以一个意识形态上敌对、核武力强大的苏联领袖,却带着修睦心态出现时,其魅力达到顶峰。当他的政策反映出混淆而非目标时,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开始下滑。政变失败后过了五个月,戈尔巴乔夫被迫辞职,由叶利钦通过五个月以前西方国家大为不满的“非法”程序,取得政权。这次,民主国家迅速表态支持叶利钦,其论据与早先支持戈尔巴乔夫者大体相同。戈尔巴乔夫在外界由声名显赫沦为无人理睬,只得壮志未酬地含悲隐退。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缔造了当代意义最重大的一场大革命。苏联共产党组织起来,只有一个特定目标——夺权、抓权,事实上它已经掌控了苏联人民生活的每个层面;戈尔巴乔夫却摧毁了共产党。然后,数个世纪辛苦建立的帝国,也在戈尔巴乔夫治下瓦解。苏联帝国瓦解后的各个独立共和国却担心俄罗斯仍缅怀昔日帝国大梦;她们又变成不安定的新因素,因为她们不仅受到昔日帝国主义的威胁,同时更因为俄罗斯人主宰她们百年,已在境内迁入许多不同种族族群——通常以俄罗斯人势力最盛——而备受威胁。这些结果绝非戈尔巴乔夫本身所规划。他要促成现代化,不是自由;他想要苏联共产党与外在世界接触,不要故步自封;可是,他却推动了把他送上权力宝座的那种制度的覆亡,进而享有历史声望。
苏联人民怪罪他在任期内肇致重大灾难,民主国家遗忘了他,而且他无法保持住权力宝座也让他十分难堪。其实,戈尔巴乔夫不该受到如此的盛赞与贬抑。因为他继承了一套真正棘手,甚至可能无法克服的困难。戈尔巴乔夫继承权位时,苏联灾厄之规模才开始显露出来。四十年的冷战,几乎使得全体工业国家都集合起来,组成一个松散的反苏同盟。苏联早先的盟友中国,基于实际理由也加入反苏阵营。苏联只剩下东欧附庸卫星国家做盟友,而他们是因忌惮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主义代表着苏联资源的流失,而非积累)隐含的苏联军力威胁而不敢有二心。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冒险行动,不但耗费巨资,且没有结果。苏联在阿富汗重蹈美国在越南的覆辙,只有一项大差别:阿富汗是苏联广袤的帝国紧邻的一个邻国,越南则与美国相距千里。从安哥拉到尼加拉瓜,美国重振旗鼓,使得苏联的扩张主义所费不赀仍停滞不前,甚至含愧认输;同时,美国的加强兵力(尤其是推动战略防御计划)在技术上做出重大挑战,可是停滞且负荷过重的苏联经济开始无法应付。西方国家发动超级电脑、微晶片大革命之际,苏联这位新领袖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技术后进国家。
虽然最后是失败下台,戈尔巴乔夫肯面对苏联的困境则值得嘉许。起先,他似乎相信借由整肃共产党,引进若干市场经济因素灌输人中央计划,他可以使苏联社会恢复活力。虽然戈尔巴乔夫事先不知道他的作为在国内的冲击力会那么大,他却知道他必须争取到一段国际间平静的时间才能施行其内政作为。就这一点而言,戈尔巴乔夫的结论与斯大林死后所有历任苏联领袖,并无多大不同。但是,赫鲁晓夫在50年代依然认为苏联经济即将赶上资本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在80年代则明白,苏联要花相当长时间才能勉强达到堪可与资本主义世界相竞争的工业生产水平。
为了争取此一喘息空间,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政策发起重大评估。在198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届代表大会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几乎完全遭到摒弃。过去和平共处的时期被认定是暂时休止,以便重新安排势力均衡,仍然存在阶级斗争。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位完全摒弃阶级斗争、并且宣称和平共处本身就是目标的苏联领袖。虽然继续申言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戈尔巴乔夫同时也在坚持,国际合作的需求已超越了它。甚至,和平共处被认知的意义——是无可避免的冲突对峙的前奏曲——也与过去不同了;现在被视为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之固定的成分。它之所以存在,不是当做走上共产主义必胜道路中的一个阶段,而是因为对全体人类福祉有贡献。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著作《改革》(Perestroika) 书中,描写他的新做法是:
“确切地说,区别仍然存在。但是,难道我们应该为了它们而决斗吗?更正确的做法难道不是跨越使我们同全体人类利益分离的事物?同全球生灵分离的事物?我们已经做了抉择,坚持借由有约束力的声明及明确的言行举动而重申新的政治前景。人类已厌倦紧张与对峙。他们宁可追求更安全、更可靠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里,每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哲学、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以及生活方式。”
戈尔巴乔夫在两年之前,也就是1985年与里根进行第一次高峰会议后,在记者会中已暗示过这些观点:
“今天的国际局势是由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来区分,我们与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必须考虑此一特征。我的意思是: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说的不只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对峙,而是在生存和相互歼灭之间的抉择。”
无可避免地,对冷战经验丰富的人很难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方法比起从前的和平共处时期,会走得有多么更远?1987年初,我和已转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约略相当于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勃雷宁,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党部大楼会面。多勃雷宁对于莫斯科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有许多轻蔑评语,我遂问他,勃列日涅夫主义还生效吗?多勃雷宁却吼起来:“为什么认为喀布尔政府是共产主义政府?”
我向华府报告,指出多勃雷宁这句话似乎暗示,苏联可以随时抛弃克里姆林宫的阿富汗傀儡。一般的反应是,多勃雷宁为了想讨好老朋友而失言——我在将近十年里与这位“秘密渠道”的苏方代表来往时,却从来不知道他有此一特质。虽然如此,这种怀疑还是有道理,因为戈尔巴乔夫对外交政策的教义上之转变,尚未立刻化为政策上明显的转变。苏联领导人只是反复学舌,形容他们的新教义是“剥掉西方是敌人的印象”之方法。戈尔巴乔夫1987年11月宣布的此一“新思维”,“开始为世界事务开辟新途径,摧毁掉反苏的定型观念,以及对我们言行建议的疑忌”。苏联在武器管制谈判上的战术,似乎是重演他们在尼克松执政初期的战术——全面取消防御系统,却把更要紧的攻击系统搁置不谈。
大国的政府好比是一艘数十万吨的超级大油轮,掉头转身的半径面积至少就数十英里。它的领袖在寻求对外界的影响时,也得考虑如何平衡对本身官僚体系士气之影响。政府首脑固然享有职权去建立政策方向,但是诠释首脑构想的工作却落在政府官僚身上。政府首脑也几乎不会有时间或幕僚,通过执行上的每一细微差异去监督日常指令实施的状况。够讽刺的是,官僚体系越是庞大、复杂,就越会出现这种情形。即使不如苏维埃制度那么僵化的政府,政策变革的步伐经常也是极其缓慢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巴乔夫在理论上的转变已无法回避,即使葛罗米柯担任外交部长几近30年所组建的官僚班子也不能不面对它。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已经远超过调整苏联既定政策符合新现实的步调;它彻底破坏了历代苏联外交政策的支柱。当戈尔巴乔夫以威尔逊派的全球相互依赖论,取代阶级斗争论之时,他界定的世界是一个有相容利益的、和谐的世界——完全推翻了长久以来的列宁主义正统以及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的崩溃不仅使得苏联外交政策失去历史上的理论基础和信念,也让苏联局势中固有的困难加剧。在80年代中期,苏联决策者所面对的任何一个问题都难以应付,统合起来,更是无法克服。这些问题有: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附属卫星国家中的紧张关系;武器竞赛;国内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停滞僵化等等。
戈尔巴乔夫起初的行动仍然不脱离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标准模式——借由气氛的营造,设法缓和紧张关系。1985年9月9日《时代周刊》刊出一篇戈尔巴乔夫访问记,他针对和平共处提出见解:
“你问我,界定苏、关关系的主要事项是什么?我想,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对方,我们都得共存亡,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我们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是否终于预备承认没有其他方式彼此和平生活,以及我们是否预备把我们的心态和行为方式,由逞强好胜改为和平。”
戈尔巴乔夫进退维谷的两难是,一方面他的谈话符合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30年前所说之背景,另一方面,却又过于模糊,不足以鼓舞明确的反应。缺乏政治解决方案之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身陷在二十年来的正统论之内;这20年来东西方外交被认为等同于武器管制。
武器管制变成一个深奥难解的题目,即使有心人也得花费多年工夫才能解决。但是,苏联需要的是立刻解脱,不只要解脱紧张局势,还要脱离经济压力,尤其是跳出武器竞赛的怪圈。通过旷日持久的程序,确立协议的兵力水准、比较难以比拟的系统、交涉难懂的查证程序,然后再花费数年时间去执行它们;凡此种种都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因此,武器管制谈判成为对已经压力沉重的苏联制度施加压力的利器——由于它原本不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