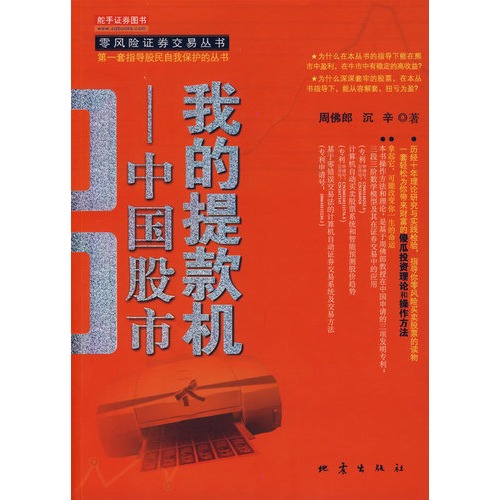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8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少出生人口 28.53 33.96 27.60 36.50 126.59
根据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计算方法见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一章)大饥荒期间,云南省人口变动情况,即非正常死亡近50万人,少出生人口近130万人。表101中最下面两行就是本书作者计算的结果。当然,这是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数据要严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的结果是,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云南非正常死亡80万,死亡率为4.2%。他没有考虑云南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
一、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由于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新政权接管云南以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采用内地那种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和平协商土改的政策原则是:“在保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基本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主从政治上、经济上作了适当让步。”“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不分其它财产,并保留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杀,除现行犯以外不捕,并一般不剥夺政治权利等”。边疆地区土地改革到1955年底才基本完成。
说是和平协商,实际上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和平协商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待政策、发动群众,组成农民队伍;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这一阶段要向地主阶级进行“有控制的、有领导的面对面的说理说法斗争,全面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第三阶段是没收征收土地;第四阶段是分配土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以后,地主富农不敢请工,也不敢拿粮食到市场上去卖。农村借贷关系也停止。坝区(云南称山间盆地里的小平原为“坝子”)和内地历年有大量粮食流入边疆和山区,1956年,因坝区和内地土地改革,流入边疆的粮食大量减少。再加上沿边一线边防工作加强,1956年3月以来部队向边沿一带推进以后,边民出国帮工和购粮也大为减少,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农具和牲口。所以,1956年以来,边疆地区粮食问题十分紧张。思茅地区1956年5月粮荒开始露头,六、七月份更为严重。各地均发生农民到区政府和驻军部队要粮食的情况。由于粮荒,澜沧东回区磨界寨“坏分子企图煽动群众抢劫区政府”,后因及时发觉而制止。酒井区大卡竜乡群众私自开仓分了粮食10多担。募乃粮库从4月下旬到7月8日,发生偷粮抢粮事件22次。澜沧东河区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为此,思茅地委在半个月间连续两次发出解决粮食问题的紧急指示。
在1958年大跃进以前,由于农村政策挫伤了农了的积极性,加上征了过头粮,云南农村就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云南省纪委1955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说,1952年思茅县龙潭、坝溜两区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人(其中龙潭105人,坝溜101人)。这个事件一直拖到1955年才作处理。临沧地委在1957年7月22日的报告说,临沧县在1956年3月到9月的6个月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在三个区26个乡的范围内,因饥饿而致死的有110人。原来属余粮户和自足户,因国家多征购了粮,又没有及时供应而饿死的占死者总数的占49。9%;原属于缺粮户,虽有粮票而无钱购粮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72%;因生理缺陷或劳动力极差而无人关心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8。18%;原是自足户因吃粮计划不周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9%;因基层干部贪污了粮票和救济金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6。36%;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粮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总数的4。54%。因此,群众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有的说:“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四区斗角乡饿死人丢在河里。家属说::“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
临沧地委上述报告说,在这一时期内,因缺粮使偷盗事件普遍发生。据14个乡调查,被发现有偷盗行为的有188人。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63起。另一方面,外逃、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卖儿卖女的也不少。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出卖了独生子(后又赎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8%,四、五两个区插秧被推迟两个节令。
报告说,出现饿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粮食征购任务上存在“偏差”。死人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四、五两个区。第四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975000斤,相当于1954年实绩3672408斤的1。35倍。第五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075000斤,相当于1955年征购实绩2930081斤的1。39倍。征购任务太重,不得不对采取强制手段,层层施加压力。因而出现了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五区平村乡工队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伍到群众家中搜查,贫农交不出粮的打欠条,富农交不出粮就现场斗争。富农王中富被打断三根肋骨,他的儿子被打成残废。
临沧县1956年饿死人的事件一直拖到1957年才处理。这个情况一直被压在地委以下,没有向中央汇报。
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土地改革比内地晚了几年,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沿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不会算账,完全不具备办社条件,但是,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不久,政府就不顾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到1957年底,云南省有初级社3015个,高级社18557个,共计21572个,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8。9%。到了1958年初,又开始并社、扩社。到公社化前,农业合作社并为18943个。经过9、10两个月的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833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为30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2。4%。有的地方上午刚挂上农业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边疆民族地区变换得更快,一些民族自治州1958年初才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土改结束后才创办起来的互助组,很快就被初级社、高级社所取代,紧接着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当时称这种现象为“一年内实现两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说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双管齐下,一箭三雕,三步并做一步走。”。就连原来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全省公社的规模一般在3000-5000户,最大的公社有3万多户。在公社化过程中,原来合作社的财产一律转为公社所有。农民私有的牛、猪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一律折价入社。说是折价,实际只算原价的50%,而且大部分没有付款,完全是无偿剥夺。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历来把牛当作财富的象征,公社化强行将其牛入社,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
随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办了起来。到10月14日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建立了98572个公共食堂,参加人数达1220多万人。大办公共食堂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有的地方强制取消一家一户的伙食,有些地方还没收农户的小农具,甚至将农户的铁锅砸碎,集体、私人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区(大队)为单位合办公共食堂,有粮食的生产队和没有粮的生产队在一起吃大锅饭,宣布“吃饭不要钱”。在居住分散的地区,社员每吃一顿饭要翻山越岭,少则走四五里路,多则走十多里路。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五风”猖獗,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据云南省委统计,从1958年到1961年,全省无偿调动的劳动力不下5亿个工作日。无偿占用和调用的土地约有245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平调的牛、马、骡、驴大牲畜约60万头,拆除农民住房100万间以上,另外还无偿占用农民住房100万间。与此同时,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盛行。在高寒山区,不让种适合这里气候的荞麦,改为不适合生长的玉米,称为“革荞子的命”。对西南边疆地区,不准在旱田旱地里种适合这里气候的旱谷,改为不适宜当地的杂粮,称为“革旱谷的命”。为了推广三轮三铧犁,强行火烧老式木犁。为了争先进、抢进度,动辄命令群众割掉没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规格”的幼苗,进行改种或重种。对不执行或没有按基层干部意志办事的扣工分、扣口粮、打骂,甚至动用各种刑罚。
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农业集体化和粮统购统销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进行的。说“阶级斗争是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强大动力”,实际是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进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1957年,在全省农村进行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于1957年8月在云南内地108个县(市)展开。8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斗争了9153人,捕了1342人。这场斗争“生动有效地批判了农村中的右倾思想。”斗争的结果,“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省委准备在这次斗争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人),个别判处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数之内。
也是在1957年,在城市开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1957年6月22日开始,云南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1958年4月起,全省又开展了“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共划出右派分子1073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8%,其中,党内右派分子1795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3。6%,共青团内右派1616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3。72%。在右派分子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58人。在1795名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1418人,占78.55%,地下党干部1221人,占67.97%。国民党起义将领导龙云、副省长龚自知、省人民委会委员安思溥、杨克诚、谢崇文、宋一痕、秦淑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给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和行政处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分人被判处徒刑。此外,还对上万名被认为有“右派观点”或“站在右派立场”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也长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视。
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全省开展了肃清“地方主义”的运动,严厉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划出了一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云南省,批判地方主义这不是第一次。1954年就批判过郑伯克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在人事上,主张干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强调地方情况特殊化。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不仅在云南省,在山东省、广东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开展过。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
1958年4月16-22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揭批所谓“郑敦、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21日,会议通过了“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是省委组织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