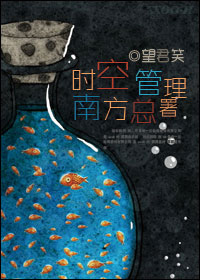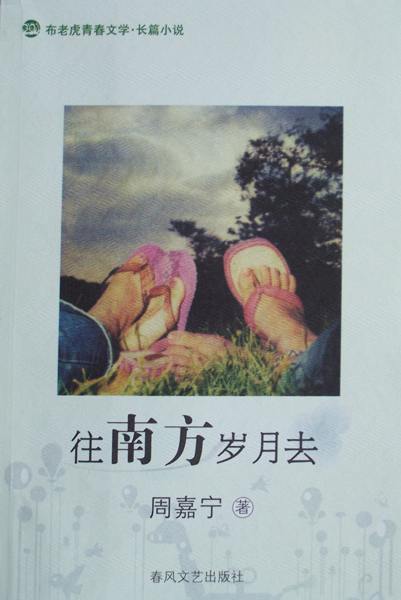南方有令秧-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听老爷说的,能一样么。”云巧话一出口就有点后悔,她伸开了胳膊,再把令秧的脑袋搂得更紧了些。她以为令秧到底是有些吃醋了,可是令秧的呼吸越来越匀称,微微地推她一下,她的肩膀立即顺从地塌了下去。云巧吃惊地发了一会儿呆,暗暗地自言自语:“你倒真睡得着。”
大夫们说,要到清明的时候,才知道老爷究竟还能不能走路。可是老爷归天的时候,还没到清明呢。老爷的卧房里外响起一片号啕声的时候,令秧出神地看着那张熟悉的脸,心里问他:“若是真的不会走了,黄泉路上要怎么办呢。”
二月初的时候,老爷的神志清醒了,他在某个黄昏突然睁开眼睛,令秧背对着床在点灯——她打发丫鬟去厨房看着药罐。二月的徽州还是湿冷,老爷房里必须一天到晚生着火盆。她弯下腰用火筷子拨了拨炭——就是在这个瞬间,听见身后有个暗哑的声音:“令秧。”
她如梦初醒。丢下火筷子奔到床边去。第一个念头居然是,别让其他人知道他已经醒了。她小心翼翼地抓住他冰冷的手——其实她的手也暖和不到哪里去,还像小时候那样,生着难为情的冻疮。她的手指缠绕着他的,她只是想知道他的手还有没有知觉——但是不成,她自己也紧张到什么也感觉不出来了。她用力地把他右手的四个指头捏拢在自己手心里——然后对着它们呵一口温热的气。一股委屈突然就从深处涌了出来,她费力地说:“老爷,你别死。”老爷唇边泛着一圈青灰,似笑非笑:“我不死。”“老爷看花灯的时候摔下来了,不过大夫说,清明以后,老爷就能下床走路。”——大夫当然不是这么说的,不过这有什么要紧。当丫鬟捧着药罐子进来的时候,老爷又重新睡了回去,她费了很大力气才让众人相信病人真的跟她说过话。
老爷的清醒是断断续续的,每天能有那么几个时辰,跟人说话毫无问题。但是他始终感觉不到自己的腿,也无法完全坐起来——他似乎完全不在乎到了清明能否重新行走——他本就是个脾气温和的人,病入膏肓之际,已经温和到了漠不关心的地步。有一天清早,令秧推门进去帮他擦身子的时候,闻到屋里有一股淡淡的腐朽的泥土气味——她就知道,那日子快到了。蕙娘早就在跟做棺材的师傅交涉着,选木材,选颜色,选雕刻的纹样——先交订银,每道工序完了,打发管家夫妻去看过,再一步一步地给钱。棺材刚刚刷完最后的一层清漆,两三天工夫,老爷就用上了。
蕙娘跪在女眷的人群里,恣情恣意地大放悲声。令秧虽说跪在她前面,但是好像蕙娘的哭声是所有哭声的主心骨。令秧哭不出来,她只是静静地流着眼泪,她心里还在想着云巧,云巧的身孕已经五个月,身子已微微显了出来,她不该这么长久地跪着。老爷的丧事办得很体面,族里拨了一笔钱给他们,上上下下的事情都是蕙娘精打细算地操持着。令秧不晓得蕙娘是如何做到在每一天死去活来地号啕大哭之后,再语气干脆地核算着灵堂里的香烛纸钱的数量,并且关心着丧席的菜式——一定要打点好来念经的和尚们的素斋,这是她挂在嘴边上的话。此刻,她只是恐惧着自己没能如众人那般,将面部撕扯成狰狞的样子。老夫人看起来倒是一切都好,哀而不伤,引人敬重,只是人们随时都得提心吊胆,害怕那种凄厉的鸣叫声又猝不及防地叨扰了亡者的典礼。
有一件事,令秧甚至没有告诉过云巧。在老爷刚刚清醒的某个午后,令秧迈进老爷房里的时候,看到老夫人独自坐在老爷床边上。她抚摩着老爷看上去已经和她一样苍老枯瘦的手背,令秧不知为何就躲在了屏风后面。她就是觉得自己不该过去。
母亲问:“疼得好些了么?”
儿子答:“不疼。”
母亲说:“不疼就好,好生养着。”
儿子说:“会好生养着,老夫人放心。”
屋里就在这时有了一股粪便的气味。老爷已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排泄。老夫人伸手掩住了自己的鼻子和嘴巴,想了想,用那只闲着的手也盖住了老爷的口鼻。令秧看不见老爷的神情。隔了一会儿,老夫人松开了双手,那双手突兀地悬在在她和老爷之间。老夫人笑了。
母亲一边笑,一边摇头:“你小时候也这样。”
儿子说:“老夫人是故意将儿子推下去的,我清楚得很。”
令秧慢慢地朝门边倒退,尽力让脚步声消弭。她知道自己此刻的身形步态滑稽可笑。她也用手掩着自己的鼻子。她得不露痕迹地出去,叫人来帮忙给老爷换洗,也需要叫伺候老夫人的人过来,将老夫人领回去。她不是害怕老夫人知道她听见了他们说的话,她害怕老爷看见她也掩着鼻子。她第一次为老爷清洗粪便的时候,就曾经心惊肉跳地想,若是老爷要这样活到老夫人那个年纪,还真不如从现在起就让她守寡,那样至少还有牌坊可以拿。
老爷在灵堂里停了七天。“头七”时候,做了最后一场法事。
送葬那日,纸钱飞了满天,在田间小道上零落成泥。他明明答应过令秧,他不死。只是人出尔反尔,也是常有的。
现在终于没有了满屋子憋屈的腐朽气,没有了被屎尿弄脏的铺盖被褥,没有了那男人沉重得像石块一样的身体,没有了他摸上去像苔藓一般的皮肤,没有了即使怎么小心也还是长出来的褥疮,没有了病人和照看病人的人都会忍受的满心受辱的感觉——都没有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死亡就像是平仄和韵脚,把脏污的生修整成了一首诗。令秧觉得老爷的棺材很好看,纹饰简单朴素,可是有股静美。正因为他躺在里面,她才能如此干净地怀念他。她成为唐家夫人,还不到一年。似乎嫁给他,就是为了送他一程。
她记得那应该是惊蛰前后,一个下着微雨的下午。她看到蕙娘到哥儿的书房里去,叫哥儿拿主意,挑选棺材上的纹饰。她跟蕙娘打招呼,蕙娘就招着手叫她进去一起看。她好像还从没进过哥儿的书房。书房一张小榻上,坐着个穿了一身鸽灰色的陌生男人。一见令秧进来了,就起身唱了个喏。她知道,那个就是蕙娘的远房表哥,暂时请来指点哥儿的文章。她忙不迭地道万福,都没看到其实哥儿也在给她行礼。
那是令秧头一回见到谢先生。她没敢仔细看他究竟长什么样。谢英,字舜珲。唐府里无论主仆,索性人人都称呼他“谢先生”。
老爷下葬的翌日,族里的人便来了。蕙娘认得,上门的是唐六公的侄子唐璞。六公是族长,六公的侄子年纪不大,可是辈分却其实比老爷还高。唐璞看起来倒不是个嚣张的人。只准那几个跟着他的小厮站在大门口候着。对蕙娘道:“族里的规矩是这样,新寡的妇人,须得到祖宗祠堂里去跪一夜,由长老们口授女德。”蕙娘做了个手势叫丫鬟出去,自己为唐璞斟上了茶,殷勤备至:“族里规矩自然是要守,只是我家夫人也要有个贴身的人跟着才好,方便伺候,夫人前些日子一直操劳着照顾老爷,身子虚弱,还望长老们担待。”蕙娘用力地盯着唐璞的眼睛,重重地说出“担待”两个字。“也罢。”唐璞放下了没动过的茶杯,“只带一个。可是有一样,夫人什么时候回来,那丫鬟就什么时候回来,中间须得在祠堂候着听使唤,不可中途擅自回府。”唐璞带着令秧离去的时候,蕙娘的嘴唇已经被自己咬得发白,她吩咐身边一脸忧心的管家娘子:“快点去把大夫请来,今晚就留在咱们府里,还有,让大夫多备点止血的药。”
很多年后,令秧即使非常努力地回想,也还是记不得祠堂的样子。她只记得那几位长老一人坐一把红木的太师椅,然后一个四五十岁的婆子放了张蒲团在她膝下,眼神示意她下跪。至于跟着她过来的那个丫鬟,早已被唐璞的随从们拦在了外面。她不记得自己对着那一行又一行的灵位究竟磕了多少个头。总之,磕到最后,俯下身子的瞬间她就错觉那些牌位马上就要对着她飞下来,“枭枭”地叫着,淹没她的头顶。她袖子里藏着一小瓶白药——是来的路上,那丫鬟偷偷塞给她的,想必是蕙娘的主意。不过她却不知道这药究竟该用多少。那些断过指的女人,砍掉的是哪一根?用左手拿刀还是用右手?要是自己真的下不了手,砍不断怎么办,难道还会有人来帮忙不成?
六公清了清嗓子,不怒自威,讲话的声音中气十足:“唐王氏,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她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得上“知道”,所以只好看着六公的眼睛。六公边上那个不知是“九公”还是“十一公”的老者慢条斯理地放下了茶杯:“唐王氏,今天找你来,是为着好意提醒你做女人的本分,也自然是为着光耀咱们唐氏一族的门楣。咱们唐家的男人向来体健长寿,上一个朝廷旌表过的贞节烈妇,怕是二十多年前了……”他朝着半空中拱了拱手,然后另一个声音截断了他的,这声音从令秧的右手边传过来,沙哑,调门却很高,听着直刮耳朵:“是二十九年了。中间只出过两个未满三十的寡妇,一个有辱门楣,沉潭了;另一个回娘家了,也是因为那妇人的父亲当时升了巡抚,来接她走,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如今我们唐氏族中也该再出个烈妇,唐王氏,恰好轮到你,也是老天垂怜。”
听起来,他们像是灾民求雨那样,盼着一个年轻的烈女。
唐璞站在她的左手边,打开一本册子,高声诵读起来,六公缓缓地说:“唐王氏,你且仔细听着,听完了,我们还有话要问你。”
唐璞抑扬顿挫地念完了一大段话,她其实一个词都听不懂。她能听懂的部分,只是一长串的名字,似乎无穷无尽。
洪武四年,河南南阳府,刘氏,十七岁丧夫,触棺殉夫,亡。
洪武十二年,陕西平凉府,张氏,十八岁丧夫,矢志守节,至二十二岁,公婆迫其改嫁,自缢而亡。
洪武二十三年,徽州府婺源县,林氏,二十一岁丧夫,绝食七日而亡。
永乐四年,湖广黎平府,赵氏,十八岁丧夫,投湖而亡。
永乐十年,山东莱州府,冯氏,十四岁定亲,完婚前半月,夫急病暴毙,自缢而亡。
正德元年,河南汝宁府,李氏,夫亡,年十六岁,公婆欲将其改嫁其夫幼弟,执意不从,自刎而亡。
嘉靖九年,徽州歙县,白氏,二十岁丧夫,时年幼子两岁,矢志守节,其子后染时疫暴卒,卒年四岁,白氏遂投井而亡。
嘉靖十一年,徽州休宁县,方氏,二十三岁丧夫,吞金而亡。
嘉靖二十年,山西沁州府,苏氏,十九岁丧夫,矢志守节,侍奉家翁,后家翁病故,其父母欲使其改嫁,自缢而亡。
嘉靖二十三年……
原来这世上,有这么多种自尽的死法。只是这“嘉靖年间”为何这么长,令秧的腰间已经麻木,略微一挪动,人就像木偶一样散了架,不听使唤地朝前匍匐,她用手撑住了冰凉的地板。这一次,她没有力气再抬起头注视六公的脸。
“我真的,跪不动了。”一颗泪重重地砸在手背上。唐璞的声音不知疲倦地继续着,有一个字像雪片一样飞满了令秧的脑袋:亡。
“也罢。时候不早,大家都乏了。”六公挥手将先头那个婆子招进来,“扶她去隔壁歇着,明日接着念。你要知道,给你念的这些,都是朝廷旌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