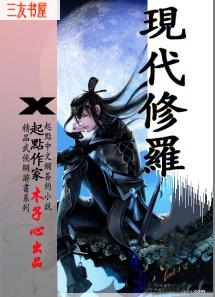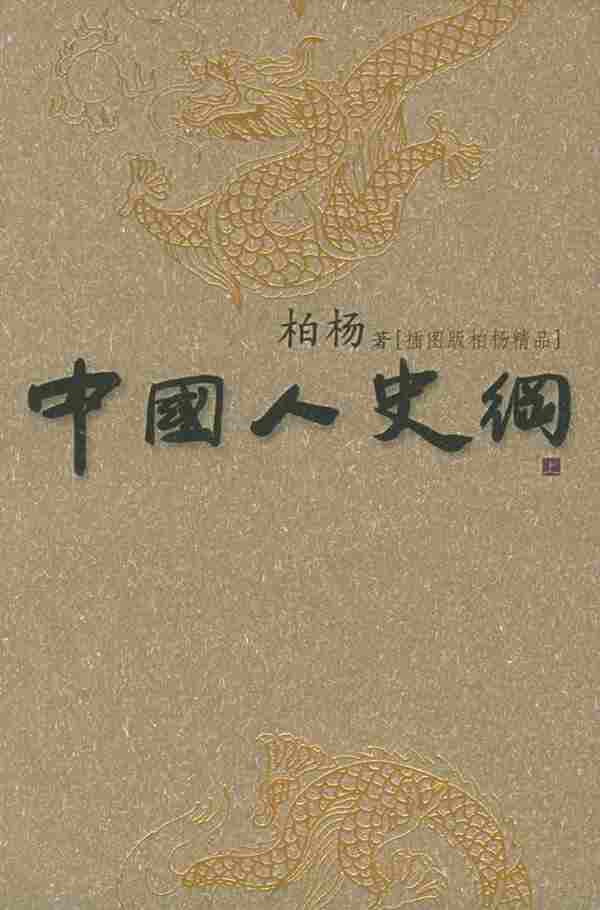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6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诗意环境。4.从象征入手,超越现实,对人生、命运、人性的思考带来的诗意的哲思(可参考《三十年》第十九章第一、二节,以及田本相《〈雷雨〉〈日出〉的艺术风格》,《曹禺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田本相、胡叔和编)。
(7)许多评论家指出曹禺的话剧具有浓郁的诗意,请结合具体作品论述“诗意”在曹禺话剧中的特色和功能。
可参考《三十年》第十九章的相关内容。在曹禺话剧接受史上,曾出现过严重的误读现象,即认为曹禺话剧是“社会问题剧”,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范畴。解答本题可将这种“误读”作为参照,从曹禺话剧溢出写实和批判框架的成分入手,揭示其中蕴涵的诗意特征。所谓诗意特征,在曹禺话剧中具体表现为主观抒情、整体象征、神秘氛围、诗化语言等方面。可将上述要点作为基本线索,结合作品实例展开论述,并联系曹禺话剧主题的宗教性和悲悯情怀,分析“诗意”在剧中的表意功能。在论述过程中,要注意曹禺后期创作风格和审美追求的转变,可从诗意特征的拓展、深化的角度,来把握这一转变在曹禺话剧创作中的意义。
【必读作品与文献】
《雷雨》
《北京人》
【评论节录】
刘西渭:《雷雨》
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
钱谷融:《“你忘了你是怎样一个人啦!”——谈周朴园》
钱谷融:《谈谈〈日出〉中的陈白露》
辛宪锡:《〈雷雨〉若干分歧问题探讨》
朱栋霖:《曹禺戏剧与契诃夫》
▲刘西渭论《雷雨》
说实话,在《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妇女。容我乱问一句,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个是希腊尤瑞彼得司Euripides的Hippolytus,一个是法国辣辛Racine的Phèdre,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前妻的儿子。我仅说隐隐中,因为实际在《雷雨》里面,儿子和后母相爱,发生逆伦关系,而那两出戏,写的是后母遭前妻儿子拒绝,恼羞成怒。《雷雨》写的却是后母遭前妻儿子捐弃,妒火中烧。然而我硬要派做同一气息的,就是作者同样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而且全要报复。什么使这出戏有生命的?正是那位周太太,一个“母亲不是母亲,情妇不是情妇”的女性。就社会不健全的组织来看,她无疑是一个被牺牲者;然而谁敢同情她,我们这些接受现实传统的可怜虫?这样一个站在常规道德之外的反叛,旧礼教绝不容纳的淫妇,只有全剧的进行。她是一只沉了的舟,然而在将沉之际,如若不能重新撑起来,她宁可人舟两覆,这是一个火山口,或者犹如作者所谓,她是那被象征着的天时,而热情是她的雷雨。她什么也看不见,她就看见热情;热情到了无可寄托的时际,便做成自己的顽石,一跤绊了过去。再没有比从爱到嫉妒到破坏更直更窄的路了,简直比上天堂的路还要直还要窄。但是,这是一个生活在黑暗角落的旧式妇女,不像鲁大海,同是受压迫者,他却有一个强壮的灵魂。她不能像他那样赤裸裸地无顾忌;对于她,一切倒咽下去,做成有力的内在的生命。所谓热情也者,到了表现的时候,反而冷静到像叫你走进了坟窟的程度。于是你更感到她的阴鸷,她的力量,她的痛苦;你知道这有所顾忌的主妇,会无顾忌地揭露一切,揭露她自己的罪恶。从戏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她只有一个心思:报复。她不是不爱她亲生的儿子,是她不能分心;她会恨他,如若他不受她利用。到了不能制止自己的时候,她连儿子的前途也不屑一顾。她要报复一切,因为一切做成她的地位,她的痛苦,她的罪恶。她时时在恫吓,她警告周萍道:“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周萍另有所爱,绝不把她放在心上。于是她宣布道:“好,你去吧!小心,现在(望窗外自语)风暴就要起来了!”她是说天空的暴风雨,但是我们感到的,是她心里的暴风雨。在第四幕,她有一句简短的话,然而具有绝大的力量:“我有精神病。”她要报复的心思会让她变成一个通常所谓的利口。这于她是一种快感。鲁贵以为可以用她逆伦的秘密胁制她,但是这糊涂虫绝想不到“一个失望的女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绝不在乎他那点儿痛痒。我引为遗憾的就是,这样一个充实的戏剧性人物,作者却不把戏全给她做。戏的结局不全由于她的过失和报复。
(录自刘西渭:《雷雨》,原载《咀华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收《曹禺研究资料》上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
▲蘩漪:最“雷雨”的性格
在《雷雨》中,另一个“不安宁的灵魂”是周冲的母亲蘩漪,在这一点上,母子俩确实有气质的相近,他(她)们同时最早闯入曹禺的艺术构思中,大概不是偶然。但周冲的“不安宁”,是一个未曾涉世的少年,处于人的“童年”状态,对未知的形而上世界的朦胧的追求,带有更多的梦幻色彩。而支配着饱经人世沧桑的蘩漪的,则是那更现实、却也更明确、强烈的情欲的渴求。曹禺这样介绍自己所创造的“她”:“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里,她的胆量里,她的狂热的思想里,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忽然来的力量里”,“当她陷于情感的冥想中,忽然愉快地笑着,当她见着她所爱的,快乐的红晕散布在脸上,两颊的笑涡也暴露出来的时节,你才觉得出她是能被人爱的,应当是被人爱的。你才知道她到底是一个女人,跟一切年轻的女人一样”。读者也许还记得,当曹禺说到他的“性情”与他的戏剧中的“苦夏”氛围时,曾经说“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一定意义上,他在蘩漪身上所着力发掘的,正是“人”的非理性的情欲,以及“人”的“魔性”方面,蘩漪的内在魅力,实出于此。但《雷雨》中的蘩漪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还是那令人窒息的压抑感。请看曹禺赋予她的外在形象:“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发红”,“她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压抑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她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是怎样一种情热、欲望的火在内心燃烧,又用着怎样的力量才将这热、这火强压下去呵!难怪她一出场就嚷着“闷”,“我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这种无时不有的、几乎成为蘩漪象征的感觉,自然早已超越了生理的意义,而意味着生命热力的被郁结,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难以言传的精神痛苦,并且形成一种持续的紧张:生命之弦越绷越紧,几至于崩裂。满蓄着受着压抑的“力”,必然要随时随地寻求某一个缺口,以便冲决而出。由此而产生了“狂躁”——这是一种超常态的欲望与对欲望的超常态的压抑,二者互相撞击而激起的近乎疯狂的情绪力量。请听蘩漪的独白——
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
而“火山”终于爆发——
(向冲,半疯狂地)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高声)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的父亲压死了,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她也是一个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
(失去了母性,喊着)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是你的!
这里的“不顾一切”——冲决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不惜放弃以至亵渎在传统中视为最神圣的“母亲”的尊严,权利,赤裸裸地要求着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情欲与性爱,这确实骇世惊俗,震撼人心。这才是《雷雨》中最为眩目的一道闪电,最扣人心弦的一声惊雷,它把从来“有母性,有女儿性,而无妻性”的中国妇女几千年受压抑的精神痛苦一下子照亮,因受压抑而千百倍加强了的反抗的“魔性”也在一瞬间全部释放。尽管只是“瞬间的闪亮”,但毕竟是生命的真正闪光;作者说,“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佩服。”
但作者又说:“她的生命烧到电火样地白热,短促;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着火星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这是不能不使人想到人生的悲凉与残酷的。
蘩漪确实是“最‘雷雨’”的性格。
(录自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论周朴园
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作者曹禺这时才不过二十三岁,他竟能把周朴园这样一个老奸巨猾、深藏不露的伪善者的灵魂,如此清晰、如此细致入微地勾勒出来。这种深刻的观察力,这样高超的艺术才能,真叫人叹赏不止。不过最后一场中对周朴园的描写、处理,却不能说是同样成功的。在这一场里(其实,前面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情况),作者思想上的不成熟,以及他世界观中的严重弱点,和他的作为一个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感受与表现的能力,同样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在周萍与四凤已经取得侍萍的同意,即将一同出走的当儿,周朴园被蘩漪叫了下来。他一下来,忽然又看到了已经说过再也不上周家门的侍萍、四凤,而且她们还同蘩漪、周萍、周冲在一起,他当时的惊骇是可想而知的。作者这样写:
周朴园(见鲁侍萍、鲁四凤在一起,惊)啊,你,你——你们这是做什么?
头上那个“你”字可能是对侍萍说的。他可能是一看到侍萍,在万分吃惊的当儿,就几乎脱口而出地说出“你怎么又来了?”这句话来。但他究竟是个老练而深沉的人,所以他终于竭力压住了惊慌,并且强作镇定地、不失他的威严本色地改问了一句:“你们这是做什么?”这时,蘩漪就拉着四凤告诉他,“这是你的儿媳妇,你见见。”又叫四凤“叫他爸爸”。并且指着侍萍,叫周朴园“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接着,她又转过身来对周萍说:“萍,过来!当着你的父亲,过来,给这个妈叩头。”周朴园看见侍萍重又回来,本来就已经是说不出的慌乱,如今蘩漪又不怀好意地一会儿叫他认这个,一会儿叫他认那个,而他又完全不知道周萍与四凤之间的事,所以蘩漪一上来说四凤是他的媳妇,他可能没有听清楚;即使听清楚了,在极度的慌乱中,在一心只想着他跟侍萍的关系时,也可能完全不理解“媳妇”两个字的意义。而蘩漪叫周萍给侍萍叩头,——“给这个妈叩头”这句话,在他的耳中却特别响亮清晰。他既然并不知道周萍跟四凤的恋爱关系,当然也就不会想到蘩漪嘴中的这个“妈”字,并不是他心里所想的那个“妈”字的意思。于是,他就一心以为他跟侍萍的关系已被大家知道了,(后来蘩漪的:“什么,她是侍萍?”这样由衷的惊奇,不是也被他认为是故意的嘲弄吗?)他当然也就无法再隐瞒了。所以,他之承认侍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