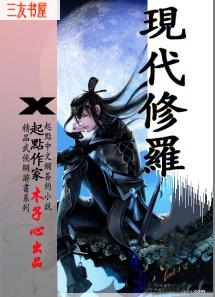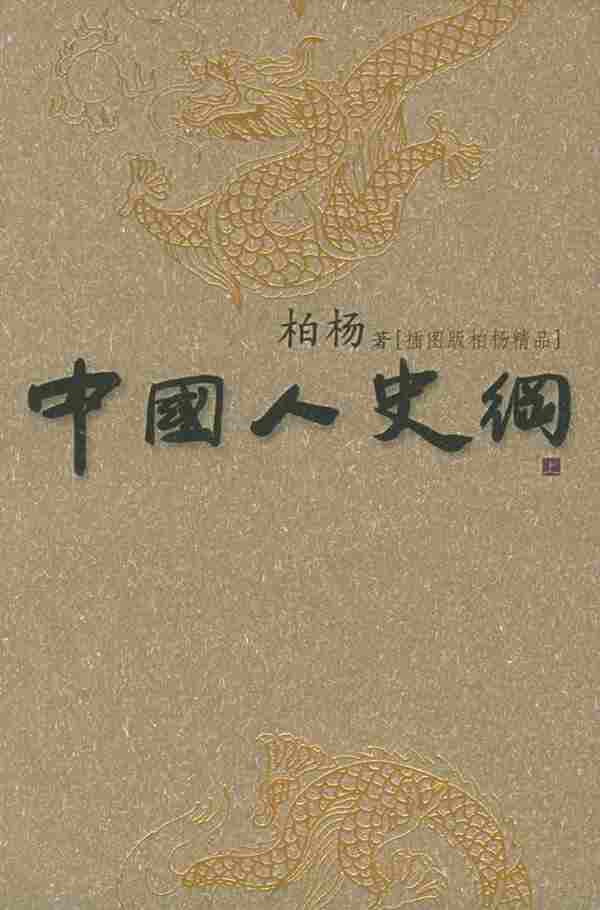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中幼(如《骆驼祥子》中老车夫老马,中年车夫二强子,顺次而下的祥子、小马等;再如《四世同堂》中的四代,其他作品里的父与子)——是这样的生旦净末丑。其中《骆驼祥子》的创作最能见出普遍文学风气的影响。即使在《骆驼祥子》里,也并非偶然地,老舍并不着力于车厂老板刘四对车夫祥子的直接经济剥削,将祥子的悲剧仅仅归结为阶级矛盾的结果。用了《我这一辈子》中主人公的说法,他强调的是“个人独有的事”对造成一个人命运的作用,如与虎妞的关系之于祥子,也如《我这一辈子》中“我”家的婚变之于“我”。这使得小说世界内在构成与构成原则,与一时的流行模式区分开来。
老舍非但不强调较为分明的阶级,甚至也不随时强调较为朦胧的上流、下层。小羊圈祁家无疑是中产市民(《四世同堂》),牛天赐家(《牛天赐传》)、张大哥家(《离婚》)也是的。在小羊圈胡同中,处于胡同居民对面的,是汉奸冠晓荷、蓝东阳,洋奴祁瑞丰,以至于在“英国府”当差而沾染了西崽气的丁约翰。至于其他胡同居民,倒是因同仇敌忾而见出平等的。不惟一条小羊圈,在老舍的整个小说世界中,作为正派市民的对立物、市民社会中的异类的,主要是洋奴、汉奸、西崽式的文人或非文人:仍然是文化上的划分。上述特征在当代京味小说中也存在着。即使现实感较强的刘心武,对于他笔下人物众多的那条胡同(《钟鼓楼》),也更乐于表现作为胡同文化特点的和谐、平等感——包括局长及其邻居之间。
老舍长于写商人,那种旧北京“老字号”的商人,所强调的也非阶级(商业资本家),而是职业(所营者“商”)。他甚至不大关心人物具体的商业活动。吸引他的兴趣的是人物的文化风貌,德行,是经由商人体现的“老字号”特有的传统商业文化。在这种时候他对人物的区分,也同样由文化上着眼:以传统方式经营的,如祁天佑(《四世同堂》)、王利发(《茶馆》),以及《老字号》、《新韩穆烈德》诸作中的老板、掌柜;站在这一组人物对面的,则是以凶猛的商业竞争置“老字号”于绝境的洋派商人。他并非无意地忽略了上述商人共同的商人本性(阶级属性),而径自专一地呈现其不同的文化面貌、商业文化渊源与背景。
上述总体构思下的人物关系,自然不会是如左翼文学中通常可以分明看到的阶级关系。这里构成人物生活世界的,是街坊、邻里,以及同业关系,也即胡同居民最基本的生活关系。其中尤其街坊、邻里关系,往往是京味小说中描写最为生动有味的人物关系。老北京的胡同社会,主要由小生产者、中小商业者、城市个体劳动者构成。生产活动、商业活动的狭小规模,经济层级的相对靠近,都不足以造成充分发展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对立关系;东方城市中素来发达的行会组织,也强调着人的职业身份,人与人之间的行业、职业联系。当代北京胡同情况虽有变动,仍在较为低下的生活水准上保留着居民经济地位的相对均衡(这种情况近年来才有变化)。这正是构成胡同人情、人际关系的生活依据。京味小说作者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又出于对北京生活的谙悉,而不全由形式的制约。来自生活世界的与来自艺术形式、艺术传统、艺术惯例的多方面制约——或许要这样说才近于完全?
(录自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骆驼祥子》的悲剧类型与社会文化内涵
就悲剧的类型而言,《骆驼祥子》所写的不是英雄悲剧,而是普通人的生活悲剧——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看,都是如此。
与这样的人物和题材相适应的,作家在构思和描写这个悲剧时,没有制造什么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没有渲染任何色彩强烈的气氛,也没有片言只语的慷慨激昂的议论,而是用冷静严峻的笔墨,一笔一笔地展开城市底层日常生活的画面、凸现挣扎于其间的人物思想感情的微妙波动,以一些灰黯的景象显示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灾祸。即使写到军阀逃兵抢车、政治暗探勒索,也没有紧张激烈的情节和动作,更没有形成戏剧性的悬念或者高潮,一切都是无声无息地发生了又过去了。除了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没有惊动任何人,即使有第三者知道了也决不会注意和关心这类平淡无奇、到处都有的事情。然而小说却有力地写出了这些都给祥子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悲剧就是这样地开始的。
作家还善于从一般人不留意的场合、或者不以为是悲剧的事态中挖掘出内在的悲剧意蕴。车厂老板的女儿虎妞主动和祥子亲近,后来还不惜嫁给他。从世俗的眼光看来,这岂不是作为车夫的祥子的意外艳福?作家却从中看出了也写出了这种强加于他的爱情和婚娶,非但没有给他带来丝毫幸福和喜悦,反而使他陷入说不出的委屈和耻辱——粉碎了作为他的整个人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凭着自己诚实的劳动成家立业的生活蓝图。“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而且使他从挣脱不掉这么一个女人的摆布,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生活的无望。
比起英雄悲剧,这种普通人的生活悲剧,在文艺史上是比较晚出的,直到近代才流行和普遍起来。它反映了文艺创作与社会现实、与平民百姓的更为紧密的接近和结合,又与现实主义思潮的兴起联系在一起。这类悲剧作品,没有英雄悲剧那种能够唤起人们的崇高、庄严、悲壮感的美感作用,和产生突然爆发出来的振奋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然而正象鲁迅所指出的:“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这类作品在揭示生活本身的悲剧内涵的广度和深度上,往往可以胜过英雄悲剧。它写的是广泛地发生于现实生活中人们身边的悲剧,有时还能“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隐蔽于生活深处的悲剧因素。这类作品又总是努力排除各种外在的、偶然的、或者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刺激性的因素,而是以人物的平民性、事件的平凡性和内在的悲剧性,构成对社会生活和生活中的悲剧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概括。这样的悲剧作品,能够深化最广大的读者对于生活的认识,而且由于使他们感到其中所描写的既平淡无奇又如同身受,从而激起更多的醒悟和震惊,由此产生的悲剧效果也就可能特别强烈特别持久。叔本华给这类悲剧以很高的评价:“这一类不是把不幸当作一个例外指给我们看,不是当作由于罕有的情况或狠毒异常的人物带来的东西,而是当作一种轻易而自发的,从人的行为和性格中产生的东西,几乎是当作(人的)本质上要产生的东西,这就是不幸也和我们接近到可怕的程度了。……我们看到最大的痛苦,都是在本质上我们自己的命运也难免的复杂关系和我们自己也可能干出来的行为带来的,……这样我们就会不寒而栗,觉得自己已到地狱中来了。”这段话概括了这类悲剧的长处及其特有的美感作用,也可以借用来说明《骆驼祥子》获得成功的一个方面的缘由。
从一定意义上说,《骆驼祥子》又是一个性格悲剧。酿成这样一场悲剧,除了来自社会的压迫剥削,还有悲剧主人公本身性格上的原因。作家的创作意图显然也不仅仅在于控诉制造悲剧的旧社会,同时还鞭挞了祥子身上的弱点。
长期以来,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分析祥子形象时,虽然也提到他来自农村,在具体分析中常常只是把他作为一般的城市个体劳动者看待,忽略了农村生活在他的性格以至于他的形象的各个方面留下的众多鲜明的印记。无论是他的健壮、木纳或者勤快、朴实,还是他的狭窄、保守或者谨小慎微,即从外形、生活习惯,到心理状态、精神气质,无不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显示出来自乡间的特点。即使在诸如喜欢蹲着跟人讲话和“觉得满世界带着老婆逛是件可羞的事”之类的生活细节中,也都是典型的农村习惯和农民意识。小说一再提到他不同于一般的车夫,没有入车夫的“辙儿”(比如不会象别的车夫那样撒野耍奸),还是因为他保持着在乡间形成的拘谨忠厚的心态和气质。他和很有心计、八面玲珑的高妈同在曹府帮佣、同属城市个体劳动者,但两人的言谈、举止和内心活动处处形成明显的对比,同样在于他有强烈的农民意识,和还缺少高妈那么多的城市生活的磨练。所以,《骆驼祥子》实际上写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淳朴正直的青年堕落为所谓“坏嘎嘎”的城市无赖的悲剧。这个因为农村无法存身、到城市另找生路的劳动者,被城市更加无情也更加迅速地毁灭了。在他的身上,当个独立劳动者的人生追求和纯洁美好的农民品格是同时丧失的。这是祥子这个艺术典型的重要特征,也构成了这场悲剧的主要线索。三十年代上半期,随着破产农民大批涌向城市求生的社会现象日趋普遍,王统照、丁玲、叶紫、鲁彦等不少作家都以此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他们或者着重描写这些人物在农村的不幸,把奔向城市作为作品的结尾,或者描写后者来到城市后不久,同样投靠无门,失望而归。《骆驼祥子》则以全部笔墨叙述他们来到了城市以后的痛苦遭遇,以他们被新的生活所吞噬而告终,在艺术上完成了对于这个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悲剧的反映。
抓住以上特点,也才能充分理解为什么从外表到内心都曾经是骆驼般坚韧的祥子,心灵深处却又始终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和软弱感,几乎遇到什么事情都束手无策,当他因为走投无路而感到惶恐和苦恼时,“更让他难过的是没地方去诉诉委屈”。这不能只从他是个个体劳动者的一般原则加以说明。
祥子性格的最大特点,又是导致这场悲剧的主观上的契机的,是他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命运的强烈愿望和执著追求。既然他所承受的是来自整个社会的沉重压迫,孤立的零散的个人奋斗自然难以取得成功,即使有了自己的车子并且始终保持着,又何尝能够摆脱那些压制而成为真正可以独立自主、幸福生活的劳动者?这种不切实际的打算,使他从一开始就陷入盲目性,一切真诚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等待着他的只能是失败和悲剧。
对于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丰富深入的理解和杰出的现实主义才能,使老舍从一些富有个性特征的言谈行动中,揭示出祥子社会的阶级的属性,准确而且鲜明地表现出小生产方式的阶级的属性,准确而且鲜明地表现出小生产方式和闭塞落后的生活环境,它们的狭隘性、保守性和盲目性何等深刻地决定了祥子的生存形态、行为模式和交往准则,造成了他性格中的严重缺陷(前面提到的祥子对于小福子的态度,也是如此)。小说有力地写出了祥子的悲剧不仅是当时那个社会作为外在的力量造成的,同时也是社会对于他的性格的深入影响、阶级的局限性,即社会转化为人物的内在因素造成的。所以,不但应该改变那样的客观世界,同时也应该改变这样的主观世界,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