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水中画画-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不是它的翅膀太小,所以飞不起来呀?’
‘嗯…’假装检查起风筝,她翻看几次后,问:‘是有点小,这谁做给你的啊?’
‘是玺…玺…喜欢风筝的少京哥哥给我的。’他眼珠子溜向一边,为自己捏了把冷汗。
‘少京?这就奇怪了,它样子长得像之前玺亚哥哥做的。’若无其事地又问:‘这应该是玺亚给你的吧?’
因为被一语道中,家颢瞪着大眼睛,满脸藏掩不住的心虚:‘不…不是啊!就说了是少京哥哥嘛!’
原来小家颢被说服,达成协议了。
小苗当下转了转脑筋,和蔼地笑:‘你是不是…跟人约好了?实话一个字都不能说?’
这个大姐姐似乎能明白男人之间的义气,家颢犹豫一下,然后点点头。
‘好吧!那你都别说话,就像刚刚那样点头回答我好吗?’
‘啊?’
‘咦?破坏你们的约定了吗?’
‘嗯…没有耶!’
‘那就好啦!咱们谈完之后,我就教你放风筝,保证可以飞得高高的。’
家颢抿着唇想了想,经过他深思熟虑三秒钟后,好像没发现任何不妥之处,便答应了。小苗佯装漫不经心的样子,慢吞吞整理起风筝线,一面信口发问:
‘咱们家这个少京哥哥…其实真正的名字不叫少京,对不对?’
他点点头,不加思索。
‘那…他的名字,该不会是玺亚吧?是不是?’
他又点头,发现小苗缠线轴的速度放得更慢了。
‘是玺亚…亲口跟你说的,说他不是少京,是玺亚?’
家颢抬起头,又点了头,还奉送一句:‘就是咱们家的玺亚哥哥呀!大家都以为他不在了。’
夏日炎炎,此起彼落的蝉鸣声势浩大,正充斥在这片沉默里。
他歪斜着脸,眉头可以皱得跟婳姨一样凹深:‘苗姐姐,你要哭了吗?不高兴吗?’
侧下明瞳,她对他露出一缕凄恻的笑意:‘不是,我连自己该不该高兴…都不知道呢!’
家颢嘟起嘴,对于她的反应不是很满意,显然这天大的秘密并未带来预期中的惊喜。
一会儿,小苗发现又有人要出门,登时却认不出是家里的哪个ㄚ嬛,一身再朴素不过的中国服,搭上两根垂在胸前的麻花辫,手里却捧着一本大书。
‘姐姐?’
‘啊?’小良倏然转身,脂粉未施的脸上尽是仓惶:‘你…你在这儿啊?’
‘姐姐,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
说朴素是好听,但真的很土。
‘没有啊!这…这样很奇怪吗?我可是先说好,我才不是要去跟踪谁呢!’
小苗目送着她匆匆忙忙地出去,莫可奈何地想:‘我又没问你要干嘛。’
北京的夏季长,自五月下旬到九月一百多天,虽位处北方,一热起来几乎与南京无异,所以街上行人并不多,独独宋琳还撑着阳伞伫立在文化厅门外,像在等人,叫路过的行人不禁要多看她几眼,她虽然不怕热,站了半个多钟头也渐渐香汗淋漓了,不时用绢子擦额头,不时眺望远方来路,路像被太阳烤熟了会冒烟。
他不会来了吧……也许忘了,这场泰戈尔的演讲当时有头没尾地带过,他连答应都没说呢!而她,宋琳,竟可以跟小苗一样痴傻,漫无目地等着,她的夏日漂鸟。
‘好蠢哪…’
轻声嘲笑自己在地上的影子,而后不期然地,一个较为高大的黑影加了进来,因为是跑步来的,身子还喘个不停。
‘对不起,你等很久了吧?’
她稍稍转移阳伞,晃见了云笙比炎日更璀璨的笑靥,他流的汗比她多,自清逸的眉稍滑下,宋琳伸出手,细细擦拭。
‘我不知道自己等多久,就知道你来了。’
云笙看看表,演讲已经进行了二十分钟:‘咱们进去再说吧!’
他们进去了。小良这才放心地从胡同中走出来,理理长辫,又逡望一下四周,像个偷儿一样地跟上去。她可不是来跟监的,只是一时兴起,想听听那个叫泰什么东西的人演讲,如此而已。
会场中的座位坐得零零星星,观众大部份是上了年纪的学究,要不就是为了功课、报告而来的学生,云笙和宋琳拣了后头的座位坐下,聆听讲台上的国外学者将他们带入泰戈尔的文学世界。
‘我原是在犹豫的,不知该不该来,又不想让你担心、失望。’
单调乏味的演讲声中,传来云笙沉笃好听的声调,他平心静气面对讲台方向,宋琳好奇地看向他专注的侧脸。
‘梁夫人…她知道吗?’
‘就是为了向她报备,才迟到了。’
‘她不气炸了?’
‘呵…没有,小良这个人,嘴硬的很,喜欢说反话。’
什…什么啊!干嘛一开始就说她坏话?坐在后一排的小良从书本中探出头,气忿忿瞪住怡然自得的丈夫。
‘她说的反话不都很伤人吗?怎么梁大哥…好像一直都能甘之如贻呢?’
‘她啊…她和小苗这对姐妹完全不同,小苗是外柔内刚,你应该很清楚,虽然很容易受伤,可她能自己再站起来,完好如初。而小良,乍看之下是比妹妹强悍多了,那是她的保护色,随时用来掩饰背后的伤口,小良很容易受伤,必须有人帮她一把才行。’
‘所以你一直在帮她?一直都这么了解她?你们不是媒妁之约而结婚吗?为什么可以……’
‘因为我爱上小良了。’
宋琳睁大着湛湛黑瞳,在麦克风持续的播放中,彷彿听见了一阵振翅而飞的声音。
那本大书缓缓遮盖到鼻尖,小良还回不过神,她知道自己一定脸红了,而且红的不得了,可再管不着,她的视线曾几何时,早已被那个背影不可自拔地吸引。
‘当然这是我的一厢情愿,有时候却也有丑陋的一面,看着小良夜夜出门寻欢作乐,我的自私,和想给她自由的宽容,每每交战激烈,深怕有一天这可怕的嫉妒…会在小良面前爆发出来。’
咬紧唇,握紧了手,宋琳深深呼吸,这么动人的词句当前,不能哭,现在还不能。
‘梁大哥…也是个傻痴子,你这么默默不言、日夜忍耐又是何苦呢?她根本不知道,根本就没办法体会梁大哥的苦心嘛!你是肉包子打狗,我看不出这中间有什么交集之处。’
小…小贱人!竟然把她比喻成狗?小良气得捏皱了书页,叫邻座的一位妇人狐疑地打量这名奇怪的女学生。
‘是啊……真遗憾,我提起诗词歌赋的时候,她不能附和我,除此之外,跟小良在一起的时光很愉快,就算没有文章、书本,还是快乐极了。我还在领悟,这夫妻数十年如一日的道理,而这个…却是不能与宋小姐分享的。’
她是真的听见鸟儿挥翅的声音,翩翩然走了,再不栖息她的窗。
‘宋小姐,在我的遗憾里,你却能同我畅谈许多文学名着,我真的很高兴,也感激不尽……’
‘可那还不足以取代你和梁夫人的愉快时光吧!’
她转过头,在云笙深不可测的眼眸里补捉住一丝惆怅,那是他无能为力的情感。
散场了,他们谁也没动,离去的人潮在身边来来往往,她感觉到季节冥冥替换,属于她的、绚烂的夏日已经悄悄过去了。
‘宋小姐……’
‘梁大哥,’宋琳站起身,明了而恻然牵动愁美的笑意,让后方的小良看得有些心疼:‘那么美的文学世界,我不会再与你同游了。请你带着梁夫人,好好出发,好好浏览,有一天,希望有一天你们的交集能早日出现。’
她黯然离席,头也不回地走。
云笙重新跌回座位,双手垂下,望着发黄的天花板出神,似乎为自己的残忍自责,或对一位知己告别而感伤。
小良就看着他发呆好久,至少过了三分多钟,清洁人员已经纷纷出来打扫了,他才挪挪眼镜离开,走到后头又绕进座席里,轻轻拿开了那本遮掩用的大书。
‘咱们回家吧!’
小良怔怔与他四目相交,顿时陷入全身赤裸般的窘境,毫无遮蔽,只得动弹不得。
‘演讲棒吗?’
他伸出手,让小良扶着站起来,就听见她嘟哝着:‘完全听不懂。’
‘没关系,以后慢慢教你。’
她走了几步,脚尖绊到了椅脚,一个劲儿扑到云笙怀里。
‘好痛…’
‘小心点。’
云笙正想走,怀中的小良却没动静,净挨着他,脸因为埋在他的胸膛而看不见任何表情。
‘小良?该走了。’
‘再等一等。’她将他搂得更紧,闭上眼,倾听云笙稍嫌快速的心跳:‘我什么都不会,诗词歌赋、文章书本都不懂,只会抱着你,黏着你,就让我待久一点吧……’
他浅浅一笑,低下头与她两两相依:‘我倒觉得…小良多才多艺呢!大庭广众突然这么神来一笔,叫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小良知道会场的工作人员都在看他们,有的还笑得羞涩万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仗着这突来的勇气,便什么也不怕了。
宋琳停下脚步,伸手接住了一片飘落的黄叶,这小东西过于早熟,夏天还没过去,就凋零枯萎。
‘夏日的漂鸟,来到我的窗前,发出啁啾歌声,然后翩然而去。秋日的黄叶,没有歌唱,只一声叹息,便飘然落下。’她心有戚戚焉地叹息:‘原来…我是黄叶啊……’
前方路面上的落叶被踩响,她敏感抬头,小苗亭亭而立,穿着黑白相间的典雅衣裳,一股怜悯伤楚的精神,像极了学院中圣洁的修女。
‘我是跟着姐姐过来的,有点不放心。’
‘不放心她又因为我跟你姐夫吵架吗?’她笑笑,扔掉了手中树叶。
‘我不放心的…是宋琳你啊!’
她?难道现在的她是一副楚楚可怜、受尽委曲的模样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还笑着,我就担心,这时候…’小苗走到她面前,心疼宋琳坚强的样子:‘不该是你放声大哭的时候吗?’
‘我…?我又不是你,哪能说哭就哭的。’
刚刚最难过的时候她都忍住了,现在更不可能在小苗面前放肆宣泄。
‘你瞧,你跟姐姐一样,都是死鸭子嘴硬。’小苗轻轻抱住她,眉心皱蹙得更深切,彷彿她才是那个受伤的人:‘真希望我是你的白马王子,现在能搂着你,安慰你,叫你好好承认…其实你是难过得要命了……’
她没有,不难过的,若真要觉得懊恼,也是恼着自己忘记组织的规定,轻易就掉入感情的网罗去。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她重新与人划清界限,继续在那冰山一角自筑窝巢,恢复从前的一切了。
小苗侧眼看见,靠在自己肩头上的宋琳,净秀的眉宇也正紧紧深锁,却无法阻止泪水从合闭上的眼眸中不断涌出,将她的白衣裳浸濡成透明颜色,透明得像此刻的宋琳一样,伪装的混浊不再,还原一方干净清澄。
‘给我五分钟…不,三分钟就够了……’
‘我的肩膀可以一直借给你,虽然没有姐夫的宽,姐夫的壮,撑着你,倒是绰绰有余了,直到有一天…你也能找到可以倚靠的肩膀,让你撑一辈子。’
“小苗,别再哭了,你的眼睛会瞎掉的。”
小苗九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大厅中全是前来吊唁的宾客,小良被方老爷紧抱在怀里哭得厉害,小苗则躲回自己房间,蜷曲在墙角下啜泣不停,玺亚就蹲在她跟前,慌得不知手措。
“你的眼睛又红又肿,再过半分钟一定会变瞎子的,要不,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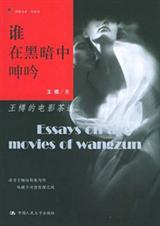

![[希腊神话]水中倒影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27/27144.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