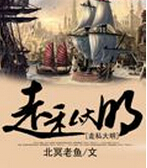梦回大明十二年-第5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实还有许多传闻紫燕没有敢说,譬如铃儿去世之后,张先生当晚就被锦衣卫带走了,这些日子一直没有消息,也不知是被关在哪里。紫燕知道了不免会有些担心,这些事会不会也牵连到李夫人身上?可事实却是,自从铃儿故去后,安媛就仿佛被所有的人都遗忘了一样,再也没有任何人来找过她,当然,她也丝毫没有要离开这里的意思。
哀伤过度的嘉靖皇帝,一日之内仿佛老了十岁一般,再也无力为自己的孙儿操办丧事。反倒是刚刚面临丧子之痛的裕王表现得格外坚强,亲自主持了整个丧事的置办。临到出丧前那天,他破天荒的来到了安媛的屋子,眼前依旧是收拾得温馨而整洁的屋子,就连屋里的那个消瘦的女子也依旧穿着洗的干净的旧衣裳,这一切都还是半个余月前的样子,只是不知不觉的,却有什么似乎都改变了。
“茗……安媛……”他轻轻的叫她,不自觉的拢了她的手,人却向前靠近了些,有些心疼的皱了眉,“这些日子忙得都没有顾得上来看你,你怎么瘦了这么多?一切可都还好?”
“还好,”她清清静静的略一颔首,不动声色的避开了他,忽然又扬起头来,一双眸子里晴光潋滟,“张先生现在可好?”
“你倒是消息灵通的很,”裕王有些不自然的笑笑,“叔大被投下狱的事,这内廷之中恐怕都没几个人知道。”
安媛清澈的眼神只是冷冷的瞧着他,“臣妇只是想,最后陪伴在皇长孙身旁的,只有张先生和臣妇二人,若是张先生下了狱,恐怕臣妇也脱不了干系。据说如今宫里主事的正是裕王爷,那么还请王爷一次的下了圣旨,把臣妇也一并抓到狱里去来的爽利。”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他很快敛了笑意,生硬的说道,“父皇起初很是震怒,要把叔大投到狱中去。我和几位朝臣一起力保了叔大,如今父皇的气渐渐消了,昨日已经把叔大放出来了,想来应该无事的,你尽管放心吧。”
“那就好,这事原本就是无辜牵连了张先生。”她听了他的解释,答得却是干脆,“既然如此,我也有些倦了,要歇息了,王爷请回吧。”
无辜。这两字的语调不阴不阳,又被她刻意强调了几分,听到他耳里着实有些刺人,他忍不住怒气有些上升,“我这些日子忙的足不点地,一得了空便来看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凉凉的顶了一句,“铃儿原本就是你名义上的长子,他小小年纪死的不明不白。你为他奔忙丧事还有什么不对么?”
他的脸色瞬时煞白,气的嘴唇亦有些发抖。安媛侧过身去,不去看他,却听他的声音甚是低沉,“你是怪我没有去追究害死铃儿的凶手么?父皇平日里多是宠幸段妃,段妃心思缜密,也未尝没有给自己铺好了后路。如今铃儿已死,宫里实在不能再掀起波澜,更何况父皇年事已高,也再经不起什么打击了。”
他骤然压低了声调,无不苦涩的闭上了眼,“我知道你怪我,可是……对不起,我别无选择。”
安媛默然无语的从铃儿昔日的摇篮里,拣出一串小小的彩石风铃,轻轻用绢布擦拭着。略一碰动,风铃便会铮铮作响,很是好听。是了,他们是父子,是亲人,再也亲不过的骨肉之情,又怎能强人所难?她瞬时心中一片冰冷。
“明天就是铃儿出殡的日子了,依着父皇的意思,铃儿虽然身份贵重,到底年纪还小,便按照郡王的礼数下葬,随葬到永陵去。父皇说他百年之后,地下有个孙儿相伴,一老一少也不寂寞。”他转述着父亲的话,忽然心中有些酸苦,父亲平日里对待他们几个兄弟从来都是非常严苛,从来不苟言笑,但唯有这次在对孙子上,终于显出了几分舔犊之情的老态,却格外让人觉得凄凉。他默默地愣了一瞬,续道,“你若是明日里得空,也一同去看看吧。”
安媛转过身去,用很小的声音说道,“这串风铃是铃儿平日里最喜欢的,明日里也让他一起带走吧。”
她的声音里不知不觉的带了几分呜咽。他细细的看着她面上哀楚的神色,忽然轻轻搂住了她,温热的胸口瞬时给了她许多暖意。
她到底还是撑不住了,呜的一声终于哭了出来,“铃儿……铃儿还那么小,还是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他怎么会就走了……”
“不要哭了,”他轻声的安慰着,也动了感情,“人生本就是会有许多遗憾,铃儿的一生虽然短暂,可曾经有过你这样一位母亲,他也是幸福的……你还年轻,以后还会有自己的孩子……不要再糟践自己了……”
她努力的控制着自己不要流泪,眼泪却似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的滚滚落下,很快把他胸前一大片衣襟都浸湿了。她慌忙要拿帕子去擦,便将手里的风铃搁在一旁。
他心底轻轻的叹了口气,接过那风铃细看,只见十来块彩石都是一般大小,每块上面都刻着一个小小的娟秀的字。他越看越奇,仔细读来,串起来竟是两句诗: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他心中一动,半晌说不出话来。
那天夜里,她做了个梦。
梦境里是一片漆黑而又晦暗,深邃中似乎是铃儿鲜活的身影,一点一点的放大,纯真的面目亦是逐渐清晰起来。漆黑的双眸瞪得大大,藕段似的小手臂高高的举着,好像在责怪安媛为什么不早来抱他。她惊异而又欢喜,上前直欲去搂住他,好好在怀里疼爱一番。可手刚刚触到他锦缎的小袄子,铃儿却努力的挣脱了她,面目上忽然露出痛苦的表情,她分明看到他小小的眼鼻中都是血渍,一点点的渗了出来,淋得满脸都是血肉模糊……
她骇得大声叫喊,从睡梦中一下子惊坐起来,只觉得额上都是涔涔的汗意。一只手臂忽然牢牢的扶住了她,传递出一丝温暖的信息,”不要怕,不要怕……是做噩梦了么?“
她牢牢的攀住那手臂,小声的抽泣着,“铃儿他在怪我……他在怪我没有救他。”
“铃儿不会怪你的,他知道你已经为他尽力了……”他叹息着劝,另一只手放下了笔,轻轻抚了抚她的脸。她下意识地躲闪了一瞬,抬起头来,却见裕王一身玄色的衫子,正是悄无声息的坐在身侧,一双眸子却有些黯淡。她这才发现自己睡梦中牢牢抱住的居然是他的右臂。而他半躬着身子斜靠在榻上,竟然是一直以一个甚是艰难的姿势,一手搂住了她,一手在批公文。
她赶紧松了手,回了回神,努力的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开始想他怎么会在这里,她赫然回忆到自己哭得累了,似是沉沉的在他怀中睡去……那时似乎天光还是白亮的紧,难道这一觉,竟然这般漫长?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抬眸四处望了望,顿时只觉得心尖也颤了颤。之间榻旁的木几上堆满了厚厚的公文,旁边还搁了支朱笔。想不到他不仅一直没走,竟然还把办公的场所搬到这屋里来。
他循着她的目光望去,似是知了她的心意,缓缓解释道,“你先前沉沉睡了,还兀自抱着我的手臂不肯撒手,我怕抽离了去会搅了你的睡梦,便借这只手臂由你去做枕头了。”说着他抬起自己有些酸麻的手臂,瞥了一眼身旁堆积如山的公文,苦笑道,“父皇重病不起,奏折都堆积到我这里,明日还有铃儿的出殡之仪,今晚便也只能赶在这里批复奏折了。”
她的脸瞬时红了红,惴惴的低下了头去,声音细若蚊子,“王爷还是回昭和殿去批复吧,这里实在是太狭窄拥挤了些,不敢委屈了王爷。”
他无声的笑了笑,淡淡道,“如今你是睡醒了,便要赶我走了?”他的语声贯是不高,却有一种迫人心的压力。
她听他语音有异,不免怔了怔,勉强笑道,“哪里敢赶王爷,这不过是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嘛……到底奴婢是个女儿家的,深夜与王爷相处,恐怕多有不便,传出去名声上也不好听,将来真个想要出嫁时,也不免多有阻碍。王爷自是个大度的人,相比能体谅我这点小小的用心。”
“你就这么担心要嫁出去?”他冷冷的挑眉看她一眼,眉目间都是锋利。她尴尬了半晌,忽然见他用力搂紧了她,在她耳边低低叹了口气,声音几乎微不可闻,“其实从前……你也是这样陪我批复奏折的……”
安媛心知他又想起了那个于自己百分之百相似的“茗儿”郡主,不知道该说什么,心想还是哑口无言的好。于是不动声色的朝旁边挪了挪。想不到他却是牢牢的搂着她的腰,愈是感觉到她有躲闪的意思,便愈是赌气似的箍得更紧,手臂似铁箍一样,两人拉锯战似的无声的僵持了一会儿,直到他的手臂箍她生疼的闷哼了一声。
她终于着了恼,艰难的推开他的手臂,颤声说道,“王爷,你早已知晓我与叔大结下了情谊,此生双双许下誓言,非伊不嫁非卿不娶。我与王爷相识多日,早已当作知交朋友一般。可王爷两次三番的这般不避讳,恐怕与你我和叔大都多有不便。”
他默然不说话了,轻轻松开了手,脸上瞬时变化了神色,眸子里多了几分冷淡且复杂的神色。
她低下头不敢去瞧他,只是努力稳着声气说,“我知道王爷对前头去了的茗儿郡主的一片深情,可我与茗儿容貌虽似,却毕竟不是一个人,王爷这番苦心用在我身上,怕真是错付了。更何况如今王爷又有了福华郡主这样的佳偶,我冷眼瞧着,福华郡主虽然行事冷了些,却是对王爷一片热心的。王爷岂不更应该好好珍惜。”
“我知道的。你不用说了,”他忽然斩钉截铁的拦住了她的话,不愿再听下去,“都为你安排过了,明日去永陵的路上,你便趁机离开吧。父皇那边你也不用担心了。明天依旧是原来和张先生商定过的计划,到时候他会备下马车,在宫外接你离开。”
她有些哑然的听着他的话,瞬时说不出话来。
“现在太晚了,再叫秦福他们把奏折搬走太麻烦了。我今晚就在这里批完再走,”他轻轻给她掖了掖被角,却背过身去,拾起了一本奏折坐的离她远远的,他背转了身去瞧不见面上的表情,却只听到他平淡的语声,“明天去永陵的路还有些遥远,你早些休息吧。”
她嗯了一声,飞快的钻入了被中,只露出一双点漆似的眸子转了转,却是看着他又斜倚着床榻的玄色背影很是深沉,灯火下仍旧勾着身子在批复奏折。
……
窗外依旧是黯淡的夜幕低垂,安媛眯着眼又撑了半个时辰,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便阖了眼想略睡会儿打个盹。睡梦中,似乎又有人轻轻的抚过自己的眼角唇边,伴随着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
她醒来时,窗外天色早已透亮。床榻边哪里还有人,就连木几上也收拾的干干净净,一本册页也没有。如果不是因为身上轻轻搭着的一件玄色长袍,她直疑昨夜的情景不过又是一个梦中的梦境。
第二天安媛倒是很早就被唤醒了,自有几个丫鬟婆子替她收拾衣装。明代丧葬的风俗不同于今日,宫内有亲王公主去世,宫人要齐哀三日。于是此时宫内再也见不到华丽鲜艳的宫装,都是一水的乌履白服,女子更是要去了全部的首饰,只戴一顶麻质的盖头,望起来很是素雅。
安媛刚刚收拾停当,却见门口不知什么时候立了一个素服角帽的身影,便连腰绖、首绖都是素色,唯有一双眸子幽暗如初。她倒是鲜见他如此打扮,怔了一回神,无话找话道,“你的公文都批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