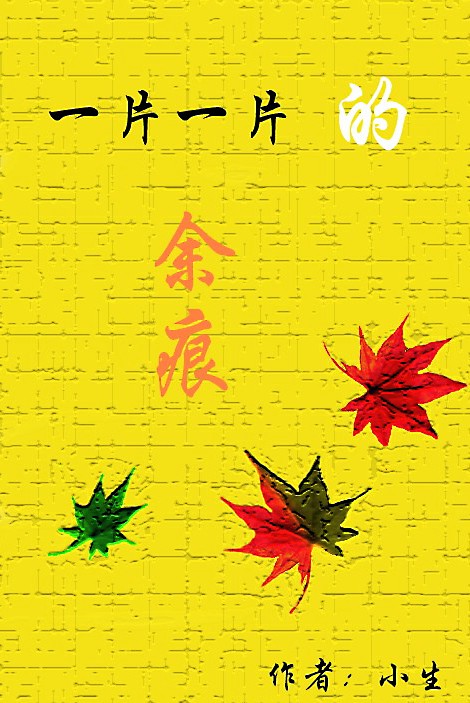圣罗兰鸦片的诱惑-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没有。其实我今天找你……”
“我知道。我爱人跟我说了你们谈话的内容了,我觉得很可行。”他握了我的手说:“秦姗,放心吧,有 我在,放心。”他说着,从随身的黑色皮包里拿出十叠人民币,都是还未曾开封的,有着银行工作人员的签章 。
“安邦,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想要你的钱,因为我不想在我们之间的感情里搀杂哪怕一点点不纯净的成分 。你送给我的项链,我会永远保留,因为它就是我们之间这段路的见证。而对于钱,我不会收的,但是,今天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向你先借一些,等我有的时候,一定会还你。”
“不用你还。我给你的,你都要收着,并且我根本不需要这些。”他拿起我的背包,就往里面装。
“不,不行!”我阻止。
他看着我。
“不行。我只借四万,太多,我就没有能力还了。”
“没事,等你以后从国外挣了钱,再还我不迟。”他还要装。
“真的不行。”我夺回背包:“你就给我四万吧。请尊重我的感情。”
他紧紧地抱了我:“秦姗,你怎么这么傻?”
我抬头:“傻就傻吧,如果在你这里都不能清清白白的,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装好四万,转头说:“我要去公司办理辞职手续,你陪我去吗?”
“我会在车里等你,然后我们去吃饭。”
当我把四万块钱扔在会计桌子上的时候,会计笑呵呵地看着我,说:“就是嘛,有钱就该早点儿还,那你的工 资不就按时给你了?”
“麻烦你数数,看看对不对,然后把欠我的工资补给我,咱们一码事说一码事,别掺乎在一起……当然, 也麻烦你把欠条还给我。”
会计笑说:“欠条在老板那里,你去找老板要吧。”
“我当初把欠条给的你,当然还要找你要。如果在老板那里,还麻烦会计跑一趟了。”我一屁股坐在椅子 上:“快点儿,安书记还等着我吃饭呢。”
会计看了看我,要把钱锁进保险柜。
“哎,别啊,一手交钱,一手交条。你先取条子去。”
她转身出去了。
我看着这四万块发呆。其实以前我不是这样蛮不讲理、气焰嚣张的,对吧?
会计很快便回来了。我整理好所有的票据,找严芳签了字,都在财务报销了,也拿到了他们欠我的工资。 不错,我又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了。我不禁笑了。
写好辞职报告,我交给了常姐,说了声再见,就出了门。其实,我以为,我会和她握握手的,但是我没有 。现在回过头去想想,我实在说不清,当初常姐从那么多女孩儿中选中了我,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一度认为, 她至少是欣赏我的,可是,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我发现,也许我错了。大概,果真就是各为其主,常姐 不过就是用老板的眼光来对我们进行了第一轮的面试,或者说,这每一个选中的秘书,不过就是她在老板面前 居功邀赏的一颗颗棋子而已。常姐对我的态度,其实一直是以老板对我的态度为准绳的。她本人对我如何,我 无从知道,甚至我觉得,她自身,对我没有任何的评价。直到今天,我从这个公司离开的时候,才明白了常姐 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司的一棵常青树的真正原因。
办完了一切手续,我最后和菲菲拥抱了一下,说:“结婚的时候记得通知我,我一定去参加你的婚礼。” 她点了点头,却流了眼泪。“祝你幸福。”我在她的耳边轻轻说。
我带着无比轻松的脚步下了楼,如同我初次来这个公司上班的时候一样。安邦的车停在一棵树的树荫里, 车子的玻璃贴了膜,显得里面非常神秘。
我打开车门:“安邦,结束了。”……
又是这家酒店。
又是这间房间。
他,又来褪我的衣服。只是,我阻止了他的手。
我拉着他的手,来到窗前,俯视这个尘世,仿佛当初我站在公司的落地窗前俯视这个世界一般。人们都蚂 蚁般渺小而忙碌,汽车仍然如甲克虫般地移动,丝毫没有因为我的厄运而改变些许。
“安邦,你来看。”我拉了他的手,站在窗边。
他高我那么、那么多,站在我身边,犹如一堵坚强的城墙。我的头微微靠在他的肩头,感觉他身上的温度 烫在脸上,很是舒服。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烟味儿,手上也是。我拉起他的手,放在唇边,细细地吻。吻着吻 着,我就哭了。
“安邦,以前在公司的时候,我常常这么俯视这个城市,看人们匆忙地生活,看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挣扎,那时 候,我以为我看得很清楚,我以为自己是超脱于他们的,会有着与他们不同的命运。可是,现在,当我仍然在 俯视的时候,他们没有变,变了的是我。——原来,任我如何的清醒,其实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我同他们一 样,劳而无功地忙碌着。
“安邦,你知道吗,关于爱情也是。爱情这条路,在你我之间,很短,短得让我站在起点就可以看得见终 点。我知道结果。但是,我仍然心有侥幸地奔跑,绕了好大、好大一圈地跑。我以为,多跑一会儿,我能够创 造另外一个结果,但是,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所有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我最终停在哪里 。这可能就是这个游戏的定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可以容忍我去获得另外的结果,或者,它本就不 存在。
“安邦,尽管如此,可是你知道吗,奔跑的过程是快乐的。因为那时候我有希望,虽然希望只是一种梦幻 ,我是带着美丽的梦幻去跑的。我快乐,我像春天的麻雀一般乱跳,跳得很高,都不怕从枝头摔下来,因为希 望就是我的翅膀,它会在每一个危险的时候拯救我脆弱的心,让我坚持下去,尽管坚持的是一个错误。和你在 一起的时候,每一秒钟,我都认真地珍藏。我希望,有朝一日,在我无力再爱的时候,翻检出来,我会同当时 一样地快乐。所以,你的每一个痕迹,都装在了我的脑海里……可是现在,我希望,我希望我能够失去这份记 忆。因为我承受不了这样的落差……”
安邦从身后搂了我,一语不发。我觉得浑身都被他的温度包围了,好幸福、好幸福的感觉。我的头向后靠 在他的胸口,感受他呼吸间的起伏。
“安邦,你会记得我吗?”
“当然。”他的声音仿佛从喉咙深处冒出来的,沙哑而无力。这样的声音对我有着致命的杀伤力,每每都 可以引起我切肤的痛。
“安邦,你猜,如果我不去流产,会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男孩儿。”
“为什么?”我回转头,看着他,问。
“因为我特笨,笨得只会生男孩儿。”他说完,嘿嘿地笑。
“可是,他死了。他多可怜啊,没来得及成形,就死了。”
“秦姗,不要乱想,你要好好地活,听见没有?”他把我的身体转过来,面对面地,对我说。他握紧了我 的手,我的手边立刻充盈了暖意。
仰视啊,这样一种仰视的幸福!
我感觉我的眼泪汩汩地流,滴在我的胸口,溅在他的衬衣上,无声地。
“你听到没有?”他微微摇了我的肩,捏得我有点痛。
“我答应你。”
“一会儿我带你去全市最好的川菜馆。”
“不,我不要吃东西,我只想和你多一点时间在一起。”
“一定要去。我们认识以来,还没有专门带你吃过川菜呢。”
“可是你不吃辣的啊。”
“谁说的?认识你以后,我开始吃,味道还不错呢。”他笑。
他笑,我也笑。我就是这么贱,他高兴,我就高兴,他不高兴,我想办法让他高兴。若他烦了我,我是那 么地伤心,心里像扎了把针似的尖疼、尖疼的。
他放心地俯下头来吻我,我想拒绝的,可是偏偏一点力气也没有。
他把我抱上床,我再次拒绝。
“医生说,一个月以内不可以……”
他失望地看着我,然后道:“那我可以吻你吗?”
他细细地吻我,甚至一度,我觉得活在他的唇下,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事情。
“安邦,你这一生一世……有没有……很认真地爱过……一个女人?”我抽泣着说。
“有……就是你……你一定要……相信。”他吻着答。
“那为什么你不……不说那个字……?”我的眼泪像夏天的急雨般迅速滴落。
“因为不能说……”
“为什么?只一次……好吗……?”
“不能……”
“一次……一次,我只要听一次……都不可以吗?”泪水像开闸的洪水,泛滥成灾,湿透了床单。
“我宁愿对不起你……让你……痛苦,也不愿意……让有的人……更痛苦。”
“究竟……为了什么……”
“……责任……”
“责任……是基于爱情的……对吗……”
“不知道……”
我终于没有听医生的话,破戒了……
那天我回家很晚。我不但吃到了最地道的川菜,还如愿以偿地在车里和他聊了很多、很多,从他小时候,聊到 年轻的时候,到他和他老婆的认识以及结婚。喜欢,听他描述一切的他的记忆,触摸他曾经的轨迹。喜欢,他 全权做主的样子,随便带我去哪里,只要别太早分开。也聊了我,但是,我仍然没有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了。
那天夜里,落雨了。在车的后座上,我蜷在他的腿上,静静体会幸福的感觉,懒得睁开眼睛。我感觉有灯 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感觉我的呼吸宁静而柔淡。他抱着我说话。
我用手指划开蒙在玻璃上的雾气,看雨点打出的痕迹,恍然,有些想哭。夜色寂寂,雨声细密而轻灵。街 灯冷冷地亮,而他的手,温热异常。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指甲剪得圆润。我细细地看他的指纹,用力记在 心里。他的手,他的脸,他的呼吸,他的怀抱。
仰望着他,真幸福。
我知道,以后我将再不会见到安邦了,所以,那夜,我把每一秒钟都尽力拉长,长成一分钟、一小时,长 成整整一季的青春,长成绵延一生的爱恋……
我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我打开电脑,进入聊天室。“月射寒江”也在。
寒箫吹月::)
月射寒江:好久没有见你,你好吗?
寒箫吹月:一切都结束了。
月射寒江:你是指?
寒箫吹月:孩子和钱,还有爱情,还有工作,反正一切的一切,都结束了,只剩下我,一个空虚的生命。
月射寒江:你的情绪很不好。
月射寒江:孩子的父亲给你钱了?
寒箫吹月:你怎么知道?
月射寒江:可以想象。
寒箫吹月:你是男人吗?
月射寒江:或许是。
寒箫吹月:那你了解男人吗?
月射寒江:一点儿而已。
寒箫吹月:他为什么会给我钱,是因为爱我吗?
月射寒江:不。他只是不会再见你。
寒箫吹月:不过我说我会还他的钱。
月射寒江:其实你不该向他借钱,这钱你还也不是,不还也不是。
寒箫吹月:为什么?
月射寒江:明摆着,这钱他是给你的。你这边呢,若不还,你就给自己标了价了,和小姐没什么区别,虽 然这么说可能很伤害你。
寒箫吹月:你太过分了!
月射寒江:对不起,不过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一样,只是卖贵、卖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