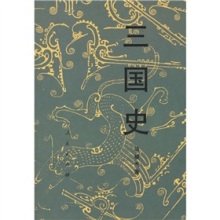爱的罗曼史-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乎能从一个住处的厨房窗台上轻易地跳至另一住处朝南的卧室。我一次又一次做着这种沉溺于往昔中的游戏。与此同时街道各处的景物并没有因为城市规划中数十年来的扩张搬迁而改变。似乎,市政工程中的推土机从未停留在风景如画的北门一带,在它靠近君山的一段斜坡上,在陶瓷厂门口,山南小学的操场上。那里被连根铲除的长势茂密的山林里夏天浓阴深处的知了依然在那儿啼鸣。知更鸟、布谷、燕子依然在郊外的农田上空啁啾(而并非改建成了一幢幢新村的楼房)。记忆的兀自游逛脱离了我的身躯,脱离了我平时的日常生活的行踪。即使我后来外出打工,远至广东、新疆,我的眼睛的一部分依然看得见我们在三楼住过那幢旧楼房的阳台窗户——阳台上晾晒的被褥、棉布床单、枕巾、枕头(那上面绣花的图案)——她的连衣裙、冬天的羊毛衫,吊袜和背带裤。我自己27岁那年穿的T恤。我的眼球上似乎残留着往昔生活中的阳光的光斑。透过它们,我可以看见一切,看见坐在课堂第二排座椅上的她。内心忐忑不安的她。在人群中郁郁寡欢的她。下班回家时疲惫不堪,却又勉强挣出一丝笑容。在流逝的光阴后面在镜中忽然发现眼角一丝皱纹的她。穿着过年的新衣裳。在秋风中默默地推脚踏车,散步途中山林的“飒飒”风声。同学们大声朗诵课文。那四楼窗户夜晚的灯光。课堂里镇流器的声音。
我用的是自己设计打印的辅导教材。我每晚提早一小时到达教室,在黑板上抄写课文示范,做准备工作。我请一名当地的画家朋友设计制作了二十张课桌大小的海报,上书“理解诗歌——现代诗歌的欣赏与写作”几个大字,贴到县城各处的公共宣传栏。广告用的海报收到了很大的成效。报名人数多达五十多人,满满一教室都坐不下。我却担心害怕得要死。因为我从未有过任何那怕一种以上的授课、讲学经历。随着开课日子的渐渐来临,我几乎要放弃,打消掉这一开班讲课的念头。我只是硬着头皮,在上课铃响的最后一秒钟前鼓足了勇气。我周围跟我一起走上楼梯的有很多我在那些年里地方上的朋友,我不能够使他们失望。然而我一边悄悄地硬起头皮,一边却像往里面充了太多气的气球一样快要爆炸了。有那么一刻,我紧张得一言不发,只要有人跟我说一句话,我就会情绪失控。幸亏身边没有人问我话,跟我交谈,而象征着权威和空间的讲台大黑板,已经在眼前了。虽然这样,在开始讲学的前一秒钟我仍然觉得一阵晕眩、仿佛,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的奇迹——我听到了自己说话的音调、口吻,有生以来,第一次从我自己身体里跑出来,陌生面孔的听讲者,我能正常说话了——我感到一阵抑制不住的惊喜。按照我以往的性情,我会当场做一脸的傻笑。但这是在一般市民以为壮严的夜校课堂,我最好是收敛一点平日言行中的恶习。于是我一边宣读备课笔记,一边依依不舍把一口暗自窃喜的唾沫咽下肚去。
我后来才知道,上第一堂课时,我的小英子并没有到场。她那天医院里临时加班,白天加晚上的一个班连着上。她苦于找不到可以替她班的别人。就像早 年上初中,高中一样,她独自一人跑到城里来,白天黑夜寄宿在上班的医院。她在医院里有间临时宿舍的床位。房子紧邻着医院的太平间和大片很少有人经过的林荫道。那排红砖头房子起码有四五十年了。水池边上所有的自来水管,都生了锈,认识我之前,她就住在这样一个地方。从小到大,除了外婆,自己村子里的房子和童年,她生活的环境一直比较恶劣,阴郁。通过她不同于常人、格外敏感的心灵,又在她苦着脸的羞涩,清秀的外表上反映出来。我初次用心注意她时总感到她身上那么一种宛如偏僻旷野上的清溪般与众不同的气质。她有点像是长在一大片罕有人迹的野树林边上的幼树林。从她的身上,一种透明澄澈、孤零零的美被从背后的黑夜中衬托出来。人们有时看不到这一簇洁白的花瓣,只看到了聚拢在花瓣周围的夜色。她受她外婆影响很深。一种旧式深闺女子的含蓄、拘禁,深藏不露。她具有一种跟社会上别的女孩子不同,超乎常人的意志力。她的意志力成份明明白白被写在她在人面前时常严厉的眼神中。她吃东西时勾着头,不愿被人看见。她身上有一种女性的隐忍之美,仿佛幼年时代受过严格的家教和训练(其实没有,只是外婆潜移默化的影响)。她有一种认真的,对生活细加咀嚼的风度,并且介于随时朝后躲起来和随时献身之间,或两者皆而有之。她骑的那辆枣红色,夏天新买的女式脚踏车。爸爸知道她要外出挣钱了,就给她买了这辆车。她往类似小书包一样的背袋里塞了几样欢喜吃的零食,一小册英语课本(她仍在自学),一条小围巾,一本诗集,几件旧的替换衣裳,就骑上车头也不回地出门上班了。她的家在距离市区只有五公里路的郊区乡下。她那时正在读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一本诗集是顾城的《黑眼睛》,或是《古诗一百首》(我记不大确切了)。她对诗歌的爱好由来已久,仿佛生下来就会读诗。诗歌进入她的眼神、举止、声音,就像她乡下家门口那片四季喧腾、而万籁俱寂的田野。就像大自然中的风、太阳、月亮、晨露,草地的芬芳,河流的迂阔起伏。就像一个下雪天的空气进入新婚的房子里,进入新娘子羞涩的心情,健康晕红的脸。就像月明星稀的晚上,夜空洒落在秋天,天井里一层淡淡的清辉……
第四部分前奏曲(3)
她没有能够考上大学文科(她的理想是外语或中文系),显然,连自己都有点意外。而她家人则感到失望。这一结果将表明,冯姓的家庭这一辈人里将不可能再有人踏进高等学府。她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一个弟弟,年龄尚小,而且已经被重男轻女的父母亲宠爱得不行。她在学校的成绩,一直都很好。而她又是那种非常少见的倔犟脾气。因而夏天里生过的那场病,以及高考落第后失意的印迹,都反射在我们最初相识时她那张脸上。
她看上去要比一般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结实,也比别人文静。一种狂野的文静。但前者——狂野……——则隐藏得很深。恰恰相反,目光差一点的人会以为他们看见的是容易厌倦或有气无力。总之,她身上总有些什么让一般的人不敢轻易走近她。她的微笑看起来像反抗。她的拒绝看起来像认同。她很喜欢热闹人多的场合,但却是因为她渴望在此类场合中更好、更完整地品尝自己的那一份清静寂寞。她很随和地笑着,凑在同学堆里瞧热闹,但与此同时,她那一颗心却明显地在别处,飞到了一个近乎于空无 ,不可知,但却肯定是遥远的地方。而且十分镇定自若,仿佛她在下意识中玩这一套把戏时已经绝对肯定四周不会有人看出来,识破她的真相。有时,她像个突然失去了自信心的小偷,站在热闹的超市里,不知该拿自己怎么办。她的若无其事和她的慌乱、慌张可以说是她身上最出众的两套女孩子的本事。我很快完全地被她迷住了。我知道,并且差不多用自己的鼻子闻到了:这一切都是女孩子的柔情。是情窦初开的少女特有的一种秘密的炽热。秘密的情欲。仿佛有一只斑斓的火蝴蝶从那里飞出来,腾飞而起。她使我的耳根很快滚烫起来。她晶莹的目光在我身上滚动,宛如从天而降的天籁。因为,她跟世界的关系只有两种:信赖和不信赖(她就有这么固执!)……。不信赖,她已经学会了简单,原始,马马虎虎的伪装,而且看起来每次都能蒙混过关。至于信赖,就像童年的事物。她很少能够找到。但她却把这一罕有之物,从一开始就给予了我。于是,我就像从末见过大海的内地人被一种奇特的旅行一下子扔到了湛蓝的海边;在空荡荡、完全洁净自由的沙滩上……
当我们彼此用目光流露亲昵之情,她的脸上就会现出一种如同入定少女一样的光彩来。这时候如果有旁人的眼睛注意到她,没有一个不会被她略略腼腆的美貌所打动。那是一种仿佛窖藏已久,从遥远的过去飘然而至的美。一种古典,同时又充满真正少女气息的美色,被古代中国的诗词所长久封存的少女仪态,格外端庄,清纯、热烈。也格外纯朴,似乎,这是一种她自己也心仪已久的境界。突然有人在耳畔悄悄告诉她她已经具备了,已经有了这一幸福的权利……;于是她慌张得手足无措,并且无端地忧虑,害怕起来。
她的这一幸福感来得很短,她的忧虑则来得很长、很快,被一种哭泣的愿望俘虏住了。
她向周围的每一个人看,试图证明自己的感觉,或者,弄清楚此时此刻自己究竟身处何方。首先,这样一种求助于外界的事态本身,足以扰乱她的心房。因为她以前几乎想不起来,自己在任何时候曾经这么做过。其次,周围的人,班上的同学们逐渐地确实给她了信息,给她肯定的回答。她又一次被这一回答吓了一跳。情急之中,她就像一名客人来访,已在大厅门前按响门铃之后的期待中的家庭主妇,本想仓促间换上一件体面的衣裳,一不小心,却又把通往卧室的房门给关上了。天哪!她竟然没能留意注定要从阳台外面吹来的那股空间的热风。风把房门关上了,而她手中没有拿钥匙——身上披了一半适用于社会场合的衣裳也前后穿反了……
于是,她又偷偷、像做了件错事的小学生一样看我,试图在我身上找出那怕一丝的安静、正常、没事发生的表情。或者说,她暗暗地祈望我,能像以往一样从容。并且,从容之余,还能悄悄流露出一点对她个人很特别的爱护。那知道我这边,也早就像被火烧着一样急叫起来!对于女性,我虽然在那个年龄,仍比较迟钝,但却有一种可称之为迟钝的贪婪。我不可能不会有反应!我虽不是求之不得,却也期待已久。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甚至想都不可以想这个问题,一想,上课时就分神,并且整个人就像患上了一种奇怪的舞蹈病。
她是从第二堂课开始加入到诗歌班同学的行列中来的。她溜进教室,夹在稀稀落落的同学们中间,像以往一样不为人注意。我怎么可能对她有特别的印象呢?上课之前,底下的台位照例“乒乒乓乓”一阵乱响,大家就座。因为来得早,她坐上了自己中意的第二排位子,靠近前排,甚至也靠近右侧的教室大门(一般女生都比较喜欢,进出也比较方便)的地方。她第一课进来时,我应该仍旧昂头在黑板上抄写课文。我每讲一课必定要至少抄写一首诗到黑板上去。我的教学材料太过简陋了没有条件给每名学生印行一册课文范例。于是,我带头抄,学生们跟在后面抄——逢正式上课,我再逐句逐段地讲解。我第二堂课讲了些什么?萨福?狄金森?保尔·策兰?我大概不会那么快讲那名希腊女诗人,因为前一堂课是茨维塔雅娃。是的,她们俩都剪着齐颈的短发,甚至,脸部过份严厉的表情、眼神都有些相似。这是为什么?这是命运对我呼唤的回应吗?英子的短发看来剪得更薄一点,头发根根也显得硬、浓黑。在我讲这堂课之前,她知道她吗?她不知道,但看一眼立即就喜欢了。后来则是喜爱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