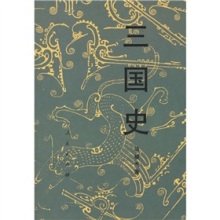爱的罗曼史-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粢廊辉诮盘こ盗刺跚逦淖小D浅底佑卸嗲嵊叶运纳畎陀卸嗝床豢勺圆Α诟裢饧啪驳睦杳鞯暮铮液鋈豢牡孟肼蠼挚癖迹笊腥隆N壹ざ蒙砩舷穸溉宦淞艘徊阊┮谎肷硪徽蠖哙拢∽阅且院螅乙舶狭舜游壹业较匾皆旱哪翘趼砺贰N腋鋈恕冻霭<凹恰返南呗吠迹荷角奥贰喙贰偕铰贰V屑淙埔桓鲂⌒〉腟形。寿山路往东就是红十字会医学大楼。门前有个半圆形停车场的县医院,路旁的老房子散发着一股废弃了的私家园林的林木气息。
第四部分少女的祈祷(1)
一种贫困、卑贱、低矮屋顶下的生活,
知道苍穹的各种巨大轨道,
穿过乌有之乡,除了它自己小屋里的白昼或黑夜。
——乔治·埃略特
我即将要回到那个下雪天。先是整个县城的夜——全城有一种腌臜暗黑的电影院味道,走廊过道座椅底下,是一踏上去“卡嚓”响的花生瓜籽壳声音。而后,她在拐向体育场正门那条朝东的岔路上,那棵长得很高大的香椿树下面喊我的声音——我的名字——穿过了全城的黑夜。我后来深信自己那一晚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有力气和脑筋把我从县城的任何旮旯角落里挖出来。她不用用手挖,轻轻喊一声就足够了,好像台上变魔术的人对自己手里的手帕喊一声“变!”,我就是那只腾空而起的命定的白鸽子。那是1989年农历的小年夜,距离正式的春节还剩两天,这之前我们夜校的课业已经结束,告一段落,学生友朋皆已星散。乡下去吃喜酒那一晚过后我们犹有过几次相见,碰面,聚餐,等等。然后……然后——
有时我想,我一生只受到过一次召唤,只耳闻一次明白无误的心灵的声音,那声音就由那一晚上的她心里面发出来——这一次召唤过后,我的灵魂的听觉完全沉寂了……若是上天许可,仍会指使某个可爱的嗓子在风雪之夜里朝当街愕然的我叫喊,我一直暗暗期待,但之后再也没有过。在那种神圣的召唤面前,我仿佛已永远消亡、不再存在。我们整个相爱的几年里,双方都有对彼此的各种不同的低唤或称呼,但那只是在完全平淡正常的情境下面,没有一种情境可以比得上1989年最后的倒数第二天的夜间。她是在完全孤身一人,并没有明白无误地从大街上看见,仅凭一种直觉和深情大声喊出我名字——而恰在那会儿,我正好看完电影(我看电影也纯属为了对她的寻访)出来,在回家途经的路上——如果不是她喊得这么果敢及时,这么动情,我们的爱情故事不可能这么缠绵深沉,我心里也不会有这么多美丽的光亮……她喊一声我名字的声音是全部乐曲的音叉、音准,构成最热烈的和声。如果世上每一对相爱的恋人都存在一部分和声学的话。
那天傍晚,先是周遭一切暗沉沉、阴碜碜的灰黑,大街上风吹得行人全像菜场落市时的白菜叶子。一个典型的快要落雪的傍晚天气。我在几名熟人胁请下——他们全都注视着我的闷闷不乐——到一个朋友家吃火锅。起因只是因为他从乡下家里弄来了一只老式的铜火锅,加炭烧那种。大家都对现在还有这样老式的东西兴奋不已。此外,我们一帮青年是仍处于反叛的年龄。逢年过节从来不屑于留在家里,和父母平平和和一起吃那些花样百出的染上古老习俗的菜肴,而情愿到外面什么地方喝碗粉丝汤,以示对传统文化之轻蔑。我们在那些年里都是这样一副德性,那天晚上,我那个朋友家里菜肴还很丰富,准备了很多火锅的料头,只是一桌人望去,无一例外都只有25、6岁,都有做单身汉的预备役表情和……危险。他们切出来,端上桌的菜也像准单身汉弄出来的一样配置粗率、全无讲究大大咧咧。平常我在他们中间一向妙语连珠,可在那天天黑前后,却像后脑勺挨过了一闷棍那样一脸苦楚,闷闷不乐。大家在热腾腾的火锅(按本地习俗,小年夜是一家人裹馄饨吃)面前开吃开喝之后,我仍冥顽不化,一脸苦相。实际我自己并不知晓,只是心里眼门前来回晃荡着一个她,心里委实思念得厉害。你怎么啦 ?他们问(朝我大声喊!)而我置若罔闻,被追迫几句后才回答,肚子不舒服……。他们也就半是疑狐、半是谅解地放过了我。
那确是一种类似腹涨、肠绞痛般的感觉,不知道年月和饥饿,只是本能地想弯腰,用手去捂住空气中某个溃烂的伤口……的没出息样子。恋爱过的人想来大多有此体会。在这之前,我们已经两天(加两夜)没见面了。而她曾告诉我她在过年前后的行程,初三下午值班。初五上班。大年夜(除夕)放假。小年夜(也且今天!)是上午上班,下午开始放过年的假……那么下午呢?现在天黑了,这么坏的天气,她会不会已经骑车回乡下的家里?恋爱中人总是深受想像力之苦,凡想像力够不着的地方,总是他们的心更容易执著进去,更固执和枉费之处;他们的大部分生平,都逗留,游移在这一大块悬崖的边缘、蛮荒之地。他们的身体都本能地朝向那边。明明有太阳,却仿佛向往更深的黑夜,仿佛是一大群广漠天空的图腾者……我在那只火锅面前动的就是类似的郁闷的脑筋。我的坏情绪显然感染了那一桌朋友,大家吃着吃着,声音慢慢就小了,说话,吃菜的动作都稀落下来。
“那怎么办?我帮你找黄莲素……”
“酒要末别喝?”
“嗨,没事,肚子算什么……”
他们七嘴八舌帮我出主意,谈论我的腹疾,而我忽然站起身来,表示先走一步。“那——赶紧吃一碗饭”主人说。
饭盛来,我匆匆扒了半碗,就往外面暗黑(天完全黑了)的夜里一钻。朋友家朝南的大房间门一开,就有一阵夹杂小雪片的寒风扑面吹进来。
“再会”。我头也没回,嚷了句。出了门,才发现自己竟然还手捂着肚子。
第四部分少女的祈祷(2)
我担任夜校的文科教师期间,认识了不少社会上的朋友,其中有一帮大学毕业回来,分配在县医院的业余足球迷。我们甚至还和他们一起组织过比赛。小年夜那晚我寻到医院去,经过门诊部到住院病区那条阴森森的水泥过道时,我一眼看见墙上的橱窗里排列着许多介绍院区医务人员的照片文字,我甚至停了下来,似乎饶有兴趣地扫视了一遍那上面有没有熟悉的面孔,有的话,应该是那里最年轻的几张面孔。这一回忆颇感真切的细节那一晚上似乎缓解了我部分的紧张情绪。我一生都厌憎任何医院。自从我妈妈上两年(1988年)去世以后,这是我第一次迈进医院的过道。整个事情像一个梦游的过程,只有朝西的走廊墙上医务人员那一排照片,使我在那一晚曾有片刻的清醒,通过它,我记得自己当时曾有多么惶乱。当我走近县医院那幢大楼时我有一种虚脱了的犯罪感。我的脸色恐怕不比杀人犯更难看。医院周围特有的那股药物气味差点窒息得使我转身退却。我把自己那辆脚踏车停在医院大门口,独自站在停车场上像一枚寒流中不停打旋的枯叶。我不停地自责这一行为有点类似于勾引。她还这么年轻,初涉人世……。俩人的将来会怎样?我能真的对她好吗?我本能地意识到,自己即将跨出的一步是多么重要。只要鼓足勇气,往木楼深处迈那么一小步,自己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很清楚自己正在干的事情,我是在去往一名单身女孩的宿舍区房间。在之这前,我们已经有过很多次搂抱、亲吻,但全都是在马路上,在野外,俩个人还从没有过单独,无人打扰的房间。进入那样的一种狭小空间就意味着将要进入……个人完全的私秘区域。而在这之前,她并没有邀请我前往。她住在医院家属楼哪幢房子,我只有个大概念头。准备寻里面的人打听,而我这样冒冒失失一路打听上门,没准,会让她大受惊吓……。我去干什么呢?她真的很爱我吗?为此,可以谅解我的粗卤闯入?再说,她不一定会在屋子里。她这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呢?我脑海中全是她红扑扑,孩子气的脸蛋,齐颈的、蓬勃的黑发。当我经过医院大楼时我仿佛是在卡戎的渡船上,正在迈向一道地狱的门槛,周围的门诊楼室,药房、飘然而至的医生(穿白大褂)和靠墙放的木头长椅(空无一人)全似鬼魅的幻影——只有东墙上那一排橱窗照片使我稍稍回到现实世界,松了一口气,那些半陌生半熟悉的准工作人员面孔和表情,似乎在提示我有关现世生活的话语和讯息——当我站在那排宣传橱窗面前时我惊奇地察觉到自己发烫的呼吸和额头。我浑身上下被一种忽如其来潮水般的情欲所燃烧,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男人,也有点像少女初来月经时的惊恐,一样生涩,陌生,夹杂微微的喜悦。我整个人像是被人当头浇上一盆冷水一样失魂落魄。我有一种想寻人倾诉的冲动,而又克制得很厉害,很得体。我每往前从容走一步都是残忍的——真正的我应该在另一行为和空间内,而我却找不到。这些忽如其来的情欲使我有生以来初次相信,我自己是多么可怕地耐下着性子……我就像一名凶手急急地要去杀一个人,或暴徒要冲破那囚禁着他的铁屋,秘密地从光线昏暗的病房区经过,整个夜晚静悄悄的过道,只听得见我自己的脚步声孤零零地回响,在我听来,那却是我自己的心跳,固执,难过……
我像是行进在一个地下坑道内,四周全是某种古怪的黄澄澄的暗影。医院的墙,墙已老了。医院的走廊,这还是距今六七十年前民国年代的建筑,连墙上的宣传栏,那些文革时期的标语样式,也在支数很小的灯泡光晕里暗暗衰老了。时日和节令,那一天是小年夜,农历1989年最后的两天之一,那条从门诊部去往住院病区的长长过道仿佛是在为这年关尽头的一天塑像造型,也许,我在县城里已经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去处了。它有一种美学形式。人们用走廊前后匆匆而过的陌生人的脸为自己送葬,为那过去一年逝去了的岁月。我碰到了六七个住院病区的人,家属或陌生的探访者。我暗暗惊讶于这一份无端的见证、淡漠的邂逅——他们就像是刚从地狱里走出来,身上有一种夹杂惋惜和无所谓的气息,一一把自己所探视的病人对象留在了那寒夜过道的另一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夜医院周围的气息。那种各类药物、垃圾、人体和自然界的空地园圃相混杂合成的非人间的气味,在寂静的医院走廊里,人的气息是某种文静的自弃后的无所谓,医院的气息深处则有一种由残酷的灯光黑夜相搀杂的镇静的杀戮,使我联想起我小时候在城郊看见的屠宰场,这里也有跟平时的屠宰场里一样的安静,但这安静却隐含着不祥,阴影或彻底的失去理智。灯光沮丧地从头顶洒落,使人误以为那是心脏停跳的死者身躯上松开的白绷带;我经过那里去看我的心上人时心情格外的凄凉,不知为什么,那天晚上医院的气味频频刺激我回忆起来我的童年,也许因为县城上空已零星响起年关临近的炮仗声音,而我在自己每向前跨出的一步中停止不前——就像在小时候的这一天,我对于亲人的存在和关怀格外敏感,似乎要比一年中的任何一天里都更依赖于他们的笑靥,他们的一举一动,而难以忍受这黑暗和寒冷中忽如其来的孤单一人。听着外面天空上的炮仗声音。我几乎要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