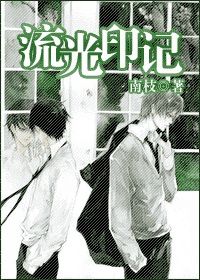流光容易把人抛-第6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女帝静听下论,“哦,你且说来。”
“是,陛下您瞧,”女帝顺着俆止指引,望向棋盘,“臣这一片苦心经营,不料陛下突如其来的一笔落下,皆付了东流水,陛下胜局已定,臣又何须挣扎?正所谓,举大事者,必有天助之。一些意料之外的状况,也可以反过来利用,使之成为有助的风。”
女帝静静望向俆止一张一合的嘴,半晌,微有恼意的脸乍现微笑。
“俆止俆止,若没有你,朕已不知如何自处。”
俆止自然推辞谢恩不言。只是低下的头颅上一颗清明不曾更改的眼睛,安定祥和,望着地面,谁也不知道他心中究竟是怎番打算。
更那堪回想,孤仕去兮不复返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
立谈中,生死同,一诺千金重。
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 斗城东。
轰饮酒垆,□浮寒瓮。吸海垂虹。
闲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
似黄梁梦,辞丹凤;明月共,漾蒙孤篷。
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
鹖弁如云众,共粗用,忽奇功。
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击取天骄种。
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
……
徐思远是最后一个被放出的武举人。
刑部大堂门庭森严冷肃,不知藏有多少凄怨的怨气,又有多少冤魂至死亦不瞑目。这看似庄严堂皇的景象,落在她眼里,反倒似讥讽,似伪装。
心中隐有悲愤。面容却如灰烬,了无颜色。
强作的公平公正,可这世间又哪里有公正可寻。若是公平,为何需要铤而走险。若是公平,为何会有死亡。若是公平,她有怎能活着走出,得见日光惨淡。
她为什么还活着。徐思远不解,只觉荒诞,女帝怎能容忍她活着?
她缓步踱出,神色不卑不亢,不喜不怒,脚步亦不快不慢,不急不缓,甚至平缓倒刻意的地步。
一路走至台阶前,反而停住了脚步。
伸出手,衣袖障目望向天际,见天空细雨微微。雨势从大雨蓬勃到现在小雨不断,纷纷飞飞,已过了几个时日。
身后有人声不迭催促,“徐探花,你既然洗脱了罪名,那便早点离开吧,这里不是久居之所。”
徐思远应了。
却不见脚步有什么加快。
她的每个步伐都坚实有力,不曾虚浮,仿佛方向明确,举重若轻。
可真实的她,又清楚前途何方,路该怎么走吗。徐思远如是想,如是所闻,想及此甚至流露出一股自我嫌弃的神色来。又似嘲笑。
世间事本荒诞不经。她满心嘲弄,嘲笑皇帝老儿,嘲笑百官重臣,嘲笑螳臂当车之人,嘲笑英勇赴死之人,嘲笑自作聪明之人,嘲笑莽撞斗狠之人,嘲笑浑水摸鱼之人,嘲笑不知所谓之人,嘲笑自己。
她满头满脑皆是荒诞不堪,徐思远面带恍惚笑意,却不防有人突然站在面前,挡住了她的去路。
徐思远猛然刹住。
别人逼至面前,她方才发现来人汹汹。
入眼的那双布鞋针脚细致,布面干净,一看就与她这个刚出牢狱的寒酸人截然不同。
徐思远再抬头,一席儒雅长衫,清清爽爽,待与来人平视时,徐思远方才认出来。
不,她甚至不敢辨认。
——竟是他。
一时她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怒,是该出乎意料,还是做出一副早意料中的神色来,犹豫半晌,只得苦笑,“竟然是你,不,果然是你,不不不,都错了,应该是,——怎么还是你。”
一席长衫,做儒生打扮的憨园,挡在了徐思远面前,带着一抹神气,微有些趾高气扬,却又与寻常人的得意神色不同,他同样回望,望到徐思远眼眸深处,方才笑道,“你终于被放出来了,钦点的探花,怎么能如此狼狈寒酸呢?”
话语未完,他便牵过徐思远袖口,声线如此明朗,连天空乌云都要被清扫干净一般,“今天我做东,就算当初得罪你的赔礼,我们寻乐子去!”
寻什么乐子,她又哪里乐得起来?徐思远想摸摸鼻子,却不防被憨园突然使力向前,弄了一个踉跄。
走罢走罢。
似乎所有人的悲欢疑虑,都有人费心安抚。
又有谁去安抚死去之人一颗未曾平复的心?
女帝收过最后递交上来的报告,仍旧无甚大发现,衣料皆是今城余香斋出品。这个余香斋专供平民衣裳,人人皆可买。鞋子布料仍是今城出品,就连手中原本带来的剑,也是今城铁匠铺里的一把普通拙朴剑。刘臾等在薄上写得是出生锦官城,翻遍了整个锦州,却没有任何线索,居然是个却双亲死绝的孤儿,无人知无人识。
堂堂圣音大国,一时竟被这个杂碎玩弄,岂能容忍。
偏偏这杂碎,通身上下,如同乌龟一般,裹得严严实实寻不出破绽。
女帝银牙一咬,一把将手中书页甩砸在地上。
她今日在早朝上,被朝臣连番上书攻击辩驳,勉力支撑,心神俱疲之时还得遭遇这种烦心事。
只听得女帝语气阴冷冰凉,饱含怒气冷笑道,“找不出纰漏?那留着干嘛,挫骨扬灰,让她死了也没有容身之地!你也跟着把自己烧了,没有处理好就别来见朕!”
官员战栗,颤抖这声音应了是,蹒跚着退出殿外。
出宫后,还来不及擦拭满头冷汗,只急急吩咐,将贼子躯体带去焚烧。
焚烧厂里总是一片惊悚阴暗,蕴冤魂缭绕不去,阴冷似人间地狱。此时更是阴沉沉,无一丝阳光,仿佛死神持利斧沉默阴狠的盘踞驻足。
却又烈火骤起,火焰间似乎隐隐有骨骼碎裂声,甚是恐怖。
官员手腕微抖,颤颤巍巍的掏出手绢来抹了抹面颊上的汗珠。
拔节的浓烟一时带着刺鼻的呛味,没多久便染成了骨灰粉末,拔节的大火中隐约可见一个暗影,在黑暗间挣扎幽咽,魑魅横行,却在无边烈火里逐渐消失。
这般的灰飞湮灭,惨淡收场,不免让人徒感人生无趣。
挫骨扬灰,死了连捧祭拜的黄土都没有。
——可又有谁会去祭拜。
乱臣贼子,天下诛之。
徐思远被憨园拉拉扯扯的往前走,心中悲愤绝望又麻木。师母吩咐下的局,她们设了,师母吩咐做的事,她们做了,这一切她们尽力却无法成功。
以一己之力,行刺一国的皇帝。本不可为。
她的师姐已然为此死去,而她自己去成了一个劳什子的探花,还莫名其妙被这个男子拖着不知去往何处。
以她为饵,为引开视线的物,以她汇集众人注目。
而师姐在旁窥视,伺机而动。这本是一个必死之局。
她有赴死之心,偏偏师姐阻拦。飒然一笑,说:“师母有命,我心中也有天下大义,不公之事我亦无法吞咽。——这必死之事,何必多搭上你一个?”
整个人生仿佛凝聚成停滞的瞬间,迷迷茫茫,混混沌沌,一场大梦。不知前途是什么,更不知道脚下的路,又往何处通行。
南湘躲在王府之中,她知道此刻风声紧,时局又尴尬,她最好谨慎行事,所以越发的深居寡出。
她看看天,赏赏花,处理处理事情,时日便过了。
杏则在乱局中,频频出手。她是要趁此机会,尽力得到王女吩咐下的事物。王女生出归隐之心,所必须得到的便是一纸新的身份,杏抿了抿嘴,乔装易服,看着面前这块牌匾,户部,心中一时竟踌躇满志起来。
眼看着风波起,风波又平,她端木王府身处其中却不受风雨,南湘捂着嘴,悄悄打了个哈欠。
相背对秋风,我病君来高歌饮
外面风雨不住,可不影响南湘思考她的前途。
她无野心。只求平安脱身。
前途难料,逃离更需趁早。
外界狂风骤雨不断,南湘远走之心越发坚定。眼见着外面混沌喧闹,朝廷六部各司命也是一团乱局,杏趁此机会,将伪造的文碟户籍假身份制好,在今日早晨,递交给了南湘。
南湘抚弄着来之不易手间被细绒布包裹完好的事物,垂眸半晌无言。
谋划是一回事,实物真正拿在了手里又是另一回事了。
杏见南湘默然观望,也低垂了睫毛,静静道,“殿下吩咐购置的田地庄园已经落实,巣洲,锦州,曲沫这三个边境州衙都有房产。今冬,便可修葺完毕。沿途各处驿站也打点料理,车马完备,随时可以动身。”
南湘手指下意识的在绒布上抚动,静静聆听,到最后听到随时可以动身时,方才微微露出点笑意。
终究是要走的,心中何必退缩犹豫,南湘默默微笑。
杏压低的声线的秋日清晨的晨光里清澈冰凉,让人舒爽,仿佛秋日长风萦绕不去。
“府中内库中各种不易搬动的器具,在这段时间里大多已抛售租价出去,所得钱财已购置房产,店铺,其余则分散存入,换为可兑换的银票。王府外库为稳定大局,暂时没有移动买卖。只是即便如此动荡,能瞒住上下,可未必能瞒住管事的谢公子,再有府中各位公子又该如何处置才安稳妥当,还请王女示下。”
南湘抿抿嘴,缓缓点头。
走时必定要走的。她吩咐杏做好的事情,她确实未曾辜负期望,准备得齐齐整整。
南湘同时也分派给梅容手中酬堂,依靠他们灵通手段,在偌大圣音疆域中先行探索。指派给憨园的任务,收集的资料也早已放置在她几案之上。
只是万事俱备了,欠的却不止是一股东风。
如今该思考的,不止是偷偷摸摸准备万全,更是要寻觅出一个被放出今城的机会。
依她打算,乃是一片安定祥和仿佛举家出游一般。若能大大方方出京,那她便自由自在走遍四方,先领略此间山水,沿途不忘寻觅回归家园的法子。如果依旧是毫无头绪,她最后还是可以去那飘渺神山,在那个神秘的化境里设法寻找归去的方法。
想法是好的,可关键是如何出京,以怎样的姿态出京。
光明正大的封王离开?
偷偷摸摸谨小慎微的毁灭这个躯体名头,唤作他人重新再生?
离开,真有她所想象这般容易吗。
南湘在杏微待担忧惶惶的注视中,默然叹息。
*** *** ***
——“王女可还记得国风公子。”杏见南湘沉默,抿抿嘴,突然出言。
南湘应声抬头,看着杏平和温和的双眸,又移开目光,接道:
“国风是我的未婚夫婿,那又如——。”
话到此处,南湘住了口。
杏低头。
两人心知肚明,恍然大悟。南湘微微顿了顿,最后还是将后面一句,——“那又如何”,吞回了嗓眼中。
杏言尽于此,低垂了头静待南湘思虑。
国风。老丞相清流一派的首领,虽然现在功成身退却依旧拥有极大影响力的老丞相的唯一的儿子。是先帝思虑许久为她定下的亲事,其间纠缠牵扯,动一发而牵动全局。
再加上,按圣音律历,成年的王女王子在成亲,娶得王夫后,自当分封王爵,成一介王妃,受领封地。这样,若要理所当然的出今城,便容易起来。
这是一把怎么也不会输的棋局,但是——
但是——
棋局只有黑白两色,落子的只有面对面的两个人。可是,这场婚姻,却是一场多人的博弈,它不知是棋局,谋划,布局,落子,它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博弈。
牵扯角色太多,老丞相的态度,皇宫中女帝凤后的姿态,朝臣百官,那个黑衣丞相俆止,还有南湘本身的私心,与之相比之下,国风本身的意愿显得这么微小,不足以考虑。
其抗拒,冷淡,和推拒。她目睹感受。即便后面态度有所转圜,他们彼此写信,述说生活和思想,总算有所进展,也仅仅是笔墨之交罢了。
并且事件的关键还不仅仅在于国风是否甘愿与她结为连理。女帝会容忍她与国风家联姻,

![[暮光]菜谱不是辣么容易改的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15/1549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