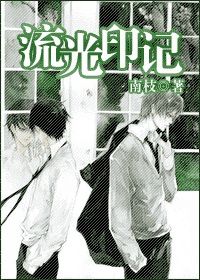流光容易把人抛-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百川终究汇入海,新力量的崛起如春潮浪涌,不可阻挡。
南湘昏迷中错过了许多大事:新皇登基,大赦天下,丞相告老未准。朝堂如市场,争抢喧闹得近乎不堪。势力增消间此落彼浮,一片混乱景象里,一介男子登上了百官之首的丞相之位。
姓徐名止,虽为徐世家嫡子,平素却是不显的。谁想,今日一朝亮剑,竟一鸣惊人。
老丞相,即国风之母,在新帝登基初始,便欲告老辞官而去。
新帝百般挽留之下,遂暂留今城。
只是丞相抽身官场的心思越发明显,朝廷原有一股清流,随着丞相逐渐退隐而缓慢消散。有的黯然离去,有的心灰如死,告老的告老,辞官的辞官,即便是留下的也不成一派,疏疏落落散在朝野。
新帝一指未动,朝中老臣便去了大半有余。
徐止,性深沉,平日喜着黑衣,行事诡秘,又被称为黑衣丞相。短短日子,便已树立其威势,众人迫于淫威皆俯首。只背后议论不断——
一介男子,区区男人,竟然登上百官之首丞相之位……哼哼,指不定也是同前朝宵姓男人一样,以色侍人……不知用了什么下贱手段,谋取到手,哼……说不定是女帝禁脔呢?……
话到此处,又忙住了口,彼此交换一个意会暧昧的眼神便过去了。
留下一个暧昧残局待收拾。
朝堂间,老臣离去,所空出来的缺省,尽由新帝历来培植心腹担任。世家子弟填充其余空位。贫寒庶族学子除了争抢其他剩余有限的职位外,几乎无出头之路。——拓宽人才获取渠道,亦是新帝心头之患事。
南湘自苏醒起,一直被软禁府中,朝廷这一系列变动自然与她无关。自一开始,南湘便被排斥于朝廷之外。
只是皇室血脉本是单薄,刻薄如女帝亦不能随意提及杀伐二字,此乃南湘之幸也。
除却被软禁的南湘外,单薄的皇室只剩当今女帝以及与南湘同父所处的皇子碧水南漓。几个异性诸王,如巣洲王元白等,亦在先前削藩剪除中逐渐不成大气。
南湘被软禁府中,就连身处今城,却也无法观望一眼。
她只能阅读书籍,从字里行间慢慢填补她心中对未知世界的空白认知。
圣音地处南部平原,东面是海,气候润湿,四季分明。今城是一国之都城,寒江离水在此处交汇,又不回头的奔往更远的地方。
圣音背面是北国,到处被冰雪覆盖。
南面则是性情平和的大奚。而被崇山峻岭阻挡的,则是畅国。
南湘翻阅书籍,既好奇又仰慕。
天下如此之大,你知道天下如此之大,却被囚禁在一处狭窄之地。她自觉自己仿佛处在一件能看见风景的房间,心随一张张绘制并不详尽的地图而飞远。
若能出门寻访,若能亲眼看到冰封的山谷,富庶的国都,那出产精巧物品的隐藏在大山之后的日出之地,那该多好。
天下如此之大。
而不知新登极的女帝,心中的天下又有多大。
南湘坐井观天。她在春日阳光下喟叹。天下之大,她却只能坐井观天。
*** *** ***
众人皆忙乱,只有抱琴这家伙,一向喜欢架桥拨火隔岸观火。
他顶着一双漂亮眼睛,忽闪忽闪的看你出丑,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这几日他见杏对自己闲散模样很是不爽,内心也颇有些只一个人玩乐对不起兄弟们的意思,这几日雨下大了,也寻了件事情干。
“——这府邸积水啊,经忠实的侍从抱琴我,亲自查量受灾程度得知——最深积水处已达到我膝盖部,不幸的是,因亲自检查又遭受积水侵染,糟蹋了我那件得来不易的冰丝长袍之外,还有其他小小损失,例如小厨房被所淹,所储存的部分食材受潮,酒窖不幸被水覆没,美酒变为脏水一窖,——幸好无其他人员伤亡,淹死的猫狗不算。”
“至于其他的,像是房屋漏水啊、墙壁侵湿啊这些,已吩咐工匠加紧修补,重新涂漆。雨季一到,王府修整期也到了,真是忙啊,咳——”
杏、锄禾、墨玉轮流甩来白眼。抱琴出力不讨好,悻悻躲回墙角一个人呆着。
往事皆不是,人间空唱浮生梦(一)
“杏,怎么今日还不开饭?”南湘扑倒在桌上,只觉饥饿难耐。
“王女杏鲁莽,杏倒觉得在王府就着这□在外野餐,会更有情趣。”杏一脸的笑容灿烂,堪比灿阳,朝南湘递过一壶茶。
饿了先喝水是么——南湘哀怨。
接过茶碗,闲得无事,托着碗刮着碗底,优哉游哉等着用膳。
“王女,可是杏刚才遗漏了,未告知王女么?”杏目光无辜,笑意切切,言语正经,“王府修整,工匠们正加紧修补,主屋自然也在其中等待休整,所以——”
所以——
一日晴早,王府内院。
铺桌子的铺桌子,放盘子的放盘子,安凳子的安凳子,设餐具的设餐具,一边百无聊赖的当然还是在乘机偷闲。
等南湘刚坐下来好好吃饭时,抱琴倒是优哉游哉的回来了。
“王女好雅兴。”一屁股坐下来,朝南湘客套一句,便不客气地拿起筷子夹菜,墨玉坐在南湘身边便觉满足,笑眯眯的啃着筷子望着南湘。
这墨玉小孩子,不争气只顾着发花痴顾不了其他,抱琴又是一一人吃饱全家饱的主,正经事指望不上。
只有杏锄禾两人正正经经的伺候在一边,南湘看着别扭,便挥手让他们都坐下一起吃——
难得一次野餐,虽然说只是因为房屋装修,被迫在家门口搭家伙,不过也算是难得的休闲。
反正,也不坏。
时值和风适宜,晴好知暖的好天气。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难得有个晴日。
春风扬起浮云,端木王女碧水南湘,率内侍墨玉、抱琴、锄禾,总管杏等在王府后院一角架炉起火设桌野餐,此谓春日踏春是也。
至于好好一次野餐踏春变成现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情形,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难以用言语形容。
瞠目结舌,奇奇怪怪,白日闹鬼,莫名其妙。
一切本来都是好的,摆上一两壶美酒,三四个合心人,五六盘小菜,七八碟点心。行行酒令,捻捻花签,再乐不过。
而她只是稍稍吃多了些,胃部微有涨意,便放下手中捏着的筷子,慢慢站起身来,稍稍走了几步,再不经意的抬眼,却正好看见到了什么。
到底看见了什么?
等南湘事后回忆起来,仔细回想,还是不得不说,那简直就是个鬼影,实在让人胆寒。
这王府本来就足够宽大,宽大得不像一个府邸,倒像一个人民公园,有足够的空间让一个影子用极缓慢的速度靠近。
由小变大,由远变近,仿佛一个拉长了镜头的缓慢特写。
南湘只觉惊悚,准备唤人一起走人时,却赫然发现,刚才还围在一起抢吃抢喝的几个人,这一秒却消失得彻彻底底。
除了这一片惨不忍睹的狼狈局面,一个人也不剩。
南湘眨巴眨巴眼睛,内心更觉诡异,便再转眼望过去。那鬼影现在在哪?南湘手搭于额前,努力看得更清楚,如此清楚,南湘甚至看清他一身黑衣,黑发,以及一双阳光中更显得熠熠发光的黑眸。
莫非是,——鬼?
大白日的哪有闹鬼的道理,南湘自我安慰。
她努力按捺住内心的惊悚之情,顺带在心里讨伐那四个没有阶级同志情感将她抛弃掉的没良心的家伙,勉力维持平静。
*** *** ***
“呵……南,湘……”
语尾轻轻挑起,又没在一双磁石般的黑眸中。来人轻轻坐下,黑衣肆意铺散,言语颠三倒四,失心疯一般。
南湘不禁微颤,忍住内心诘问来人,是人是鬼的冲动。
“南、湘……小南湘,你怎会在这?……”
那人来得肆意,像是披着夜幕的黑猫一般,诡异得不行。
南湘心中微有惊惧,来人已自觉坐下。他行事自由,轻扬衣袖,仿佛漫卷长夜似画轴徐徐展开,一双黑沉沉眸子不见光暗。
南湘勉强朝他苦笑,“你得先回答我,你是谁。”
“……呵呵,王女呐王女,难得我如此卖力入了戏,却打动不了我铁石心肠的心上人……小南湘呵小南湘,你理也不理睬也不睬,徒留我相思复相思,徒唤奈何……”
这人,怎么回事。南湘忍住一身鸡皮疙瘩,只觉恐怖。
再这样装腔作势下去,要死人的。
南湘强逼着自己一寸寸的勉强移开目光,不,不仅是这个人,这个王府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都是些不正常的主呢……
这位依旧神色自得,还颇为陶醉,轻轻一甩衣袖,袖长笼乾坤,——那袖子黑底勾着混天穹地的纹饰,扬起来确实有骨子飘飘乎似仙似魔之感。
南湘捕捉到他衣料间不俗的纹饰,她知道这种衣服不是寻常仆役穿得的。莫非,难道,不至于吧——
南湘怪异的从头到脚打量他,却赫然发现,这神经质的家伙却长着一张无比端庄的面容。眉、眼、鼻、唇皆是端庄姿容,偏偏说话举止,这么夸张,仿佛故意做出的诡异模样。
南湘静下心来,仔细打量他的眼,顿生惊讶之感。
这人来得闹腾,一双眼眸却死寂,仿佛不能视物一般空茫一片。即便是嘴里如此闹腾,为何他眼中笑意全无?
她甚至想到,莫非这人精神上有些毛病?所以言行才这样的出位特别,所以杏墨玉抱琴锄禾这几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就因为害怕而撇下了自己么?——南湘不由后退。
又觉得不太对。
南湘撇开那堆胡言乱语,又仔细瞧了瞧。
这人一脸的端庄,言语却神神叨叨的。秀长的眼睛长得秀丽却不失英气。眉也锁得静逸。若他能不言不语,这副容貌,甚至堪堪说得上是烛火香油后的宝象庄严。——哦,他眼角尚余一粒泪痣儿,欲笑欲哭,悲怜天人。
这人容貌,真是一等一的。不差那些贵公子分毫。可他浑身不打调啊——
南湘扫过这张端正得带有些许悲悯之象的脸。
应该是一双多情的眸,却生成静湖一般的冷眼;应是通身雪白才能出庄严之感,他却披着一身黑衣,散着一头黑发,黑得纯纯粹粹。
对立又矛盾。
南湘只觉得怪异。他言语间尽是不正经的打诨中。打诨,打诨,他不是在不着意打诨玩笑么,为何那双斜睨着秀目,却突然带了抹近乎严整凄厉的正色?
喂喂,你又怎么了啊。
——“天干壬癸,律名黄钟……壬为孕育,癸乃揆度……这天地世人愚钝,我亦愚钝,乃至揣摩至天道,仍不明白何谓机缘……”
“……谁能解我心中情仇,谁又知我彷徨处?”
这有精神病院没。
南湘默默无言的转过头去。
“为何躲着我呢,为何你秀丽的眼眸四处辗转,却偏偏掠过了我。为何视我为无物呢,我亦是满心牵挂之人,亦会感触痛楚,亦会觉察伤心……”那疯子懒懒的支手撑头,眼波安静如同一潭死水,可腔调依旧拿捏成这,倒正经不正经的装腔作势,活像是戏子在戏台之上装哭傻笑一般。
可他话语甚至更轻声了些,更戏剧了些,却是一声声叩问着南湘,“您又忘了我么,您又将我忘记了么……咫尺天涯,沧海桑田不过转瞬,亦抵不过您善变的心……”
微微蹙紧眉头。南湘只觉负担再次压来,她本已是歉疚,没想到欠债如此之多,多得让她无力招架。
“算遍了天地,寻悟世间苍生,了寻皇天后土,在女娲案头万千次祷告……却仍算不透你我的命数该是如何——”
男子支着手肘懒洋洋的扯了扯嘴角。那一颗泪痣滴于眼角像是欲哭欲落的泪,
“我是谁——”
笑容消融于唇角,眼中却是殊无笑意,不落点尘,“我是谁?天地命运……我亦不知我是谁……”
他静湖一般的冷眼,与他多情伤

![[暮光]菜谱不是辣么容易改的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15/1549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