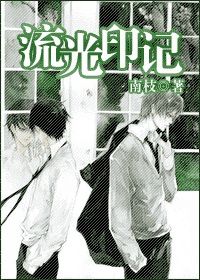流光容易把人抛-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梅容挑了挑眉,只一个动作他依旧做得别人学不来的妩媚“王女生梅容气了?”
“不是生不生气,只是我不喜欢这种方式。”南湘看着他眼睛,她对他着实感情复杂,偏于负面,能像现在这般安静与她对话,已经出乎她自己预料之外。
他并不回答,背过身把盒子缓缓放在桌上,只背对着南湘没有转过身来,好似轻轻一笑,“王女说笑了,梅容今天可是特地来的。”
南湘只觉得有光芒刺背一般,身旁人仿佛是醒着的。南湘嗯了一声算是答应,站起身来,准备送客。
光线如水流淌,雨声细密,过树梢滴落。
春雨清新润泽,只觉金贵。
梅容背对着南湘,身形依旧妖娆不定。
“听说公子胃不好一直嚷疼疼疼的,药石药汤的又起效慢,王女总嫌梅容多事,梅容也知道,不过梅容手里放不了好东西。梅容福薄,也消受不起,正好这手头里却有着以前老朋友送的药酒,想着,呵——其实也没想多少就来了,巴巴的来了讨王女嫌梅容——”
“谢谢。”南湘笑笑。
她努力克制,内心依旧有着自第一次相遇结交后,便拥有的不堪与尴尬。让她实在难以平静面对他。
梅容依旧冷滞,却侧过头笑得妩媚多姿。
他愿意怎样便怎样,后果如何,他不在意,亦不关心。
南湘手里拿着那瓶药酒,轻轻放在窗前的小橱上,她可还不敢随便用药,若是不好,那该怎么办。
——好像有稀稀疏疏的声音,却不是雨声。
南湘动作停了停,莫非是国风苏醒过来,南湘转脸一看又不是这样。南湘侧耳一听后,一把推开窗子。
就见着抱琴混着墨玉在那探头探脑的模样,一下子尴尬尽烟消云散,徒留满肚子啼笑皆非,“都出来吧,这什么样子啊。”
被南湘发现后,墨玉红着脸,责怪是坏人抱琴拐带了他,抱琴则笑眯眯的反说墨玉小孩子心性闯了祸,王女莫怪。
祸水东移还移得这么理所当然的人,南湘还是第一次见到。
一片混乱里,还是梅容大大方方的说了句“病人要休息。”就先走,南湘顺道让他把抱琴墨玉两人带走,才又安静了下来。
南湘坐回凳上,自知刚才吵嚷喧闹,国风必定被她吵醒,遂问道,“国风公子?”
见没有回应,南湘叹口气,自己微垂了头,准备打个盹。
“你好好休息吧,醒了叫我。”
南湘又吩咐小厮看顾着,自己则躺在一边榻上。
窗外雨声不断,雨雾霏霏而降,万物仿佛在雨中消融。
涨水的时节到了。
惆怅黄昏后,时节薄寒人病酒
她本是好心——
时不时检查下国风额头温度,再替他掖掖被角,又吩咐小童及时温药,端来喂下。
她将其看成同寝得病的室友,更加上国风此人地位微妙,南湘自觉如此对待他并不过分。
只是南湘越是体贴殷勤,躺在床上紧闭双目的国风,则面色越发难看。
南湘心觉不对,正准备找来大夫复诊,杏则偷偷扯了扯南湘衣角,出门才对南湘附耳道,“王女不必宣医师,国风公子只是害羞了。”
……
她过分殷勤了是么,可她以前的室友生病了,她也是这样亲切对待呐,还亲自熬了一锅乌鸡白果汤,虽然被嫌弃“我又不是坐月子,你干嘛熬这种汤水”,可毕竟也是一番心意呐。
……
“一会还是让医师再来一趟,刚才梅容送来一瓶药,他说是应症的好药,只是我不懂医,不敢随便乱用,问清楚医师比较好。——这年头,做好人真难。”
“是王女,杏知道。”
杏憋笑,那屋子里躺着的那位多半早醒了,不过面薄,自己王女又温柔体贴,更不好睁眼。国风公子也未必真的心硬如铁。只是心结难解,心病难医,太过着急反而坏事。
杏已将消息传递进丞相府。宫中亦使人向凤后告罪。还好凤后与端木王府关系甚笃,与王女亦是青梅竹马的情谊,并无太大担心。
宫里又将王女拉下的女帝赐下的事物悄悄送出宫来,凤后侍从悄悄嘱托道,“烦请端木王女小心注意,殿下不可时时都有照顾。”
杏连声告谢。
……
……
春的天气,像是善妒的女人喜哭的男子,让人捉摸不透,雨水亦是喜怒不定起来。
国风在端木王府呆了三日,今天丞相府派车接人回府。
从国风进端木王府起,天气就慢慢阴沉了下来,绵绵细雨不断。南湘在国风进府后,便提笔写信。
她如今的一手行楷,虽不算上佳但最起码总算可以见人。
信上几行字,只说是因为国风公子突发病症,一直昏睡不醒,不能移动。王府虽简陋,却不敢怠慢,请丞相放心。待公子病情稍解,可以移动时,自会亲送回丞相府。
碧水南湘谨上。
三日之后,一直持续的阴雨方才停歇。被雨清晰过的天空明朗淡澄,映照得景致一片清朗。
王府中门慢慢开启,女人们簇拥在王府大门前,预备好的马车停靠在门外。侍女先行走下台阶,前面的躬身向前,掀起车帘,后面的则小心的搀扶着带着病容的国风,慢慢走下台阶。
侍从飞快的垫好踏板,贴身小厮小心翼翼伺候在一边。
见国风缓缓踱过来正想伸手帮忙,国风也眼不抬,挥开那双伸来的多余的手,竟自上了车。
南湘将这幕收进眼底,只觉这位公子实在是好倔强的脾气。却不让人讨厌,倒让人感佩。
就她看来,柔弱只能让人怜惜,只有好强的男人才能并肩而行。
即便在女尊国度,也要自己为自己撑出一片天空,这样方是顶天立地的男人。南湘弯了弯眼眸,盛出赞赏的笑意。
这笑意溢出,又被旁边那双精明的眸子收入。
站在一旁被国风称为先生的男子,眸光轻闪,心里暗自掂量。
对别人好意置之罔闻的国风,正要抬脚上车时,脚下却突然一顿。
身后是她,却不知又何日才能相见。
心里一阵空茫。
南湘见他不对劲,身边那男子轻轻一咳。
国风听闻声响,又垂下头,安静上车。
“劳烦端木王女搭手相助了,王女之举,实非谢字能概言。”
南湘复望向身畔男子,不着声的上下打量着:什么样的主子什么样的奴才,丞相府出来的就是丞相府的味道。
长挑身材,严整容貌,一身青色质地上佳的长袍,除了一脸的审慎斟酌之外,再无表情。
“先生这是哪里的话,举手之劳,劳烦二字实在是当不起。”微微一笑,“本是南湘分内之事,还请先生不要这么见外。”
“再次谢过王女。”男子也一笑了之,老狐狸似的笑容,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王女高洁风范古道热心,实乃圣音之福。”
“南湘受之有愧……”
彼此又客套寒暄一番,终于作揖告辞,“时日也不早了,丞相在府中定是心急如焚,我等就此告辞。”
南湘点头算是还礼,那人告辞后亦坐进马车前的轿子里。
列仗在前的侍卫行过威武,一边陪侍的侍从清润养眼,坐在轿子里的老狐狸走过时南湘方才心里松了口气。
而后,马车缓缓行过,国风在马车里窗缓缓掀起窗帘。
依旧是那种固执温润的眼光。安静,执拗,带着贵气的雅致,藏在其中的尽是一片含蓄的眷念温情。
南湘回望过去,她直到此刻方才深刻体味到国风的心思。
他的讥讽和高姿态,他屡次出言不逊,分明是自我保护的外壳。里面潜藏着的,还是一颗痴执的,牵挂在这个王女身上的心思。
这种安静的视线,比他最终刻薄话语更为伤人,像是一捧碎且尖的玻璃,直入人心。
南湘待马车远走,才转身回府。
他们都是很好,很好的人。偏偏所牵挂的那个人早已死去。满心不愿却毫无办法的她,鸠占鹊巢。却无以回报。
这些痴痴念念的目光,这些执着深沉的情感,对她而言却尽是歉疚的负担。
她待国风好,是因为知道他身份特殊,自己有求于他,遂越发尽心思。
她待元生,如同自己不知事的弟弟。她待董曦,则更像自己同性性别的姐妹。她待萦枝,仿佛是自己嘴巴刻薄内心柔软的朋友,她待梅容,则是避之不迭,并非厌恶,只是梅容感情太过浓烈,她无法招架,只能逃避。
她只能逃避,什么兄弟,姊妹,朋友,尽是她逃避的借口。
她知道,这些俊秀男子对她皆是男女之情,满心的牵挂。而她却没有法子。他们对她而言,是陌生的路人,她又如何以同样的感情回应?
原本想着他们能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谁想助力没有找到,自己反倒陷进了一团解不开的乱局中来。
唉。
只向从前悔刻薄,一片伤心画不成(番外)
国风国风,国之风范。
先皇宽容且欣赏的笑着,对着身边众人抚掌赞道,“君子自端方,圣音男儿皆因同此儿一般。”
众人皆诺诺,“……是是。由小可观其大,丞相公子必定不同凡响。”“……男儿当如是……”“得此儿,丞相好福气……”
而他站在璀璨宫殿中,微扬下颌。
众臣应声的声音像是蜂鸣嗡嗡,回响身边不去。他心中虽有怯意,两袖却随风舞动,绝不将内心怯弱显露一二。
国之风范。
他本不是这名字。却因先帝的赞誉,遂改名为,国风。
天子骄子,宇宙寰宇魂魄尽吸附于他。
那时候,母亲是时任丞相。天下学子之师,百官文臣之首,是最受先皇宠信的臣子,父亲是少傅翰林学士之子,书香门第,百年府邸。可以想见的滔天富贵,权倾天下。还好母亲是绝顶聪明之人,知道相权皇权孰为重,从不自恃聪明,妄图只手遮天。
母亲荣宠一生。犹如上好的美玉,只觉光彩照人,不见其疵瑕。
国风倾心崇仰。这是他的母亲啊,他最尊敬的母亲,他毕生的希望莫过于能成为像他母亲一般的人物。
先帝御批:国风国风,国之风范。
大好的时节,花如落英,父亲生下他,正合凤后诞下她。先皇心情大好,御笔一挥朱批示下,从此姻缘定。
都是富贵的人儿,都是固执的傻子,都骄傲如斯。
青梅竹马,瑟瑟年华逝去,还记得先皇亲手将那只凤凰挂在他脖子之上,摸摸他的额头,掌心暖和,笑得温柔怜惜,而目中却藏着几许思索,“入我门,自是我家人。你以后就是她的夫,凡事都是缘分。”
从背后牵出的女孩笑靥上有清浅的水涡,直直望向自己,脖子上同样是只展翅欲飞的凤凰,皇家女子果然同寻常女孩不一般。姿态闲雅,仿佛久居上位之人。
小小年纪一双眸子就如同碧空一般澄澈——她的目光望来,他的心中突然一窒,莫名其妙。
“国风,是吧——”女孩含着笑意拉长了声调。
他有些疑惑,怎能有这么好听的声音?
一出神,没有防备。那女孩居然大胆到居然初次见面就可以利落的牵起自己的手来,秀雅的脸上居然还是一片毫不在意的笑意,“我是碧水南湘,你知道的——”她突然一顿,脸颊飞起两抹晕红,小女儿家羞态毕露,而那时的自己只顾着发楞,忘记伦常礼法,只由着她牵着自己的手笑得满足,“原来你就是我以后的夫啊,我想见你很久了。”
多大的孩子,就这样肆无忌惮的说这些。而那时的自己被娇溺的过了,要强不说,却也由不得别人轻薄自己,哪怕、哪怕是自己未来的妻主,也不行——
记得自己被那一声夫惊得恍悟过来,好像是大力挥开她牵得紧紧的手,昂起头,骄傲回拘,“哪里来的登徒子,竟随意轻薄人!”
这话说得好没道理,他自己脱口而出没等她反应过来,自己早已经羞红了脸。
她好似一盆冷水浇到头上一般的愣了愣,一直站在一旁

![[暮光]菜谱不是辣么容易改的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15/1549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