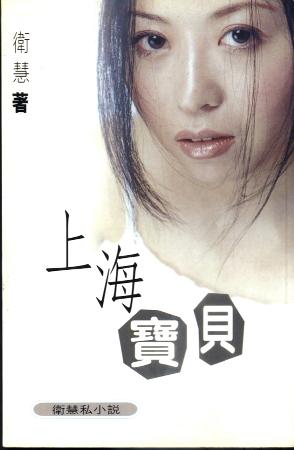谍战上海滩-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通常这种“濒死前的训练”,没有一个学员枪不落地的,个个都吓得魂飞胆裂。
明台是第一个站得笔直、枪不落地、魂魄俱在的人。
明台、于曼丽、王天风都很安静。
机舱里几乎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你们提前毕业了。恭喜你们逃出生天。”王天风说。
机舱里几名随行教员走上去,从明台手上取回手枪。明台没有动,因为动不了。于曼丽也没有哭,因为哭晕过去了。
“每一个站着走出这座特殊军校大门的战士,我都会让他们有一段回味无穷的经历,以至永生难忘。”王天风说。
飞机舱外的云被气流冲散,明台肢体麻木,眼睛望着机舱顶,他在想,所谓永生难忘!所谓死地求生!所谓百炼成钢!所谓天道铁律!所谓英雄豪情仗义万千……明晰清远,其实,就是一句话,四个字,舍得牺牲!
戴笠一直守在电话机旁边等消息。
终于,电话来了。有人很详细地向戴笠汇报了飞机上的一切,几乎是一个字也没有漏掉。戴笠问:“他临刑前,叫大哥了?”
回答:“是。他说,大哥,对不起!”
回话的人没有说全,抑或是故意没有说全。因为明台喊的是:“姐姐、大哥,对不起!”切掉了前面的姐姐,单喊了一声大哥,显然,这个大哥就另有含意了。
传话的人抑或是疏忽,抑或是因为佩服明台,刻意为之,给他一个“好前程”。
果然,戴笠听完这话,脸上绽出笑容来,在他心里,明台口中这一声大哥,非他莫属,舍他其谁!
戴笠发手谕:“毒蝎淋漓血性,忠勇可鉴,特委任毒蝎为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接到命令后,三日内赴任。盼坚忍奋斗,为国建功。”
夜晚,小树林里一片寂静,隐约有铁镐声和树叶的簌簌声,王天风的军靴踏着落叶和泥土,顺着铁镐声走来。
明台正在帮于曼丽挖泥坑埋东西,什么绣鞋、手帕、青布衫,凡沾了过去锦瑟痕迹的物件、首饰,全被二人一镐一镐铲进泥坑里,狠狠地敲打平了。
再没有锦瑟这个人,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了。
于曼丽下了决心,永远与锦瑟决裂,因为锦瑟死了;永远与于老板的情感不再有交集,因为于老板死了;永远都不再记得什么养父,因为养父在她心底也死了!统统去死吧!
王天风依旧觉得明台与于曼丽实在可爱。经过了这么大一场生死洗礼,稚心不改,当真埋了旧痕迹,就能忘旧吗?
但愿能吧,他想。两个孩子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于曼丽看见了王天风,吓得往后一哆嗦。明台发觉有异,回头看到教官,扔下铁镐,小跑过来,立正,敬礼。
“陪我去走走。”王天风说。
“是。”明台跟着王天风向树林幽静处走去,他的手伸在背后,给于曼丽打了一个“休息”的手势。
于曼丽的脸上露出微笑。
明台不回头也能感应到搭档的笑容,于是,他嘴角上扬,面带几分自得。
王天风和明台沿着萧萧落叶铺满的小径,走在寂静的山林里。树梢上不停有水珠滴落,湿气很重,空气里裹着新翻泥土的香,军靴踩在泥上,一踩一个脚印,很新鲜的痕迹。
“明天你就要离开这里了。”王天风口气很淡,但是,明台能从这淡淡的口吻中听出老师的“难舍”之意。
“恨我吗?”王天风问。
“怕您。”明台由衷地说。
王天风失笑道:“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
“记得,在飞机上。老师盛气凌人。”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目中无人。”
明台笑起来,依旧很纯很优雅。
“会想念军校的生活吗?”
“会。”
“军校里的人呢?也会偶尔想起吧?”
“会,除了您。”
“一枪衔恨?”
明台低下头,不作答。
“我在军校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孩子。有的送到了秘密战场,有的送到了郁郁葱葱的荒冢里,有的送到了血火纷飞的战壕。这些孩子有的敦厚,有的清婉,有的温和,有的烈性,都是好人。就算有贪生怕死的,也是好人。他们只是生错了时代,来错了学校,找错了对象,走错了一步。我的心也是肉长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长长地叹了口气,“送走你们,最难熬的就是等待,有的时候,等来你们立功的喜讯,有的时候等来你们失踪的消息,一旦失踪,你们的骨头和血屑,你们的头发和指甲,我都不可能碰到,那个时候,我就会到荒冢去,看看埋在那里的孩子们……”
“为什么不让我们都战死在沙场呢?采取这种极端残忍的方式来考验……我们。是人,谁不贪生呢?”明台说出心里话。
“是啊,我把贪生怕死的孩子送出去,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一个贪生的孩子,会毁掉我们整个行动网;一个贪生的孩子,会图自保出卖组织。你们一旦走出这个门,所有的危险都是真的了。行动中无所依凭,没有后援,精神上人格分裂,备受摧残,时时刻刻置身于险境。死亡,对于你们来说,就变成家常便饭了。稍有不慎,就会自我毁灭。一个优秀的特工,唯一的生存根基,就是不畏死!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谁也别信!甚至,包括自己。”
明台深受感触,同时对王天风制伏自己的一系列手段和谈话感佩折服。他心底油然而生英雄惜英雄之意。
王天风从手腕上取下一块看似很名贵的手表,明台认得,那是一块瑞士表。
“这块表,是我所有家当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礼物。送给你。”王天风说。
“我从不用别人用过的东西,表也不例外。”明台看似很不给老师面子。
王天风无语。半晌,他说:“那就留着做个纪念吧。”
“压箱底,您不介意吗?”
“不介意。”
“好吧,我收下了。”一副勉为其难的口气。
“你没有什么要送给我吗?”王天风知道明台给自己买了一套西服。
“原来有的,可是,我改变主意了。像老师这样清廉如水的人,我就不贿赂了,免得挨军棍。”
“你按我的尺码买的衣服,你能穿吗?”
“能啊。等我老了,发福的时候穿。”
“好。”王天风喜欢明台这股调皮劲,骂人都骂得不拖泥带水,他是在干干脆脆地告诉王天风,你老了,“你记着,下次千万别再落我手里。”算警告,也算玩笑,说完王天风向回头路走去。
“您是专程来跟我告别的吗?”明台在他身后问。
“不,干我们这一行的,不需要告别。”
“将来还会再见面吗?”
“有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老师!”
王天风没有停下脚步。
“我会让您感到骄傲的!”
王天风停住脚步,回眸一看,明台立在树林里,站着笔挺的军姿,清雅、英俊、自信满满,一个帅气中透着坚忍不拔的军礼,让王天风步履轻健,他频频回首,看见明台岿然不动,满身都是月光。
明台和于曼丽走了,走得无声无息,就像树林中的落叶,凭风升降,飘零而去。对于在特殊军校毕业的学生,王天风从不送行,这是他的原则。
他每次都克制住自己内心的难舍,在他看来,他们始终都是要舍得的,牺牲对于他们来说,过于稀松平常。
他每次烧毁一份学生档案,他就会怆然心酸。
此刻,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套包装漂亮的西装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同时,搁在桌上的还有两套军装、军衔及一枚五等云麾勋章,以及一封书信。
王天风展开书信,上面写着很简单的几句话,几乎没有多余的字,干净、简洁。
“老师,我们杀敌去了。军装等物替我们收着,若战死,替我们烧埋了。若胜利回来,我们还要穿着受勋。老师好好活着,正如我们努力死地求生!学生:毒蝎。”
明台第一次把自己的代号写在了书面上。
第一次用这个代号,是给王天风的留书。
王天风感觉内心异常温暖、满足。
这个学生绝非寻常之辈,将来定会在战场上杀敌建功,血溅征袍,尽作一生拼,翻作三江浪。王天风能够感觉到,此刻的明台和于曼丽,声情激楚,胸怀壮烈,在一片荒山野地,一马双骑,披着一身霞光,光彩照人地朗笑而去。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
王天风忽然有一种“被冷落”的滋味。
原来自己才是一片落叶,再也飞不起来,飞不出去,永远飘在荒冢的上空,盘旋,盘旋,直到落地。
明楼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
他住在周佛海的公馆里,安排、调配着“和平大会”的安保事宜。由于天皇特使在香港遇刺,南京新政府除了深表遗憾,同时也加强了对参加“和平大会”新官员的保护措施。随着“和平大会”日程表时间的推进,各方势力的蠢蠢欲动和各方政权的压力已经将明楼死死地遏制住。他连呼吸都会感受到空气里的枪火味,他快累得支撑不住了。
阿诚告诉明楼,明镜打电话到新政府办公厅,要明楼回家一趟。阿诚说:“大小姐这两天咳得厉害,家里还有要紧事要您回去处理。”
这趟电话打得不早不晚,对明楼而言正中下怀,他顺水推舟,就跟周佛海告假一天,周佛海知道他连日操劳,嘱他好好休息一下,凡事切莫太过焦灼,身体第一。
汽车上,明楼心底盘算着怎么回家跟明镜周旋。他每每想到明镜那咄咄逼人的目光,犀利的言语,就很头疼。但是,再头疼,他也要去完成属于自己的工作。而且,他始终相信自己巧舌如簧,有四两拨千斤的能力,他会巧妙自如一次又一次转移阵地。
这一次,他会很主动地出击。因为,他没有多余的时间了。
“粉碎行动”已经开始了,一分一秒自己也耗不起。
“先生,您真的会跟大小姐摊牌吗?”司机阿诚一边开车一边替他担着忧虑。
“不然,怎样?”明楼淡淡一笑,说,“放心。”他顺手拿了一个抱枕压在自己的腰间,让自己在汽车里躺得舒适一点,然后合上眼皮,养精蓄锐。
明公馆很幽静。壁灯昏黄,明镜坐在小客厅翻阅着一份上海画报,西式壁炉里不间断地射着红蓝色的光,很刺目,但是很温暖,有一份属于家的祥和与安静。
明楼从外面走了进来,阿诚跟着他,替明楼拿着皮包和大衣。
“还没到冬至呢,天气倒冷得厉害。”明楼说。
“是啊。”明镜淡淡地回着,“人心也冷得厉害。听说昨天夜里在矿场又枪毙了几十名抗日分子,好像都是76号的杰作。”
明楼站在壁炉前搓了搓手,仿佛有意避开这个尖锐的话题。
“听说姐姐身子不大好,哪里不舒服,找苏大夫来看了吗?”明楼坐下来,很关心地问。
苏大夫是一名俄国籍医生,也是明家请的家庭医生。
明镜不说话,端起茶几上的清茶来喝。
“苏大夫来过了,说大小姐是肺热所致,开了清痰的西药,说先吃几颗试试。”阿诚小心翼翼地替明镜回着明楼的话。
“阿诚,你出去。我有话跟大少爷说。”明镜发话了。
“是。”阿诚应声。
“阿诚,你就在客厅门外守着。任何人不准到小客厅。”明楼吩咐着。
“是。”阿诚依旧应着,用眼角瞟了瞟明镜,明镜不做声,阿诚放心地躬身退下。他随手带上小客厅的门。
客厅里只剩下两姐弟,面对面,壁

![[一触即发][初次]上海探戈--夜未央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7/755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