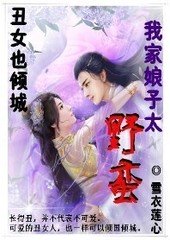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附记:
沙飞枪杀泽津胜,并为之偿命,这是战争的悲剧,中日两个家庭的悲剧。
从小就知道,父亲的死与张致祥有关。1997年3月初次拜访他,当感觉到站在大院门口的老人就是他时,心痛极恨极;然而当面对着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看到他们在整理、手抄晋察冀日报社论时,仇与恨在胸中一点点融化。张夫人伊之告知,80年代末我们把《晋察冀日报》史写好后,拿去给聂帅看,在代笔的前言中,聂帅当面亲自用铅笔加写了几个字“沙飞、洪水、邓拓等同志先后领导过这份报纸的编辑出版工作。”聂帅记着沙飞。后来又几次采访90多岁的张老,他思维敏捷、记忆力很好。作者早已理解、谅解了他,不,应该说是对他们那一代人!但一谈到历史,双方都很冲动,谈一半,他都先离去。张夫人善解人意,两次主动谈起自己的丈夫:他工作有能力,大刀阔斧干事,他要速度、效率、急,不能与他共事,他左的很,不讲情面,不做思想工作,他的位置、暴躁的脾气、简单的工作方法容易伤人,他整人、伤人不知道,他不圆滑,心里有话全吐出来,没坏心,刀子手、豆腐心,智商高、情商低,在社会上不好混,他内心软,我内心刚强,他不记往事,不想将来,只想今天、此时此刻,他经常检查自己。夫人对他知的很深。
2000年8月与住在沈阳的李荒通电话,他感到意外又高兴。他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他说,张致祥是章太炎的大弟子国学大师吴承仕的得意门生,是有名的才子,很正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铁血将军为爱将洒泪(4)
再见到张老,就会平静了。祝愿他健康、长寿!
小时候一直听说父亲的死是朱德签的字,后来才知道是聂荣臻拍的板。事件一发生,聂荣臻立即提出“沙飞精神是否正常”,当张致祥汇报“沙飞在医院检查神经健全”时,他决然“挥泪斩马谡”,同时,铁血将军为爱将洒泪。在沙飞平反过程中,聂荣臻亲自批示:“沙飞已经处刑。当时我不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予以平反,请总政办。”一个既有极强法律意识又重感情的领导人!聂荣臻对父亲有知遇之恩,没有他,父亲只是个优秀的摄影师而已,不可能创办《晋察冀画报》,建立一支摄影队伍,……无法干出这么辉煌的事业。我们全家对聂荣臻有一种特殊的深厚感情。
对朱良才上将,应该说几句。父亲死后,他的老上级中,我们只与朱良才伯伯有联系。我还在上小学时,好几次跟着到北京开会的妈妈去看望他。朱良才是继舒同之后父亲的顶头上司,晋察冀画报是在他直接领导支持下创办的。父亲出事后,徐桐岗开会讲沙飞的历史,朱良才说,这些你别讲;徐桐岗提出沙飞精神不正常,朱良才说沙飞精神正常。但是当副主任张致祥把以政治部名义写好的处决沙飞的报告给主任朱良才签字时,他拒签。没人知道,更没人相信朱良才在有关报告上没签字。1980年代在为沙飞平反的过程中,曾有人,包括梗直的孙毅将军为沙飞的死责怪他,他没有向任何人解释,而且他仍然认为“沙飞精神正常”。但他在家里说,“精神正常也可以死缓!当时不就是一个人一句话嘛!”一个在高层里少有的不随波逐流的人!
父辈们生活在那个年代,他们属于一代有自己原则的共产党人。
txt小说上传分享
执行时不下跪(1)
华北军区政治部张鼎中 1986年、2001年回忆:我当时是保卫部三科科长兼管军法处工作。关于沙飞犯错被判执行我知道一些,事件发生不知道。石家庄华北军大报到华北军区军法处,处长是张致祥,他负责,我是科长。二科管案件预审,领导批了以后,派人把档案送来,我们以军法处名义写判决书、盖章,我们去宣布。当时让一个副科长去,他认识沙飞,他说工作忙,走不开,我和刘德惠是由张致祥派去,执行命令。1950年3月3日我坐大车到石家庄,当晚到华北军大保卫部门。他们把情况介绍了一下,如何布置警戒,安排对沙飞本人做思想工作,让他有准备。我是在3月4日上午,把沙飞叫出来到办公室。我第一次见沙飞,他穿军装、戴帽子、有手拷。当时屋里有十多人,都是军大警卫部队战士。我说你是沙飞同志吗?他说是。我说你犯的错误很严重,要处理,问他有没有准备。他说有。我接着就念判决书,念完后,他什么话也没讲。我说判决后立即执行,他就点点头。当时他就出去,上车去了,我没去。当时拿衣服当枕头,拿了被子去,这是应该的,很好的安排。上午执行完很顺利,我下午回去了。我只是向他宣布,随即执行宣判,至于遗物、埋葬,我都没参加,是军大办的。我们三科就是军法处,五六个人,负责2千多犯人,重大案件都得我亲自审讯,我主审孙殿英、黄维等几十名国民党高级战犯。我这一辈子就执行了沙飞一个老同志,还是错的。如果当时沙飞由我们关押,看出他不正常,我们向上反映,可能会好一些。平反我完全赞同,很高兴。沙飞对革命贡献大,是功臣。
当时人们认为政治部有富贵贫贱之分:保卫部富,组织部贵,宣传部贫,敌工部贱。张致祥这人左得很。
韩彬1987年回忆:3月4日早上8点多吃饭,饭放在院子里,每人拿碗分菜,沙飞吃得慢。袁干事叫他走,他走时挺胸,反复看我,意思叫我没好事,用手比比头。他又回来了,我看到他刮了胡子,就知道他回不来了。他关了两三个月,没有理发,胡子很长,最后宣判前才刮胡子。他穿毛袜、棉鞋,把自己的衣服全套上,裤带还给了他,他系裤带时对我笑,咱们永不再见了,你对我最了解,将来替我说话。小刘问你替他说什么?我说,让我给他老婆孩子说说。那天是我给他穿的鞋,人家不让他穿皮鞋,他非穿,要不就不走。他走时对我哈哈笑,仰头、闭眼,表示回不来。挨着纱窗的湖南人说,今天看来凶多吉少。沙飞走时,他想捅小条过来未捅,他向我招手说再见再见。我说慷慨就义去吧!上午10点他出去,再也没回来了,从此就和我永别了。我只能流泪同情。12点多看守所的警卫小战士回来说,沙飞执行了。我问在哪?他说了地点。怎么执行?很威风!坐小卧车去。一出去就打。沙飞死的情况,小刘告诉我的,他戴脚镣,下车后,有人从头上打,苟部长、小个子四川人小陶、谢连长打的,打完马上擦干净头部血,用毯子包上。小鬼说,军区来个官是参谋长,在大会上宣布处决沙飞,有干部、和平医院代表。听说沙飞走前提出要求:1。刮胡子。2。换上夫人织的毛袜子、毛裤。3。立个碑,搞个记号,将来叫孩子弄回家去。4。执行时不下跪,他是共产党员,不是犯人、敌人,犯了谁的法。我出狱后,去看过几次墓。碑一尺多高,广东开平人,沙飞之墓,一九五零年立。墓在烈士陵园外东南角,最多200米。我问警卫连的,沙飞枪毙时恐惧吗?他说很自然,上车下车很自然,没后悔、没顾虑、没难过、没掉泪。他走后,很多人说,沙飞很有骨头,很有军人气派,不是拽、拉、拖。
军大负责人李钟奇等认为关关就算了,没想到是处决,大家想不通。
张富云:3月4日公审大会我参加了。阴天,灰蒙蒙的,上午在和平医院小操场宣判,沙飞站在临时搭的台上,穿着军衣,不戴胸章,他很帅,很精神,很整洁,整整齐齐的。他脸苍白,但没有害怕,对着台下看东看西,视死如归。大家议论,他什么都不在乎。日本人参加了会,军区来人宣判,大会时间不长,当场宣布极刑,马上拉去执行。葬在烈士陵园东墙外。沙飞死后,日本人佩服,说中国共产党真伟大!
审判过程我不知道,不知道有审判会。当时传说,这么大干部,非要毛主席从苏联回来定,是毛主席批的“杀人偿命,照顾国际影响”。我们都没想到是死刑。
津泽有4个孩子,小的三四岁。沙飞很有才华,他有好几个孩子,小的还很小,一转眼,两家都没爸爸了。我们感到真可怜,挺惋惜的。
姜杰2001年回忆:在医院操场,我在下面坐着,来人宣布,沙飞在台上,一点不害怕,像在病房时一样。大家在下面议论,沙飞是不是有病?杀人犯法,他是知道的。
和平医院司机焦恩1997年、2001年、2002年、2003年回忆:沙飞出事后,华北军大来一个人,我开车把沙飞和他从医院送去军大,当时不知沙飞的名字,他穿棉衣,带着大衣,他下车时对那个人说,拿大衣来,别把我冻着。满不在乎。冬天送去,关了几个月,春天执行。没有开审判会,上午10点多,我开车把沙飞从军法处送到刑场,这次我才知道他叫沙飞。我当时开的是一辆军用中吉普,美国救护车,军大军法处去了两个人,没有其他人,车是两排座,中间可以放担架,他们3人坐着,没说什么。沙飞穿的是新军装,他没有恐惧,没有带手拷,到刑场也没有带。下车后他对执刑的人说,我的事情,希望组织考虑考虑。人家说,你的问题早经过讨论了,毛主席都参加会议了。刑场很近,没2里地,破破烂烂的,挖了一个坑,位置在烈士陵园后面。我没等他们,马上开车走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执行时不下跪(2)
王朝秀(汾阳中学退休教师)1995年、2001年回忆:当时我从华北军大毕业分配到军大保育院,在石家庄市西郊的一座黄楼。1950年3月4日,天阴沉沉、灰蒙蒙的。7时许,我们正在吃早饭,有的在门前蹲着、站着吃。我们看见从围墙外进来一辆马车拉着一口棺材,没上漆,白白的,车拉到传达室后边,好像不愿让别人看见,但我们都看见了,都笑,我们围上去问拉车的老头,干嘛拉棺材?这个50多岁的穿一身农服的老人说要枪毙人。是什么人?听说是个当兵的,打死了个日本大夫。老人语调沉重,很是不平。大家愤慨地议论纷纷。不久听到围墙外汽车打鸣笛,赶车的老人跑到门口,又急匆匆返回,将拉棺木的马车赶了出去,紧跟在那辆军用绿色小吉普后面。我们觉得这车里就是那个人,我们20多人就跟着跑,出了围墙往左,再往上有一片荒地,离黄楼有几百米,车停住了。车门开了,下来3个穿军装的人,还拿出一块绿军毯。两人持步枪,另一人中等身材,脸色白净,似乎还有些红润,少年英俊,神态自然,穿军装,没胸章与帽徽,低着头背着手,没捆绑,步履坚定。开始3人并排向前走,走出二三百米,一人站住了,两个人继续往前走,又走了百米左右,两人也站住了,其中一人向旁边走了几步,回头向站在后面的那个举了举手。后面的人突然打了个立正,并敬了举手礼,我觉得是给要被打死的人敬的礼,然后他就朝那个背着的人举起了枪,那个人也不紧张,也不动。吓得我们有的睹住了耳朵,有的背转了脸,有的用手蒙住眼睛,露着指缝还想看。我瞪着双眼,站在那里,脑中一片空白。枪声响了,他倒下了。惊恐的人群突然清醒了似的,跑向他倒下的地方。后面的军人跟步向前,两个军人将他慢慢地翻过了身,正了正军帽,拉平整个军服,用纱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