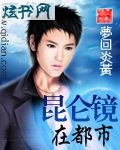拿破仑-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先生,”有人对他说,“不要丧失理智,您是国王的学员,要牢记这一点,您要克制您对科西嘉的感情,科西嘉早已成为法国的一部分了。”
军校学员每个月要参加一次忏悔,指导神父提到他热爱科西嘉的感情。拿破仑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谈科西嘉,作为牧师,你无权在这方面训斥我。”他词锋严厉,往往对答如流,叫人哑口无言。当巴黎大主教德·日涅大人来学校施按手礼时,听到拿破仑的名字很惊讶,说在日历上从来没看到过。年轻人辩解说,一年只有365天,神那么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主教笑了,拿破仑后来在为德·日涅大主教祝寿时还回忆起那难忘的一笑。
紧张的学习生活不能使他忘怀故乡,思亲之情常萦绕心头。因为路途太远、旅费太贵,他已经有五年没有回过科西嘉了。在布里埃纳时,他母亲曾经到军校去看过他。当时莱蒂齐亚看到瘦弱、憔悴的儿子时,不禁潸然泪下:“拿破仑,你还在长身体,千万别太劳累呀!”
当时拿破仑给母亲揩干泪水,回答道:“我不能屈居人下,我们不比别人有钱,但我一定要比别人有志向、有知识!”
成长在逆境的拿破仑,在小小年纪时发愤图强的道理就早已洞晓在心了。特别是父亲夏尔·波拿巴的英年早逝,更是牵扯了拿破仑的心。1785年2月,夏尔因患胃癌故去,终年仅39岁。他在逝前,多次呼唤远在天涯的拿破仑:“儿子,你若回来,一定能驱走病魔的!儿子,你什么时候归来啊?”
父亲去世,家中的顶梁柱坼塌了,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在担起保卫家庭的重任。他感到自己的前途只有靠自己去开创,要想让家中摆脱贫困,要想让自己平步青云,必须凭借自身的努力。这时的拿破仑少年老成,思维已成大人模式。他对炮兵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同时对现实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当时军校作风不正,学生沉湎于饮酒谈女人,疏于学业时,拿破仑曾就这一现象上书给学校当局:“学生生活奢侈,所需费用一般家庭殊难承担。学生一旦沉湎于此,返回故乡无法适应清淡生活,走上疆场则忍受不住战争之煎熬。所以,校方应严禁学生雇佣私人侍从,取消佳宴与华奢服饰,令学生自理生活,食粗劣面包。只有如此,方能造就体格强壮、作战勇敢之军官,令士兵尊重与服从。”
尽管校方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与支持,但对一位15岁少年能有如此独树一帜的真知灼见和嫉恶如仇的胆识却大大折服。到1785年9月,16岁的拿破仑用一年的时间,学完了军校规定的三年必修的课程,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被授予了少尉军衔。这是科西嘉岛第一位从专业军校毕业的正式军官。拿破仑基于对社会和政治的极大兴趣以及家中贫困的原因,他提前毕业了。当时学校鉴定是这样的:“拿破仑·波拿巴,为人勤奋、谨慎,兴趣广泛,博览群书,酷爱抽象科学,擅长数学、地理;沉默寡言,喜欢独处;任性、高傲、自私、善辩,自尊心强,雄心勃勃,求知欲强,有培养前途。”
拿破仑成为皇帝后曾无不由衷地说:“我一生中最骄傲的那一刻,是接受授予少尉军官,因为今天的辉煌正是那一刻的点燃,才使我生命的航船渡入了腾达的航线。” 。。
荒野雄狮(7)
枫丹白露是法国北部的一个美丽的镇子,距巴黎65公里,位于塞纳河的左岸,原是法国王室的狩猎场,在1527年改为国王行宫。这个城镇在诸多建筑师、雕刻家的精心设计下,花园亭台相映成辉,清水小舟点缀其间。不少旅游法国的人都会来到枫丹白露一饱眼福。
拿破仑对这个闻名遐迩的小镇仰慕已久。
他在巴黎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法国南部的瓦朗斯城的途中,没有忘记抽时间一览枫丹白露风景。
他站在一座豪华的建筑物前静思了许久。这里体现着权力与尊严,那一座座富丽华美的亭台则意味着享受与金钱。
拿破仑不知道炮团的道路将会把他带往何处,但他对这里富饶的一切却在此时此刻产生了欲归己有的豪迈情怀。
他不知道这一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但他凝视着脚下被踩踏倒伏的草坪,竟由衷地露出了少见的微笑。
1785年11月3日,瓦朗斯城拉费尔炮团来了一位个子瘦小、脑袋硕大、两腿粗壮、黄色皮肤的青年军官。这就是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来到这里的最初三个月,他不得不站岗放哨,执行一些列兵勤务,直到1786年1月他才正式就任,下团任职。
当时年俸1120法郎,而且除了薪饷和津贴之外再无其他收入。拿破仑没有想到成为一名法国军官后,依然不能远离贫穷,而且这里纪律涣散,风气不正,军官们大多嗜酒、找女人,距拿破仑想像的一展宏图的氛围相去甚远。他在失望之余,不由得想起了英国史学家卡赖尔的话:“学会服从命令,是学习统治的基本的艺术。”他又回到了拼命学习、与书相伍的生活。在这里的日子,他系统地扎实了征服别人、统治世界的军事素质。
到达瓦朗斯后,他住在一位姓布的老小姐家里。她开了一间咖啡馆,有几间房出租。开头三个月,他跟同学们一样,必须从最低层开始逐级服役。
他混杂在队伍中,开始当炮手,接着当下士,而后当中士;他站岗放哨,担任周值星官。因此他熟悉部队生活,为他后来善于向法国士兵讲话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他第一次穿上了军装,翻领蓝上装,蓝色的军裤,菱形的小肩章是丝绸织成的,金光灿灿。拿破仑感到这些漫长而又艰苦的岁月没有白熬,总算得到了报偿。
早餐是一块夹馅面包,一杯清水;但晚餐在“三鸽”旅店用饭。店是热尼家开的,承办中尉军官们的包饭。布老小姐殷勤待客,为拿破仑熨衬衫,缝袖口,添花边。
他的上司待他甚好,尤其是他的中校于尔图比子爵和上尉马松·德·奥蒂姆。
“服役像在家里一样。”他后来回忆说,“上司们对下级亲如手足,是世界上最英勇、最称职的军官,纯净得如烈火炼出来的黄金,只可惜年纪太大,因为和平时间很长。讽刺挖苦是当时的风尚,年轻的军官们笑话他们,实际上是对他们表示亲密。”
拿破仑同他的同学们来往颇为密切,他特别喜欢去看望德·马齐斯和其他早已成为炮兵团上尉的兄弟。他出席过在“法国盾”福尔之家举办的军团聚餐会,也参加过为城市各界人士举办的节日联欢会。他到圣·巴尔布跳过舞。他喜欢远足,爬上“鸽子岩”,攀登夏尔特罗兹·德·布旺特山。
“我喜欢登高远望,地平线也在我之下。”他说。
他还同瓦朗斯社会名流建立了关系。由于马比夫一家致信给圣·吕夫修道院院长德·塔尔迪冯大人,作了引荐,拿破仑在当地的名门望族家里受到热情的接待。他到过德·科隆比埃夫人家——巴索的农庄去做客。到农庄有3法里路,他常沿着马路步行,边走过哼着小调。德·科隆比埃夫人是里昂人,很有教养,年纪比他大得多,却“迷恋上了他”。她希望他出来娱乐娱乐,生活不要那么苛刻。他回答她说:“我母亲负担太重了,我不能因我的开销增加她的负担,特别是在我的同学们心血来潮大肆挥霍、逼着我花钱的时候。”尊贵的夫人预言他官运亨通,前途光明。波拿巴向她表示要写一部《科西嘉历史》,她便将他推荐给雷纳尔教士。
德·科隆比埃夫人的女儿卡罗利娜既年轻又聪明。波拿巴中尉向她献过点殷勤。有几天早上,他们在树下摘樱桃吃,互相打闹,向对方的头面扔樱桃核。但不久,她同一位旧军官布雷结了婚,随他到里昂去了。
拿破仑对德·洛布里小姐也表示过一点爱慕之情。但她更喜欢蒙塔里韦表哥,拿破仑在帝国昌盛时期又见到过这对夫妇。
拿破仑这个双手细嫩、橄榄肤色的小科西嘉人,此时还是一位童男。在春情萌发时期的难为情中,这些姑娘曾使他激动。但如果他真的同她们甜言蜜语的话,他也没那么多闲暇的时间。何况她们并不对他认真看待,常常笑话他笨手笨脚,言过于实。他的消遣都用在了学习上。他感到在布里埃纳受到的教育还很浮浅,应当深化、完善所学的知识。
他的房间空荡荡的,只有又粗又笨的胡桃木家具,透过地板可以听到楼下咖啡室里饮者的欢笑声和打台球的吵闹声,然而他却埋头苦读,乐在其中。他的收入太少,月薪只有73镑,必须节省着花钱。倘若只剩下一个埃居,他便到奥雷尔书商家去买书或租书。正当他的同学们与房东的小姐们在草地上吃中饭,一个个乐不可支的时候,他却孜孜不倦地读着、记着、写着,如痴如狂,废寝忘食。他全力以赴攻读卢梭的著作,如饥似渴,狼吞虎咽。伏尔泰干巴巴的说教、闪烁其词的文风令他扫兴。
可是,卢梭这个日内瓦人,用他那精心策划的不安,用他那爱的呐喊,用他那对道德的歌颂,用他那温和、平等、自由的社会梦想,激荡着这个时代。卢梭,人们不理解他,讨厌他,可拿破仑理解他,热爱他,要步他的后尘。
荒野雄狮(8)
卢梭不是早就以门托耳自居,关心着科西嘉的命运,考虑为它颁布法律,声明自己便是科西嘉的捍卫者和好朋友吗?拿破仑觉得,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
拿破仑属于另一种灵魂,更严厉,更有条理,更精明能干。他根本就不是哲学家,也永远当不了哲学家。他还太年轻,他的思想还可能想入非非,在云雾中飘荡,但他很快会回到现实中来。
卢梭就这样牢牢地统治着拿破仑这位勤奋的学徒。波拿巴贪婪地啃着《社会契约论》、《爱弥尔》、《新爱洛绮丝》和《忏悔录》。他分析、模仿卢梭漂亮的词藻。为写他的《科西嘉历史》,他飞快地做着笔记:
“法国人啊,你们把我们心爱的洗劫一空还不满足,你们还*了我们的风气。”
“科西嘉人,过去能依照法律的所有条款来动摇热那亚人的统治,今天照样有办法动摇法国人的统治。”
他写了一篇关于自杀的激烈的言论,其文笔简直是从让·雅克那里继承下来的:“在芸芸众生之中,我却总是孤苦伶仃,我回来正是为了自己做梦,为了让自己投身到风潮而来的愁云惨雾中去。今天,这愁云惨雾已转向何方?已经转向死亡……”
“枉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何用?既然我反正得死,不如一死了之?”
当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发现眼前的世界被堵死时,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风华正茂的青年有时会悲观厌世!生命若不能立即为他带来权势和名望,这生命未免太漫长了。他的满心惆怅变成白纸黑字,自杀的念头也烟消云散,他又开始相信自己,又开始希望了。他的思想并不总是这样紧张。他深深爱上了他的炮兵职业,他专心致志于他的功课,一丝不苟地进行军官课目锻炼。
然而,他心里老惦念着他的家、他的故乡。他耐心地期待重返故里与亲人欢聚的时机。时机终于等到了,他所在的部队奉命到里昂平息一次工人骚乱。
在那里度过了半个月后,他获准半年的探亲假。他立即动身,取道埃克斯,到神学院去,拥抱了他的舅父费什和弟弟吕西安,此时的吕西安已离开布里埃纳,正为获取神父职位而用功。1786年9月15日,他终于踏上了阿雅克修的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