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巴黎-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是这位老师,在学期末组织了一个小party,在学校院子里面摆上桌子,铺了桌布,让不同国家的同学们各带一道自己国家的特色菜式过来。有一位中国同学带来一盘皮蛋,绿油油的搁在那里。同学们咨询她她也说不清,结果给人一种一堆蛋在化学试剂里面放了N天,全部霉掉长毛的感觉,闻上去也怪怪的。我还不明就里,看到别的盘子都渐渐空下去,还举着那盘皮蛋使劲推销:“吃呀,大家吃呀!”
很多时候,真正使我焦虑的,倒不是老师或者外国同学,而正是我的一些同胞。前面说过,有不少课程是和MBA一起选的。MBA专业的中国学生颇有几位,大部分也算得上成功人士,然而总体而言年龄偏大,英语很差。人在不能灵活运用某种语言工具的时候,就会给人一种比较呆的错觉——我在日常生活中和法国人打交道,一直比较呆。因此,在某些课上老师同学满嘴跑马的时候,我非常希望能够和同胞们同仇敌忾,可是他们全都呆呆坐着,缄口无言。我单枪匹马,没什么说服力。事后我埋怨道:“刚才有人胡说八道,你们怎么都没反应?”他们大惊失色:“谁说的?说什么了?我怎么没听见?”我郁闷。
我们这个系虽然针尖一样小,但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偶尔也组织一些活动,以吃喝为主。从左至右:奥地利的Margot,埃及的Suey,我,比利时的Marie,法属马提尼克的Aline,百慕大的Julie。
然而最郁闷的,还不是英语差,更在于个别人姿态不大方,上课像合了壳的蚌,考试时当着所有外国同学的面打小抄,这样还是怕不及格,要想方设法巴结一下老师。公众演讲课的老师每天都去健身房,课间吃两个橘子补充维生素,练出了很厉害的肌肉。有一位3来岁的中国女生,想过去称赞一下老师的身材不错,只听她用蹩脚英文大声说:“Sir; you have a nice body!”我们的老师也不是吃素的,竟然从上到下地红了脸。我用笔记本遮住面孔,心说:“我不认识她,我不认识她……”过了好久才抬头,结果就看见Vanessa在那里冲我挤眉弄眼。
后来就出了一件事。“国际商务谈判”是那种实战性质很强的课,好几个中国学生都选了它。没上几节课,班里的外国学生集体到系主任那里告状,说是中国学生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学习。原来这几个中国学生自己编成了一组,轮上和他们当对家,谈判就完全进行不起来。系主任费了很大的劲调停。我没有选这门课,但是听说后觉得很伤心,尤其因为Vanessa和Marie也选了这门课,告状的想必也有她们了。没想到她俩平日和我嘻嘻哈哈很亲热的样子,背地里也是不喜欢中国学生的,真是有些两面派。
后来又有一门课,分组做presentation。有位同学法瑞尔因为看病去了,回来的时候组已经分完,只剩下全是中国同学的那个小组还空一个位置。她一看这情形,竟然呜呜地哭起来,并且当天晚上还给她的几个好朋友发了邮件,说她们“在关键时刻扔下她不管,迫使她加入一个肯定得不了好分数的小组”……
得知这些,我仰天长叹。怎么办呢?我又没有法力使中国学生的英语一夜之间突飞猛进,那么,只有自己努力学好。然而作为一名munication的学生,总是在和语言打交道,我虽然没有哪一门课是特别差的,但是在一群英语是母语或是几乎像母语一般的同学中间,还是很难做到鹤立鸡群。
◇BOOK。◇欢◇迎访◇问◇
第44节:二十岁的巴黎(44)
可是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学期,系里专为我们这届四个MBC开设了“会计与经济学基础”一课。这已经是把MBA里名目繁多的会计学和经济学做了很大的压缩,就是考虑到MBC学生数学不是强项,只要大家入门即可。我在巴黎高科的这帮朋友,都是理科大牛,就是数学15分的卷子考个14来分说是马失前蹄,玩牌的时候你手里有什么牌他们算得比你还要清楚的那一种。我平日里已经有严重的自卑感,不料到了这门课上,我多年的屈辱一扫而空,简直是容光焕发起来。
这所谓的“会计与经济”,在我看来,不过是些拐了两道弯的数学游戏罢了。可是那几位可怜的美女们,从上一届MBC耸人听闻的介绍开始,就紧张得不得了。Aline和Marie也就罢了,可是Vanessa堂堂多伦多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竟然也紧张到这个地步,真是匪夷所思。
真正上课的时候,她们可怜地缩在教室一角,手里捧着个计算器,一脸茫然。教授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有五个儿子,本来耐性已经好得出奇,竟然也有被折磨得发脾气的时候。他在台上大讲特讲asset、liability、credit、debit……的时候,那三个美丽的脑袋已经快要爆裂。只见Marie很可怜地咽了一口水,有气无力地说:“老师,能不能休息五分钟?我头一阵阵的疼。”Aline更加神奇,整个被支晕了,还很勤恳地提问:“老师,那上一个式子的加3,到了下一个式子,怎么变成减3了呢?”Vanessa很聪明地告诉她:“从等号右边移到左边了呀!”教授翻了两轮白眼,关切地问:“Aline你没事吧?”
我大大咧咧坐在第一排,肚子都快笑疼了,然后故意把题目做得飞快。小测验一个半小时的卷子5分钟答完,交卷子时看见Aline慌得把计算器掉到地上,草稿纸堆了一桌子。后来,某一堂课之前,我们四个并排坐在教室门口的台阶上等教授。Aline忧郁地说:“如果老师生病不来就好了。”Marie说:“凡凡是不怕这门课的。唉,你怎么学得这么好呢?”我轻描淡写地说:“中国学生英文差点,数学还行。”
我们这个系虽然针尖一样小,但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偶尔也组织一些活动,以吃喝为主。中国学生是从来不参加的。一开始,我也不爱参加,尤其是头一学期在费塞特家的时候根本没空参加,可是渐渐地,就发现他们组织活动时设置的默认值等于“除中国学生外所有人”,邀请函从来不发到中国学生的信箱去。课间他们热烈讨论头天晚上party的时候,中国学生仍旧黑咕隆咚坐成一团,像牛一样在纸上写写算算。
与老师也是一样。课间他们和老师一块儿在院子里抽烟闲聊,课后一起去喝一瓶小酒。他们总是和系主任吵架,但是系主任还是更加喜欢他们。我们中国学生尊师重道,整天绵羊一样,在老师眼中却是面目模糊的一群。
于是我勉强自己参加他们的活动。正好这个时候,MIM国际市场专业又来了一位中国女生石玮,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和我一届。石玮十分大方,个头娇小但是能量巨大,一来就报名系里的服务小组,当上了小干部,整天管这管那的,很受大家欢迎。我和她很谈得来,并且有了她壮胆,也就能够经常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和大伙儿一起出去玩儿了。次数一多,发现中国外国的学生还不都一样,坐下来也就是八卦,A老师如何如何,B同学和C同学如何如何。一次从一家满是咖喱味儿的印度馆子出来,Sarah紧紧扯住我的胳膊,黑夜里双眼贼亮,意犹未尽地说:“你还知道什么八卦,快说,快说!”八卦这个词她用的是gossip,这个词我认识了十来年,从没觉得它这么传神过,而且这以后一提起就能想起Sarah那神神叨叨的模样来。后来Sarah比我们先毕业了,毕业后还写信来问学校里面有没有新的gossip。
再说石玮,有一回我们去巴黎现代化新区拉德方斯,为有“新凯旋门”之称的大拱门拍照,那时正逢国内非典闹得很厉害,假期有回国的中国同学回来后都要先隔离一周。上了地铁,突然有三四个黑人少年冲我们指手画脚,“SARS,SARS”的混喊一气,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我一看就气了,什么跟什么啊,正在那儿搜肠刮肚地想发表一些言论,看见石玮倒是面不改色,她镇定地冲着那帮人说:“SIDA,SIDA(艾滋病)。”他们愣了一下,灰溜溜地走了。
§虹§桥§书§吧§。
第45节:二十岁的巴黎(45)
我和同学们外出“不务正业”的时候,若是从前,我大约会感到一些良心上的不安。而在巴黎,我却恰恰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当我在那里天花乱坠地忽悠中国文化的时候,我的外国同学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课堂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生活更在于体会。中国学生不爱参加活动,部分是因为钱,可也不尽然。我总是记得美国的Sharam如何跷着二郎腿,大大咧咧地讲述他在加油站辛苦工作的历程,就是为了挣点钱享受巴黎,多两欧元就可以多喝一瓶啤酒。而我们有些中国同学,哪怕家里是开油田的,也不愿意出去撒点野,且理由众多。然而那些理由是不堪一击的:“英语不好”、“没有共同话题”……正因为这样才更要去说英语啊,才更要去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啊。
如果来一趟法国,只为了一张文凭,电影院没去过,咖啡没喝过,奶酪没吃过,一年完了老师同学名字跟脸对不上,英文依旧很糟,法语一个字不会,那是干什么来了?还不如在人大天桥下面找人拿个萝卜盖个章就完了。那样倒也简单,我这本巴黎书儿只写校园纪事一二三四就行,且每一篇里面都是“今日某点至某点上某课,看某书某页至某页。又:中国城购白菜一棵”。
有一次,在一家闹哄哄的小酒吧,大约是多喝了两口酒,我向Vanessa提起那一次“国际谈判”的风波,并且问她是不是对中国学生有偏见。Vanessa吃惊地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们绝对不是针对某个国家的。如果你交了很多的学费,却和一群七八岁的小孩子一起上课,你会不会觉得很亏?”我想了想,当然亏了,可是又说:“你就是说英语的,中国人当然说不了你那么好。”Vanessa说:“既然到外国来用英文上课,就应该有这个准备。尤其是这种口头表达的、分组的课,连大致表达思想的水平都没有,我很怀疑他们自己能学到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凡凡你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啊!加拿大华人很多,多伦多大学里中国学生的比例特别高,我绝对不会有什么偏见。‘跨文化交流’课上不是总在说stereotype这个词吗?对于某个国家,人们总有先入为主的笼统概念;可是与那个国家的人实际接触之后,笼统概念就不再起作用了,完全是因人而异。你和石玮等等,都是好样儿的,咱们难道不是好朋友吗?”
听了她的解释,我不知是舒了一口气还是更加难过。Stereotype这个词,原指印刷上用的铅版,一旦上了机器,印出来的铅字就板上钉钉了,引申为人们脑海中的固有观念,不一定是确切的。然而,一个stereotype毕竟是由成千上万的个人印象长期塑造起来的,Vanessa并没有完全明白,我绝不是仅仅关心我的个人形象。我希望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如同李白的诗篇,张扬个性,魅力超群。我希望除了我们古老灿烂的文化之外,还有更多可以忽悠的东西。如果在做presentation的时候,谁往台上一站,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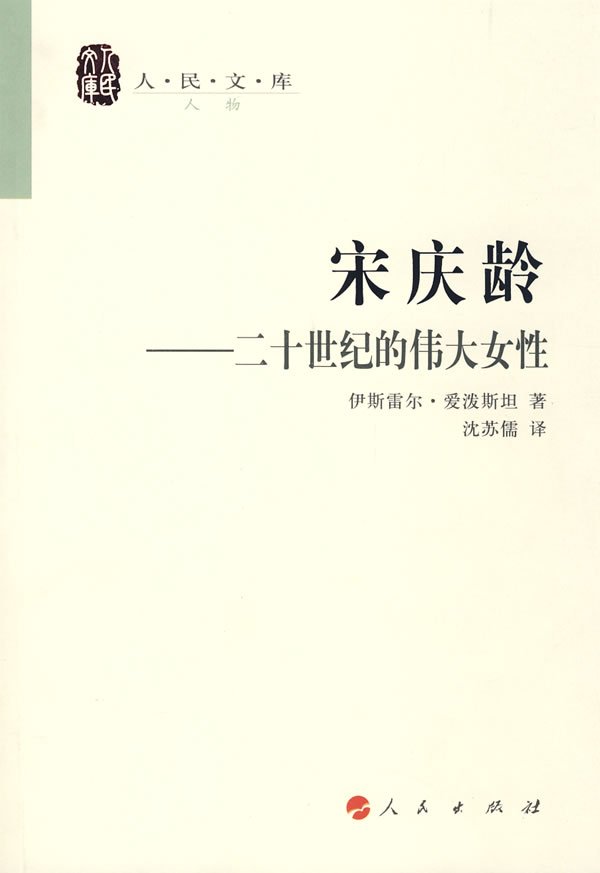

![[巴黎圣母院]教皇之路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2/204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