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巴黎-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邹滨逊漂流记(自序)
鲁滨逊乘大船,漂落荒岛;邹滨逊乘大鸟,漂落巴黎——把巴黎比荒岛,会不会伤害法国人的感情呢?可是话说回来,他们自己在法语里,可就是把包括远近郊的大巴黎地区称呼为法兰西岛的!
前两天下载了琼瑶阿姨最新偶像剧的第一集来看,哗,真是越看眼睛越大:女主角在戴高乐机场下飞机,神采奕奕,通身不带一丝褶;贴心的准姐夫接机兼作导游,指着塞纳河畔的古监狱大言不惭地说:“看,那是奥赛美术馆!”入住豪华酒店后客房经理满脸堆笑送上吃喝玩乐全包卡;用中文大大咧咧问“这东西多少钱”,店师傅立刻用法语回答“一欧元”……最神的是溜出酒店逛巴黎,马上有同胞帅叔从天而降全程陪同——这帅叔可厉害了,不仅让身材火爆的法国妞儿追出半条街狂嚷着要嫁他,还赤手空拳打退了N个前来滋事的彪悍的黑人白人小伙子——于是,女主角与帅叔得以在圣母院前携手嬉戏,惊起一群肥鸽……
这等好事,我为啥零星半点也未遇上?不过无需肉酸肉痛,我在法国的朋友也都没有——能遇上的,大约只有琼瑶女主角。七昏八素到达巴黎的第一天,我与女主角的唯一相似之处,是我们的法语水平。那时我对法语的全部认知就是一句“赛拉味”,此外连法语究竟是不是也有26个字母,都不能够确定——可惜,“赛拉味”只能让我冒充哲学家,却换不来半块面包。
那时的巴黎对我而言是什么呢?就是个危机四伏、隔膜深重的荒岛:荒岛可以风景如画,也可以生机盎然,只不过,四周熙熙攘攘,没有一个是同类,没有一个说着自己的语言,达成任何一个微小的愿望,都难于上青天……大家可以回想《猿人星球》,体味身陷群猿的感觉。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记得在巴黎的第一周,整整七天,坐在那家以夏威夷语Hello为名的小小青年旅馆猥琐的铺位上,我每天琢磨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要不要抓紧时间买一张单程机票回家去?而最后为什么没有买,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把我的旅行支票兑换成钱,并且不知道到哪里买、怎么买。
那第一个星期长如一个世纪,也正是从那个星期起,我开始了数年先以生存、后以发展为目标的摸索加垦荒。如同鲁滨逊在岛上捕羊生火、挖洞搭帐篷、用树叶做衣服,在这里衣食住行也没有一样不用操心。单说一个“食”——我还记得在第一任房东家百思不解地注视着锅里的胡萝卜块,不明白它们为什么不肯软下来,直到房东跳进厨房大喊“要加水!要加水!”还记得在费塞特家,已经放好锅倒上油,因为电炉实在慢热,见缝插针上了趟厕所,回来后菜一下锅,飞溅的油星在我左胳膊上留下的三五点印记,这么多年后都没有消去。当然也记得在超市面对那琳琅满目的瓶瓶罐罐猜哑谜,在面包店为了一块三明治和店师傅打哑语,还有聚会时从一大盘黄润可爱的圆形“蛋糕”中抢出一块扇形,大口咬下去才知道是奶酪而且是羊奶酪,一点不夸张的,我立刻热泪盈眶向洗手间奔去……
这还不是最糟的。在岛上鲁滨逊渴望有人,哪怕只有一个人能从海盗船上逃到他那里去,让他能有个同类的人说说话,而我在结识知己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之前,在把四周的猿人变成可交流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之前,也经过漫长的孤独的日子——周末无比的好天气,却只是关在房间里,看天看天再看天;偶尔鼓足勇气一个人出门,走路都抖抖索索的,像是怕踩了自己的影子……
写到这儿,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竟然在这岛上存活了这么多年,并且还活得挺滋润。当然我绝不是说我已经修炼得如鱼得水了,岛上生活,用张爱玲的话说,依旧时不时爬点虱子跳蚤,况且我所谓的摸索、垦荒,在高人眼里,都只是鸡毛蒜皮、提不上筷子……我只不过回头去看初来乍到的自己,“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自嘲一下,感慨一下,然后自己拍自己肩膀一下。
又想起海明威大叔那句老掉牙的话,“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哪里,她都将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个不固定的圣节。”(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have lived in Paris as a young man; then wherever you go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it stays with you; for Paris is a moveable feast。)——注意,他说的是生活过,不是游览过,而我把二十打头的年月的大部分扔在这里,所做的也仅仅是生活而已。亲手摸索垦植过的岛才会成为自己的岛,亲手摸索垦植过的生活才会成为自己的生活——现在,巴黎对我而言是一种立体的过程,不再是明信片上的平面景点、贴上自己的大头就是“到此一游”的照片。
→虹→桥→书→吧→。
第2节:二十岁的巴黎(2)
五年前问起巴黎,我也会说铁塔、凯旋门、圣母院;五年后我想说的有些不同,当然我也会说铁塔,但是它怎么会是“左看也是塔,右看也是塔,中间看也是塔”呢?它当然不仅是塔,还是我初到巴黎扫到出租车上的那道光柱,是我在阁楼厕所里看到的那个尖角,是我溜冰摔了一百个跟头的见证人,是我在电影节看露天电影的背景,是我和五花八门的朋友们把酒畅谈的那块草坪……
所以说,这本书不是一本“旅游手册”的书,也不是一本“哈佛女孩”的书,而是一本“荒岛余生”的书。有我的故事、朋友的故事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故事,它们都是在巴黎的岛上,确确实实发生过的。
地球这个东西,说穿了也就是个大水球,在我们出生的、熟悉的这个岛之外,还漂满了其它陌生的岛屿。我虽然没有意愿变成异乡人,然而仅仅蜷缩在自己的岛上,看我看惯了的人做我做惯了的事,早已不是我的风格。海明威说得对,以后我无论去到哪里,巴黎都将与我同在,然而同在的理由,却与海明威有所不同,不在于吃了多少好馆子听了多少好音乐甚至看了多少美景,而在于我从不认识它有点害怕它到很辛苦的认识它适应它,在于它曾经当过我的小岛留有我的印记——地球是我们的地球,所有的岛屿是我们地球人的岛屿,今后无论被扔到非洲岛还是南极岛,没有人有理由再害怕。
最后,要衷心感谢所有在书中映射下痕迹的朋友,我爱你们,你们是这岛上一切的精彩。
Aloha Hostel
Aloha Hostel
22年11月1日,飞机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整整飞行了12个小时,我靠窗的座位一直笼罩在炫目的阳光之中,就这样由东向西,丢失了一个黑夜。
向下望去,先是蒙古高原层层叠叠苍苍郁郁的山,接着山顶出现了皑皑白雪,渐渐过渡到大雪无痕的西伯利亚,再往后才是缕缕轻云下的欧洲原野。飞机安全降落后,机上的法国乘客都鼓掌欢呼起来——巴黎到了。我却实在没有那样的好心情,因为我不仅晕机,而且困倦得走着路都要睡着。办完各种入关入境手续,已是巴黎时间下午5点(北京时间半夜点)。在从机场到旅馆的出租车上,我当机立断向司机索要了一个大塑料袋,随即搜肠刮肚地大吐特吐起来。司机指着埃菲尔铁塔让我看,我有气无力地扭了扭头,只见一道光柱扫将过来,心想,谢天谢地,旅馆就在铁塔附近,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我住的小旅馆叫Aloha Hostel,类似于世界连锁的青年旅馆(Youth Hostel),通用英语。到巴黎自助旅游的学生们大多住在这种小旅馆里,因为它设备虽简陋,价格却便宜。说是便宜,我住的四床位的房间也要17欧元一晚。简陋倒是真的:每层公用的淋浴非得用手按着钮才有水,洗澡时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来。我住的那屋是依着屋顶辟出来的,天花板是个坡,没刷漆的木头横梁裸露在外,所有住户都在梁上撞头两次以上才长记性。两张双层床,各放一个大床垫、一床脏毯子,枕头床单一概没有。早餐是包括在房费里的,每天都一样,比石头还硬的大棒面包的一节,果酱、黄油自抹,橙汁、咖啡、茶、热巧克力自选。那面包真是难以下咽,就像打落了牙往肚里吞。
可是啊,每当回忆起初到巴黎的情景,我总觉得住在Aloha Hostel的那一周是无比快乐的。如果不是每天往外掏17欧元的感觉太过滴血,我倒宁愿总是那么手忙脚乱地洗澡、用胳膊当枕头、吃比牙还硬的面包,因为在这里,我第一次有了当国际人的感觉——虽然我这个国际人当得终究不是很彻底,当我的下铺换成牙买加黑哥们儿的时候,我还是颇为紧张的,把行李查了又查,睡觉时脏毯子裹得紧紧的。
我们屋数我住的时间最长,其余三名室友一直在换,先后有西班牙姑娘、韩国的尹嵘姝、两个哥伦比亚MM、一对荷兰与泰国的混合couple、美国的Angela、法国大帅、牙买加黑哥们儿。这种旅馆俗称MIX,就是男女混住的意思。一周下来,我已练就了在窗帘后五秒钟换好裤子的硬功夫。
。§虹§桥书§吧§
第3节:二十岁的巴黎(3)
其中,尹嵘姝在伦敦念书,周末来巴黎玩。她第一天在机场将就睡了三个小时,第二天找到这家小旅馆,进门时见到我如见亲人。她自带了粮食,我俩就在旅馆的厨房里炮制了一顿韩国餐:米饭、紫菜、金枪鱼罐头,还有海里的不知什么植物炖的汤。嵘姝的盛情完全可以弥补韩国菜的无味。我一边学嵘姝的样子用紫菜包米饭,一边和她聊起了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和世界杯上韩国队的“杰出”表现。
大帅就是很帅的帅哥的意思。头两天大帅早出晚归,我未能一睹芳容,第三天和他打了个照面,心里突的一下,心说这肯定是法国人,否则不会长得这么艺术。早上大帅套件破毛衣,卷着裤腿,赤着脚,睡眼惺忪地洗漱时,我觉得他简直是想象中的法国青年的标本。大帅是学美术的,每年总要从外省来巴黎两三次,呼吸呼吸卢浮宫的新鲜空气。
当我问Angela是哪儿人时,她张嘴就说San Diego,见我稍有茫然,便善解人意地补充那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城市”。后来我发现在这样国际化的小旅馆里,还真有很多美国人张嘴就是某州某市来的,仿佛对方就应该知道那是美国的地方一样。Angela说她这是第一次出国旅游,想见识新风景,结识新朋友。她比较害羞,并不像别的美国青年一样满嘴跑马,很快和人打成一片,而是每天晚上在灯下长篇大论地写日记。
每天早餐时分,风格各异的音乐轻流慢淌,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围桌而坐,笑声朗朗,高谈阔论,无拘无束,酣畅淋漓。一次,我和另外四位分别来自巴基斯坦、巴西和加拿大的朋友在厨房里炒鸡蛋,还开了一瓶法国红葡萄酒。巴基斯坦朋友谈起了他周游四海的经历,说他上个星期就在伊拉克,众人皆叹,随后便七嘴八舌地谈论起小布什、布莱尔之类的话题来。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全然忘记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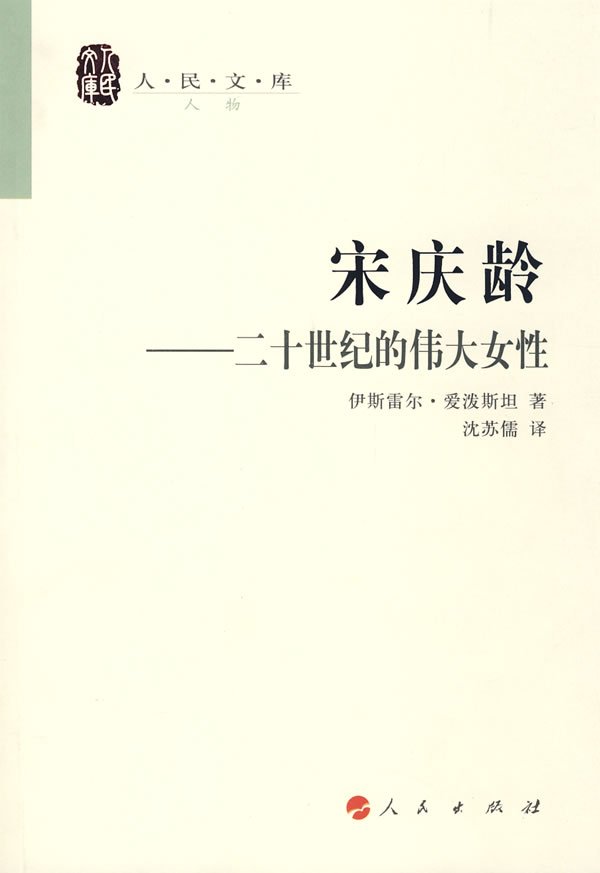

![[巴黎圣母院]教皇之路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2/204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