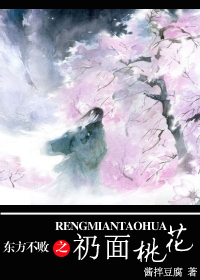兰亭笺纸桃花色-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公主——”王练之紧追几步,突然收住脚,眼里有难以掩饰的眷恋。
纷纷雪屑好似散粉碎玉碾转成灰,在风中散扬开来,簌簌飘落而飞。这一刻连天地都已被封冻凝固。君羽握紧缰绳,侧头看了看王练之,又与他身后的人相视片刻,闪烁的双眸顷刻潮湿。
暗淡的流云急速后退,四周响起千军万马的嘶鸣。雪地里的三个人静静站着,从不同角度凝望着马上的女子,面上的表情阴晴不定,却是一样的爱恨纠葛。
她闭上眼,仓促地背转身,朝着他们都无法看见的方向,抬袖擦干脸上的痕迹。狂风吹乱发丝,在空中搅成纠缠的弧线,她再不犹豫,双腿夹紧马腹,迎空抽了记响鞭,对身后陈列的大军高喊:“回宫!”
众将齐声应喏。先是掉转马头离开,断后的步兵急忙尾随上,她的身影夹杂在人潮之中,像是乌沉沉的闷雷滚滚北去。天光顺着大军远离缓缓亮开,视野蓦然空旷起来。
桓玄狠狠地回头,仰手一抛,长剑扎进雪地里,兀自泛着冷蓝的寒光。他径直走过去,在谢混身边停了一下,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听着,今日之辱我会永远记住,他日加倍奉还,君羽是我的女人,你最好不要有非分之想,否则我让你痛苦一生一世!”
谢混转过头,静视着他眼中异忽寻常的幽妒火光,忽而展颜一笑,唇角牵起优雅的弧度:“好,咱们拭目以待。”
巫山不是云(下)
君羽回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愈安宫请罪。
从偏殿角门进去,绕过一幅丈二碧玉插屏,便到了愈安宫的暖阁。此时天色昏沉,阁里掌着八角黄绢灯,塌褥靠垫也用了一色明黄,抬眼望去金碧辉煌。外面风雪交加,这寝殿里却温暖如昼,四壁悬着通天彻地的纱幔,薄烟从锁衔金兽连环熏炉里袅袅扩散开来,淡雅熏香氤氲满室。
太皇太后端坐在东面矮塌上,黄缎锦袍上绣满鸾凤纹样,手里捻着串玛瑙串珠。王神爱与胡贵嫔各坐在塌的两边,见她进来,齐齐抬起头。
这种阵势前,君羽难免有点怯场,她屏息走过去,跪下行了一礼。
太皇太后闭着眼,神态静如古佛:“你去哪了?”
没赦平身,君羽也不敢妄动,她考虑了良久,如实答道:“回太后,儿臣去了梅花山。”
“梅花山?”太皇太后皱眉,睁开眼问,“那里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让一个堂堂的公主不顾礼法,在外头抛头露面,竟敢彻夜不归。是不是哀家不下旨让桓玄去,你还不打算回来?今儿不给哀家个说法,你就休想出这宫门半步!”
“我……”君羽咬了咬下唇,不知道该怎么说。
“说!干什么去了?”
“太后息怒。”王神爱过来解围,“臣妾听说梅花山上近日有个道坛,名曰五斗米。教里的天师叫孙泰,会玄门法术未卜先知,公主去那儿大概也是为宫中祈祷吧。”说着朝君羽努努嘴,示意她自己说。
君羽当即领会,支吾道:“唔……我前段日子老做噩梦,心里不塌实,皇后建议我去请柱香,说是驱驱晦气,我听说梅花山上的道士很灵,又怕太后您不答应,所以就自作主张去了……”
太后略挑眉梢,斜眼一瞟:“皇后,是这么回事吗?”
王神爱深垂螓首,低声答:“回太后的话,公主是曾与臣妾说过宫中有秽物作祟。”
话音刚落,就听背后有笑声。胡贵嫔掩住嘴笑道:“真是稀罕,公主一向天不怕地不怕,居然也怕起鬼神。臣妾倒听过一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公主这样惶惶不了终日的,可是隐瞒了什么实情?”
君羽微微一笑:“太后明鉴,有没有秽物作祟我不知道,可这宫中有‘鬼’倒是不假。”
“罢了!”太皇太后把脸一沉,喝止住她,“皇宫乃天子之地,万民景仰所归。这种乱力怪神的谣言,以后休要再提。巫蛊之事历来是宫中的大忌,君羽你擅自出去,就算不是私逃也触及了宫规。你心浮气燥,守孝期间屡屡犯错,哀家要是不治你的罪,难平众怒……”
“太后!”王神爱立即屈膝跪下,极力帮她求情,“公主年少无知,请您念在先皇的份上饶她这一回。下月鸡鸣寺祈福,太后年事已高,不如让公主代您前去,一则理应杜除邪秽顺应天道,二则也可以代功赎过,岂不更好?”
沉默半晌,太皇太后轻呷一口蜜茶,合盖道:“唉,既然这样,哀家就罚你在明堂面壁一个月,将《华严经》抄三千遍,对着菩萨好好思过。下月祈福之前,没有哀家的旨意谁也不准放你出来。”
“是。”君羽磕头谢恩,俯下身的那一瞬间,她突然觉得释怀了很多。
也许,在这个时候,需要的也仅是一个人静一静。
此时,乌衣巷内沉寂如死,气氛闷得人有些发慌。一双皂靴在眼前踱来踱去,步履缓缓浊重,拖在灯下深长的暗影。
那双脚徒然一滞,穿绛紫便袍的男人回过头来,沉声问:“你刚才说什么?”
灯影肃杀,白衣公子跪在地上,露出背部清峭的线条。他仰起下颌,微微踌躇着说:“孩儿不想成亲。”
话还未落音,四周已经引起一阵骚动。童仆侍婢们交头接耳,相互窃窃私语。裹着鼠锦披肩的女子快步走过来,髻上的簪子纷摇乱晃。她横身挡在老者面前,回头拼命使眼色:“三哥别气,年轻人心高气傲,说一两句糊涂话,过阵子就好了,你哪能跟他当真。子混,还不过来认错?”
跪着的公子依旧沉默着,一言不发。僵持了数久,男人挥手推开谢道韫,疾步走过来,沙哑着嗓子问:“你再说一遍。”
谢混抬起头,乌沉沉的眸中映着灯影,一字一字,毫不犹豫地说:“我,不会成亲。”
啪!脆声乍起,他的面孔被掴得偏到一边,黯白的脸颊上浮起五道指痕。
谢琰喘息着,声音低沉的以近嘶哑:“我谢氏一门清誉,怎么生出你这个不肖子?这等背信弃义的话,你也说的出口?你想退婚,除非我死了,否则门都没有!”
谢混仰起那张淡漠的脸,依旧慢条斯理地说:“爹您尽可以的发泄,但话我摆到前头,不管是谁家的女儿,我谢混都不会娶。”
“那袁家怎么办?你让我怎么跟袁山松交代?这亲事订了二十年,凭你一句话就想毁了?说出去,你让外人怎么看咱们谢家?”
“哼,一桩没影的婚事就能挽回谢家的脸面?若真是这样,我倒宁愿从来不姓谢。”他唇角微挑,说出的每个字都咄咄逼人,带着不肯妥协的微蔑。
谢琰怒极反笑,一甩团锦袍子的衣袖:“好,好。你翅膀硬了,本事大了,连祖宗都敢不认了。要是真有天大的本事,去年先帝赐官,你为什么不收?整日不学无术,只顾着吃喝玩乐,靠着祖辈糟蹋银子,还敢有脸说不姓谢?”说完气的命令左右下人,“去,把家法拿来,老夫今天打死这个孽障,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
婢女们都耸着脑袋,谁也不敢吭声,只是拿肘撞着互相推委。这些小丫头平日暗慕谢混,私底下撞见都羞的满面潮红,哪还舍得见他挨打。
谢琰见没人肯动,越发气的面色铁青,转过身,亲自去取墙上御赐的宝剑,拔鞘气冲冲地过来。谢道韫见状立刻扑到谢混跟前,用身子挡住他:“三哥,有话好说,这动刀动枪的成何体统?”
“你问问他,眼里哪还有体统?上次公然顶撞先帝,这次又藐视家法,这种目无君父的东西,留着还有何用?”
“住手……咳咳……”庭外传来一阵咳嗽声,谢玄扶着门进来,兴许是走的太急,披着的裘衣已然滑落,落在门槛外瑟瑟吹拂。他紧走几步,犹带着外边的风寒,那张端方阔长的脸双颧凹陷,已经被病痛折磨的不成样子。
“三哥,咱们家虽说风光荣耀,到底已经不比从前,自从我辞了军职,身子一直不见好转,怕也熬不了几天了。子混毕竟是一脉单传,流着叔父的骨血,由他掌领北府兵的军权,我也放心。等过段日子,我就向朝廷上书,先给他一个军职。至于和袁家的婚事,不如先放一放,我去托王珣给袁山松说和,你看怎么样?”
谢琰微微一愣,赤红的双目看着前方,过了半晌方转眼,看向一直跪在地上的谢混。从侧面望去他双膝跪地,唇紧紧地抿着,眼中神情复杂,虽看不透在想些什么,却有种说不出的冷漠清峭。
谢琰蹲下去,单手握住他的领襟,俯身看着他:“孽障,你如果眼里还有我这个爹,就实话告诉我,你不要袁家的女儿,是不是自己早就有了主意?”
谢混略扯了一下嘴角,眼神明澈如坚冰,缓缓答道:“不错,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说完就听啪的一声,谢琰扬手又狠狠甩了他一记耳光。
“啊——”婢女们吓得失声惊叫,全都筛糠似得打了哆嗦。别说是她们,就连谢道韫这数十年来,也没见过他们父子发生这种直面冲突。
谢琰猛地怂开他,喘着粗气说:“畜生,给我牢牢记着,这巴掌是你欠袁家的!”
淡玉色的颊上一记鲜红的掌痕,火辣辣地疼。血像条小蛇般,蜿蜒地从嘴角钻出来,沿着他峻俏的下颌,缓缓淌到喉结上,仿佛是一抹胭脂滑过白皙洁玉。谢混抹干血迹,再抬头时已浮起意态轻慢的笑。
“呵,一巴掌抵一辈子,孩儿多谢父亲成全。”
像是终于达到了目的般,他心满意足地站起来,低头行了一礼。也不等谢琰发话,就自行向门外走去。经过谢玄身边时,他忽又停下脚步,略迟疑了一下说:“叔父,退婚的事就劳烦您了,北府兵的军职我会接手,等到旨意降下来,我就立刻去赴任。”
谢玄露出一丝惊疑,随即笑着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叔父信你,但愿不要辜负了为叔的期望。”
从门里刚出来,迎面的风拍在脸上,凛凛酷寒中,夹杂了一丝微熏的暖意。雪已经停了,皑皑地堆在庭里的松枝头,压的几乎承受不住。冰水无声消融,露出苍绿色的一点松针。
回想那一夜在山洞里,冰封的天地,不觉已经过了半月的时光。他闭上眼,至尽还记得那夜篝火的温度,有个声音在背后幽幽地说:“我喜欢你,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
寒波不溯流(上)
简一墨兰亭笺纸桃花色在线阅读全集:小说全文全集番外寒波不溯流(上)寒波不溯流(上)
群山蜿蜒环抱,苍穹在头顶栩栩展开,宛如一卷倾世名画波澜壮阔,放眼扫去一片苍茫碧草,青色连绵。巍峨旌旗在风中猎猎招摇,隐见上面绣“晋”的墨金大字,旗后一排人马浩浩荡荡,皆身穿羽林甲胄,头盔上插一束红缨。
旧历三月十五,正是每年皇家祈福的日子。
车轮缓慢,鎏金飞角的宫辇从眼前滚滚碾过。天青色的缂金缎帘子撩起一角来,里面的人探出头,盛妆潋滟,神色略有些疲惫。
道路两旁拥着人山人海的观潮,争相笑着竞睹,你推我赶,夹杂着小孩子嚷闹的哭声。人群中只有一个女子是安静的,喧闹中反而显得异常惹眼。她的眉心描着一朵花钿,杏眼水眸衬着唇上嫣红的胭脂。
君羽扭过头,正视着那个女子的脸,总觉得有些眼熟,似在哪里见过,一时却想不起来。那女子望着她,只微微一笑,车辇重又向前行去。
“公主,看什么呢?”侍女也顺着她视线的方向瞧去,并没有察觉到特别之处。
“没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