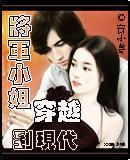刺猬小姐-第5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呵,不重要了,不重要了。
我强压下满心满肺的愁楚,对润之说道:“润之,我祝福你跟贝儿。”然后,起身离开,没有去跟策划部任何一个人告别,实在受不了那样的场面。
那之后,我删除了文博所有的联系方式,后来删着删着就笑了。原来再怎么对数字字母不敏感的一个人,两年,还是把他的所有联系方式刻在脑子里了。甚至是身份证号码和网络银行的密码。我自己的密码从前也时常要问他,救命。
看来要再花几个两年把它们一点一点血肉模糊地从胸中挖走。不过,我相信,时间是最实用的铁锹,好过任何灵丹妙药。
噢,对了,我还退掉了那一对去埃及的机票。
已经去过的地方,何必要再去一遍,冤枉路走得还少么?
只是退票时已经错过了出发的日期,这样一来得折扣了不少钱。
我心疼得直掉泪,要知道,离开文博时我硬气如此,一点没哭。
大约是东西太多,留一半丢一半,我又执意赶他出去不要他帮一点忙,便没有心思尽情哭一场。
谁知道隔了一个月,倒是对着网站上显示的那一点为数不多的退款数哭到整张脸肿胀得像个猪头。
连我妈闻声也过来,我抱着她的腰一声一声喊“妈”,难过得像小时候丢了什么心爱的东西。
她一下一下摸着我的头顶心儿,说,“嗳呀,怎么平白无故撒起娇来了,三十岁的人了呀。”
乖乖的,这一下我更撒欢地哭,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从此以后,我没有再问过晁文博,也没有再提过苏冬亦。
他们有没有一起去香港,或是哪一个去了哪一个没去,已经同我没有半分关系了。
林赛拉终于清静。
我真的又申请去法国读书啦。
读研,两年,心理学。这大概是想为自己的刺猬病找到点医学根据。
熟门熟路的手续,很快便有了消息,夏季成行。
就在快离开的时候,接到许久没有响动的锤子的一个电话,一开口便阴沉沉说,“丫头,我要走了。”
那声音,那语气,活像留遗言。
大热天的,我夹着电话,一边还吹着小空调挫着手指甲,这下心一惊跳,手一僵,“你,你,你,别想不开。”
他沉默一阵,又乍得朗朗一笑,“我说真的,我把画廊卖了!两个礼拜后就走。再回法兰西当高龄学生去。”
我一点未觉吃惊。只是,呵,巧死了,只愣愣说:“我也去。”
“舍不得?要跟哥哥私奔?”
“我说真的,十六号的飞机,直飞戴高乐机场。”
“几号?!”他知我不是开玩笑。
“十六。”我答。
“航班?”他又问。
我冲着纤纤水葱指,轻吹一口气,“我们每次都买得那趟红眼航班呗。”
他又陷入默然,连呼吸起伏也格外清晰。
他说:“行李别超重,不然到了那边,我拎不动。”
当啷,我的指甲刀就掉在地上……
没有再通知任何人,连曼达也没有说,我打算到那边都安顿好了再告诉她,而走前一天还跟她在KTV里两个人嘻嘻哈哈闹到半夜。
笑着笑着,她就哭了;哭着哭着,我就笑了。
因那天是她生日,也是结婚纪念日。
她点了首《祝我生日快乐》,说道:“千万别在生日那天注册,万一不合,事后想起来,到这一天,老了一岁不说,还得忆甜思苦。双重悲哀。”
我这一笑,也很是牙酸。
她和陆彬,到底还是离了婚。只是也未听说他和乔秋瑾成了局。
陆彬一句废话也没有,把所有房子全改成了她的名字。
可人也丢了,要房子做什么?
投资?可在感情的投资里,我们两个皆是亏损连连,眼见破产。算了罢。
走得那夜依旧瓢泼大雨,呵,心境迥然,祖国挺纠结地欢送我,只能祈求别误点。
入关前,我回头朝我妈幽幽挥了挥手。
我妈也朝我幽幽挥了挥手。
锤子大包小包得拎了两手东西,一副愚公姿态,想挥也挥不动。
好在大家都是一脸安素淡然。
因为该经历得都经历过了,也算活够本了,往下就是赚得了。
干吗不安素淡然?
快要登机的时候,雨淅淅沥沥地,居然渐渐停了。
我终于如期离开。
夜幕如遮。
飞机上,从椭圆的窗子望下去,地面上的所有一切渐若零星,为之神驰。
锤子却伸手过来哗地一下落下遮阳叶。
他说,别看了,越看越舍不得。
我回过头勉强地笑,靠在他肩上闭眼,略略矫情说道:“哥哥呀,活这么大,头一遭知道什么叫心死人去。”
锤子轻弹了下我的脑门,“你这丫头,飞机上的,说点吉祥话成么?”
我却偏偏歪歪腻腻地对他一笑,他也颇是无奈起身关了头上的顶灯,又替我拉上薄毯,低低说声:“睡罢,一觉醒了就到了。”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哪怕在隆隆的飞机声里,也能安心地睡去。
其实,还有什么好舍不得的?
你说呢,是不是?
作者有话要说:终于《刺猬小姐》完结啦,撒花,撒草。
===================================
番外全
panion Volume。 3 。。。
三个钟头连带间息十五分钟,贝儿不时低眸扫表,眼见一到点便立刻宣布晚课结束,收拾东西匆匆和外籍学生们告别,再心急火燎驱车赶往原子公寓。
今天润之也加班,女儿真希没人顾,只好交给文博照看,连幼稚园下课也要劳烦他去接。
这一有了孩子,算是甜蜜的负担。可时间通通不是她自己的也就罢了,还累占别人的,总有些不合适。
可早上润之对此,却大而化之地说,“你就放心罢。不信你看小木,简直像个没娘的孩子,还不是叫文博带得跟吹了气的球一样,抱一会我都手酸。”
她当然知道,文博是个很妥善的人,嘴上却忍不住调侃:“还好意思说,文博私下向我抱怨家里情况极惨,丈夫见不着妻子,儿子见不着娘,就是因为有你这种榨尽骨髓的老板。”
刚结婚的时候,润之嫌她说话做事太客气。转眼五年,不长不短的时间,足够把什么毛病全改好。他们夫妇一直相处融洽,极少脸红,并且约定绝对不在真希面前不愉快。标准夫妻有标准夫妻的好处,只不过极不标准如文博那一对也属罕见。
润之听到这条评价则笑说不关他的事,所有一切根本是晁文博自找的。
下课已是九点,过了高峰,贝儿很快就到原子。
进了A座十五楼,门铃按两下就有人开。是文博。
门里是暗的,他悄声说:“嘘,希希跟小木都在楼上睡着了。”
贝儿一听也只好蹑手蹑脚地换鞋,进门。
文博又说,润之他们也已结束工作,马上赶回来,小孩喂饱了才睡着的,剩下四个大人晚饭一起随便吃点就成,反正已到周末。
贝儿没有异议,她主动去厨房帮忙。
切菜时两个人闲聊起来,贝儿问:“敏之同意你长期留守家里带孩子?”
文博无奈地笑着皱眉头,“怎么可能,昨天她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下个月再不回奥安上班,叫我东西也别收拾,直接滚蛋。”
贝儿听了结眉一笑,“一听就是敏之会说的话。”
“她已经仁至义尽了,还说完全是看在干儿子的份上。有哪户人家生孩子丈夫请假请得比妻子还长的?”文博把鲈鱼放进锅子里隔水蒸,控制好火别过头来对贝儿展目说道,“这种事,只有我们家赛拉干得出来。”
明明是责怨的话,说出来却全然听不出那个意思。
“赛拉妈妈呢?她不愿意帮忙?”贝儿问,她母亲在本地啊,不像她这里没有亲故,润之的家人也在外头,希希是她一把手带到两岁才丢给润之的。不过,这算殊途同归?还好,润之多带一年,世界上有个叫幼稚园的救命地方。
“噢,那个,丈母娘一开始就说,谁生的孩子谁带。其实不过是想鞭策赛拉,谁知道她完全不吃威胁。她现在一周来三天,还是忙不过来。”文博将电饭煲定时再拿咖啡壶煮上茶,吁口气,“不要紧,下个月我母亲会过来,她巴不得能全天候蹲守来带孙子,我以前真不知道她对这种事会这么有兴趣。”
贝儿更觉得好笑,刚想再说点什么,楼上哭声大作。
小孩就是这样,一个哭带着一个,有连锁反应,两个大人连手上的餐盘刀组还没丢下楼上已是此起彼伏。
女儿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见到上了楼贝儿简直像猴子见树一样牢牢攀在她的脖子上,闹着叫“妈妈”,不一会鼻涕眼泪混一块糊腻腻就蹭到她套装领口,她也只好笑着颠着哄,“嗯?希希,怎么了?跟弟弟比赛谁哭得响?”
希希真是给她爸爸宠坏了。四岁多点的小丫头,一点点事情就哭,而且每次戏路都不同。一会梨花带雨,一会潸然湿衫,一会涕泗滂沱,一会锥心饮泣。她知道一哭立刻有人满足她,尤其对润之,这几段保留招式是百试不过,实实在在一个小戏精。润之也说,这样有天赋,要不要提前规划职业出路?
相比之下,小木果然是小伙子,简单爽快,两根水管子一爆也不外乎三桩事,要么饿了,要么拉了,要么被赛拉掐了,无意外不惊喜,要多简单有多简单。
文博蹲在床边很麻利地给手足乱舞的小木换尿布,说道:“小木,老实点,一会你妈回来又得掐你了。”
贝儿刚想说,这怎么可能管用,一岁还不到罢?乱动和狂哭是天职。
谁知,真就有用,小木收到警告马上老实,眨巴眼睛一副求饶姿态。
她不由大叹气,赛拉到底做了点什么?
“赛拉那天还拉着我说,要是希希再小点是不记人的岁数,就拿小木换走。”贝儿一边低头唔唔哄着女儿,一边微笑说:“她就这么不待见儿子?真是稀奇。”
文博整理好,把孩子抱到一边的小床上去,盖上被子,废话也不用说一句这小家伙又昏睡过去。
“赛拉生产前一天还在这张床上捧着肚子蹦跶,指天誓日地说什么如果生出来的不是闺女一律就当胎盘扔到大街上去。”他看到儿子自己别着小脑袋翻了个身,有点不可置信地说,“结果这只胎盘被我拣回来养着养着,居然下个月也满一岁了。”
贝儿听了笑到腰重,笑完又佯装毕恭毕敬地说:“晁师兄,你真是老了,老人才会说这种有伤流年的话。小孩子见风长,还是很快的。不过赛拉真是过分,让你留在家,自己冲锋陷阵去。”
这时,楼下门响,有钥匙转动的声音。
文博说:“曹操说不得,一说就到。”
就听见有人蹭蹭蹭上楼的声音,一边欢叫:“小木小木,想死我了。”
“赛拉你轻点,刚睡着。”文博迎上去。
赛拉却一把拨开他对贝儿说声:“你来啦,润之在停车我先跑上来了。”然后冲到小床边,极喜庆地看了两眼,然后轻轻挑开印花小被子的一个角,伸手到被子里去捏小手小脚,软软地,像一堆夹心棉花糖。
贝儿见赛拉呼吸还有些不平,真是一路小跑上来,也是会心。
她抱着希希下楼。文博家的楼梯本就窄,后来又装了一条手臂粗的扶手,更窄,是以她抱着孩子走得有点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