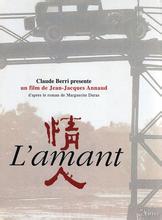情人间的诗总有两三句-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眼前人是指谁?难道这是他说给自己的?是遗言?
“嗯……我猜……”廖成开始径自揣测起来,“学长是失恋了吧?叫你惜取眼前人,八成他错过了吧。”
有道理。
我看着眼前的廖成,他蹙眉思索的模样很帅气,难怪刚入大学校门,表白的女人已可以组一支足球队了。
“看什么看?赶紧吃饭!”廖成见我直愣愣地盯着他,一脸惊悚,用筷子不客气地问候了我的脑袋。
“哦……”我低头扒饭,心里涌起不好的预感。
三天后,警方撤去警戒线,实验楼恢复了自由身,学长最终被确认为是自杀,但警方没有公布他自杀的原因,说是还在调查。校园里将这事传得风生水起,疑神疑鬼,有人说学长感情不顺心灰意冷,有人说学长仕途不顺走投无路,更悬者说是谋杀,还有人在论坛上连载了以学长为原型的恐怖小说,顿时遭到一大批学长拥护者的讨伐。
不管流言如何荒唐,学长终究是不在了。听文学社的人说,学长的母亲来从乡下赶来收拾他的遗物,几度哭晕过去,悲恸凄惨的模样令四周的人都不忍心看。
但风波远远没有结束。有传言说,每天午夜路过实验楼,总能听见从楼顶飘下幽幽凄婉的箫声,和着清冷淡漠的月光,使人不寒而栗。
于是关于学长的冤魂在楼顶久久不散怨气深重不能投胎的谣言又是满城风雨。
我得知后,十分气愤,真是可笑,难不成还会闹鬼吗?这些无聊之人,拿死去的人当谈资很有意思吗?
“怎么可能有鬼!?”我愤愤地道。
廖成看我如此激动,就说:“有没有鬼,亲自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啊?”我目瞪口呆。
结果当晚廖成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到了实验楼下,借着惨白的月辉,我们溜进了实验楼。自从传出闹鬼的流言后,个别几个喜欢在实验室熬夜做实验的博士生都卷铺盖回了宿舍。
空荡荡的长廊,黑漆漆的实验室,我的心跳得极快,好像要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
廖成捅了捅我,问我:“新,你怕么?”
“怕,怕什么?”我故作镇定,扫一眼四周,又不禁瑟缩,“我胆子大得很!”
廖成轻笑一声,明显是在嘲讽我,我不服气地瞪他,结果他也正好看我。
“新,你怕的话,拉着我的手。”他把手伸出来,等待着我去牵起。
我犹豫着,虽是做了十几年的兄弟,打过闹过,却从未如此真挚地对望过,他对我的好令我微微不知所措,别扭极了。
有什么,似乎在发酵。
我鼓着腮帮子,一把握住他的手,拽下来,贴在身侧,“好啦,赶紧走啦。” 他的手有厚厚的茧子,打篮球打的,摸上去粗糙又厚实,很有安心感。
我们肩并肩一起朝楼顶走去,结果到了四楼,便听到一阵萧索凄凉的箫声幽幽地从楼上飘了下来。
我倒吸一口气,不住捏紧了廖成的手,廖成知道我怕,也用力地反握住我的手,让我安定下来。
“鬼……?不,不会吧……”
“别瞎猜,我们上去看看!”
提心吊胆地走到楼顶的门口,箫声忽然停了,我们一顿,便看见一道黑影飘到了我们跟前,手执长箫,静静地背着月光站立。
我的腿肚子一软,趔趄一下,差点翻下楼梯,幸亏廖成眼疾手快一把扣住我的腰身,把我揽到他的身侧。我的额头猛地磕在他硬邦邦的肩头上,一阵晕。
“嘶……”
我扯着廖成的袖子,廖成把手贴到我的额头上,轻轻地揉了揉,“疼吗?”
“还好……”
在我们说话之间,那道身影悄无声息地擦肩而过,隐没在楼下无边的黑暗里。 我这人一怕起什么来,就变得比较迟钝,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下头,不肯回神了。
“是人?是……鬼?”我口吃着。
廖成笃定地说:“是人,有影子刚才。”
“难道半夜在楼顶吹箫的就是他?”我猜测。
“显然是呐。”
“为什么?”
廖成不回答我,只是把我拽上楼顶。天台的风很大,鼓起宽松的衬衣,我看见廖成的刘海也被吹了起来,精瘦的身形看上去很单薄。
除了一些生了铁锈的管道,天台上再无其他。空旷的平台上看星星看月亮倒是极为合适。天幕倒垂,上头绣着零星的星辰,孤月高悬,寂静,冷清。
等我回头时,廖成一个人蹲在一处角落不知在看什么,不停地用手掸着灰尘。
“廖成,看什么啊?”
“新,你过来,看。”他冲我招招手。
“什么啊……”我好奇地凑上去,蹲在他身边。
借着明亮的月光,墙壁上的一行字显现了出来,似乎很早前便写上去了,颜色淡褪,尘灰满布。要不是廖成掸开一层灰,怕是很难发现。
上面写了一首短诗。字迹遒劲飘逸,看得出是个练家子。
爱他的明眸与皓齿
爱他的才情与慧黠
当我去敲他的门
寂静无瑕
箫带走了他
神带走了我
诗风凌乱却张狂,不齐却有力,下一秒我便肯定这是学长写的!配上这字迹,一定是!
“学长,学长他,他真的是因为感情受挫才自杀的?”
从这首诗中可以明确地体会到学长的深情热恋,他爱得一定痴狂。
廖成幽幽地叹了口气,“新,难道你猜不到吗?”
我不解,扭头去看他,眨巴一下眼,“猜到什么?”
“学长……是gay。”
廖成沉默了一下,吐出这么一句话。
我一惊,连连摇头,直接否定掉这个猜测,“别瞎说,学长怎么,怎么会是同性恋呢!”
这种事怎么好胡说八道,对死去之人不敬啊!
廖成深吸了一口气,他似乎猜到我这反应,伸手按住我的肩,“新,你听我说。你看这诗上面用的是单人旁的‘他’,学长也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写错他她呢?再看倒数第二行,‘箫带走了他’,你不觉得刚才从楼顶下去的那个男人正巧也是带着箫的吗?”
“等等……你不能凭着这些表象猜测真相啊,说不定就是学长写错了他,那个男人恰好到楼顶吹箫罢了……”虽说这些狡辩很无力,但我仍偏执地不肯相信。
廖成看着我,他的眼睛里倒映着一片璀璨的星光,流露出几分心疼,“新,我告诉你,其实我很早前就见过这个男人了。他是声乐系的才子,挺有名的。有次我路过音乐教室,看见学长站在窗口呆呆地往里看,好像入神了一样。教室里飘出悠扬的箫声,吹的曲子,和我们刚刚听到的一样。你明白这是什么情况吗?我不信学长这么忙的人,天天抽空去那里听吹箫……”言下之意,便只有另外一种可能了。
我茫然地摇着头,心里很乱,“怎么会,学长喜欢男人?”
廖成绷着一张脸,严肃地问我:“新,你是不是……排斥同性恋?”
“啊?”问题太跳跃,我一时没回过神,我对上廖成的眼,猛然发现他的目光如火般炽热,熊熊燃烧着,也不知是激动还是愤怒。我顿时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接话。
“哎……”廖成拿我没办法,只好叹了口气,垂下眼,“当同性恋……真是辛苦呢。”
什么意思?他是在怜悯同性恋吗?
我心里很不舒服。
chapter 8
后来学校举办艺术节,廖成告诉我,那个吹箫的男人会登台。结果当天我去了,看完了整场表演,却不见那人身影。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已在半个月前退学,不知所踪。
学长死了,那个男人走了。事情似乎就这么以一种惆怅凄凉的结局收场了。然而从那晚在天台上被廖成质问后起,我的内心似乎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注意起来往于廖成身边的人,是男的,我会狐疑地看一眼,是女的,我就没好气地睨好几眼。一段时间下来,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心里一下子慌了。
我,好像是喜欢廖成……
然而年少时那些禁忌的爱恋密不可宣,我实在不敢对廖成说出我对他的感觉。深厚的兄弟情忽然变了味道,我猜他,接受不了吧……
一如现在,还是难以说出口。
廖成怒气冲冲地把我拖下这栋楼,与我吵了两句,十分不是滋味地抿紧唇,像一头见了红布的斗牛,理智全无。我的胳膊在他手里受虐,被他掐得又红又痛。可我不敢挣脱他,只好满腹委屈踉跄地跟他下楼,漫无目的地向前冲。
日头偏西,温热的暖光打照在廖成的身上,将他镀上一层虚幻的金光,犹如神祇。我睁着眼一直盯着他的背影看,看啊看,以为自己快要迷失在他的幻影里。
猛然间,廖成停下了脚步,我一头栽了上去。他的背脊很硬实,我的鼻梁真是疼啊。
“骆新……”忽的听他喃喃自语。
“……”我不解地抬起头看他的侧脸。
“新……”他在说什么,“新……”
在叫……我的名字?我一怔,立即靠过去,低声应道:“我、我在……我在……”
他略微失神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一把拉起我的手,对我说:“对不起,刚才有些冲动,不是有意要和你吵架的。”
这谦卑的态度,以前的廖成不可能有,而他现在学会了低头,可见他真的长大成熟了。
我粲然地一笑,“没关系,我还不知道你的脾气,来得快去得快。”
廖成似乎有心结,勉强笑了笑,“是吗?我是这暴脾气,一直没改掉。”
我一惊,觉得廖成误会了,赶忙解释:“不,改了,改了,比以前好很多了!”
瞧我一脸认真样,廖成这才会心地笑了起来,“是不是比以前更有魅力?”
我一翻白眼,故作迷惘状,“嗯?有魅力?那个帅哥在哪里啊?”
廖成知晓我在打马虎眼儿,只笑了笑,便拉着我走向下一栋楼。
之后仍旧遇到些奇奇怪怪的人。有个老大妈拉着廖成硬要他喝口茶水再走,廖成拗不过答应了,那老大妈泡了杯菊花茶给他……
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抱着廖成的腰身哭闹:“廖哥哥你好久没来看我了嘤嘤……人家可是你女朋友呢……呜哇……”
我斜他一眼,“十几岁的小女友?”
廖成懊恼地扶额,“忘了她了,哎,她自封的啊。你忘了,陈阿姨家的女儿啊,你走了五年,她都十八变了……”
我也一头冷汗……
直到黄昏降临,背后的影子被拉得又长又瘦,我们才算走完了所有的“单身住户”,任务完成。 可是我已经累瘫了,好久没有上上下下走那么长的楼梯了,身体素质大大地跟不上,着实丢人。最关键的是,廖成看起来仍旧精神抖擞……
“我饿了。” 廖成憋着嘴,十分实诚地看着我,像只大型犬在要食。
我撇撇嘴,回答:“我也饿……”
“怎么办?去哪里吃?”他问。
“唔,回我家吧,我妈应该烧饭了。”
“好,那就打扰了。”
“傻瓜,客气什么。”
我们俩回到家,正逢母亲端着菜盘子从厨房走出来,她看见我们,愉悦地笑起来:“哟,回来啦?都发完啦?正好,那就吃饭吧!”
我俩面面相觑,总觉得平白无故做了一回免费劳动力。叹了口气,还是坐下吃吧。
廖成捧着饭碗,鼓着腮帮子夸母亲:“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