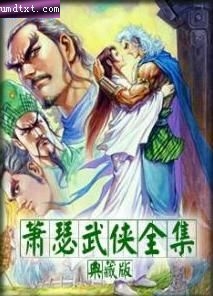何处寄余生-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薛覃霈无法入睡,只把双手叉起来放在了脑后,半躺半不躺地倚着墙。正巧几人没有枕头,靳云鹤便把头枕上了薛覃霈的大腿。
“你裤子脏了。”靳云鹤头一沾腿立马小声嚷嚷,“都是湿的。”
“刚刚走在路上踩了个水坑,溅了一身泥点子。”薛覃霈毫不在意,甚至都懒得看一眼,然而随意说道,“那你倒是把头挪开啊。”
“真湿了,还凉着呢,你不冷啊?”靳云鹤的舌头片刻不停,却是不见脑袋动弹。
“冷什么,你一枕上去就暖了。”薛覃霈倒是实实在在觉出了舒服,腿是真的不冷了。但他还是伸手拨开了靳云鹤的脑袋,嘴里道:“你得冷吧,赶紧起来。”
然而靳云鹤顺势挪上了他的肚子,另一边也不忘把手放在那块湿凉的地方:“还行,给你暖暖。”
这下两人才都舒服了,依靠在一起,累得再不想动弹。
大概是知道对方都没有睡觉,靳云鹤在片刻安静后突然来了一句:“哎你知道么薛覃霈,其实我以前老想从你家偷钱,偷完钱就跑,然后气死你和你爸。”
薛覃霈嗤笑了一声,回应道:“我以前也老想,但跑了一次,我爸根本没发现我跑了。我自己在上海晃悠,把钱花完就自己回家了,想想真窝囊。”
“我倒是后悔自己当时没跑呢。”靳云鹤叹了口气,“说真的,要是我跑了该多好。”
薛覃霈也没有回话,他在想。对于靳云鹤来说,要是当初真的跑了,也许并不是件坏事。然而谁又知道呢?
现在两人好的时候是贴了心的好,因为知根知底所以无话不谈,可靳云鹤却又屡教不改死心塌地地,非要喜欢,因此来来去去,便总也免不了有恨得牙痒和绝望到冷漠的时候。
薛覃霈是看出来了,他也改不了自己的臭脾气,所以两人臭味相投。但真正到了危难的时候,总还是能互相依靠的。这种依靠像是家里人的依靠,像船躺在水的怀抱里,像一只黄鼠狼遇到另一只黄鼠狼。
薛覃霈是如此想了,靳云鹤又如何不知道呢。他自是个眼尖的人,琢磨揣度,种种不在话下。
其间静默不久,两人各自的小心思皆是百转回肠,到末了薛覃霈发出一声叹息,不再说话了。
二狗本是睡了,此刻突然从梦里惊醒,瞧见二人黏腻的样子,便横过来钻到了中间,把脑袋往薛覃霈胸前蹭。
靳云鹤则被霸道的二狗挤到一旁,四仰八叉地摊着,也不再动。
第54章 伍拾肆 恨别离
他们并没有忘记此行目的,老王最先告别,是真的寻亲戚去了,剩下几人则又匆忙赶往他处,打听起了薛文锡的消息。
他们先回了薛家一趟,发现薛家已经隐隐有些败落了——贴上了封条,实际并没有人打理,因此几人又迅速离开,继续毫无目的的寻找。
正在他们四处奔波得口干舌燥之际,耳边突然响起了熟悉的轰鸣声。
然而与那天在船上听到的声音不同,那轰鸣声不像是穷途末路、垂死挣扎的轰鸣,而是连续而稳定的轰鸣,骇人得很。
街上本也没什么人,此刻都像约好的一般一涌而走,瞬时便没了影。大约这附近就有个避难的地方,因此四面八方皆有人连滚带爬地往这里跑,几人先是面面相觑,见人群跑过来了,便也跟着他们跑。
几颗炸弹投下来,薛覃霈觉得不远处似乎着火了,火光都冲到了天上,蔓延出一色橘红。身边隐隐传来尖叫,他恍然着,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地狱,然而还是不由自主地伸手拉了一把,期待手指能触到靳云鹤或是二狗的哪怕一个袖角。
他们想找个地方躲避了这场轰炸,但在混乱中却根本找不到方向。空中的飞机是只增不减,几乎遮住了阳光。本应是正午,日头当空的时候,上海的这一处却是有些荒诞地,在类似黑夜中孤独地燃烧。
恰巧前面一个矮楼坍塌了下来,那处的人群便散开了一瞬,薛覃霈也是瞬间清醒,欲要招呼一声,往已然轰炸过的地方躲。
可还没来得及迈腿,他便一个踉跄,自己却是被谁扑倒了。
在轰鸣过后短暂的失聪后,他先是听见靳云鹤一句声嘶力竭的喊叫,而后脑袋一凉,他以为自己要死了,慌乱间抬手摸了摸后脑勺,竟带下来一手的血。
可他一点也不痛!
薛覃霈挣扎着爬起来,心里除了慌乱还是慌乱。他分明知道自己身上趴了个谁,却又不敢问。直到终于站起来,他一低头,才看见了地上躺着的——二狗的半个脑袋。
一个横飞而来的弹片,削去了二狗的半个脑袋。
薛覃霈觉得嘴里有点腥甜,似乎是把舌头咬破了。他先是想喊叫,但声音嘶哑,在薛覃霈几乎已经完全失聪的耳中脑中引不起任何波澜。
他双膝软瘫着跪下去,用手捧起了二狗的半个脑袋。
腥甜的感觉好像是淡了,腹中却是又有绞痛,他干呕了两声,坚持着摸索到了二狗的身体,把那半个脑袋拼了回去。此时一波飞机已经远离,轰炸开始在不远处的另一地方继续肆虐。
暂时没有轰炸了。
被飞机遮蔽了的日头很快可以再次闪现,然而人命是一条一条地失去,胳膊腿儿乱飞,那都是找不回来也拼不回去的。该死的都死了,伤重还在苟延残喘。街角处突然又涌来一波人,大约是从刚刚逃出来的,正互相推搡着,手脚并用地往前跑,有摔了的,大概就被踩死了。
薛覃霈不敢逗留,先把二狗拖到一处放下,放安稳了,这才直起腰来,发现靳云鹤已经在人流里消失不见。
他心里一慌,隐隐觉得自己再也找不到靳云鹤了。
“靳云鹤!”
“靳云鹤!”
他开始是声嘶力竭地吼着,但很奇怪地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周围的世界像是变成了一个默片,除了恼人的嗡嗡声他什么都感觉不到。然而他还是喊了很久,在四处奔跑寻找。直到他喊得眼前都暗了,看不清东西了,才终于精疲力竭地一屁股坐倒在地,靠在二狗身边。
“靳云鹤没了。”他说。二狗的脑袋要往下滑,他用手托住,眼眶一酸。
“你救了我。”薛覃霈把手搭在膝盖上,肩膀靠着二狗的肩,继续道,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也不知前方有什么。
直到眼前清楚了,嗡嗡声也变小了,薛覃霈才看见——街对面还竖着个几乎快要倒塌的大广告牌。牌子上是一个女艳星,好像是叫小香。红极一时。
仅从一半广告牌上也能隐隐寻出她的风韵来——明媚皓齿,细腰肥臀,是很美好。只那被炸去一半的脑袋,倒不如二狗被齐齐削下去的利索——焦了一半,边缘扭曲着,仿佛不甘。
薛覃霈这才突然想起来,原来当初二狗的名字是由小香得来的,赛小香。
一个男孩子,硬要拿他和一个女艳星比较,二狗真是委屈,真是不甘。薛覃霈想,可自己也没能给他一个好家。
他不管二狗骇人的脑袋,又和二狗安静地靠了一会儿,最后俯下头,把嘴凑到他耳边轻轻道,“再见了二狗。”
接着他起身,从满地狼藉中挑拣出一块完整的木板,把着二狗放在上面一路拖着到了黄浦江,然后噗通一声投了进去。
第55章 伍拾伍 军中
薛文锡在后方蹲守了几日,却哪里想到这守军竟如此不堪一击。仗还没打几天,上海就匆匆沦陷了,半个中国也已经沦陷了,颓势如同山倒,他竟头一回有种无处可去的感觉。
即便是当初离家的时候,他也没有过这种感觉,因为觉得自己总有一天是能够再回来的。
然而现在,薛文锡无声叹了口气,弯下腰在横七竖八的尸体和狼藉中满地找烟头。
他早就抽完了身上最后一根烟。他烟瘾大,又没有寄托,便时不时地要找点事情做。
打仗?
他大概真是想多了。自从他投了军,便一场仗都没打过,连挨打都挨得敷衍了事。中国军队自始至终地都在撤退,如今撤着撤着,他那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念也给磨没了,心想,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呦。”此时薛文锡惊喜地看到一支完好无损的烟,正夹在一个死人手指里,大概那人还没来得及抽上一口就突兀地死去了。他嘿嘿一笑,捡起那根烟,自己划了根火柴抽了起来。
“退退退,再退就要退到南京去了!”身旁走过一个骂骂咧咧的伤兵,也正弯着腰扒拉死尸,突地瞥见薛文锡手中的烟,那伤兵站住不动了。
“你这,捡的?”那人狐疑地问道。
薛文锡冲他咧嘴一笑,也不知是什么意味。
那人则咽了口唾沫:“赏爷一口?”
薛文锡便伸了胳膊,把烟递过去给他抽了一口,而那人猴急地凑过嘴,竟是一口吸个没完了。
薛文锡不笑了,劈手把烟夺了回来。
那人急得呛了一口,被烟牵着走,险些跌入薛文锡怀里。
薛文锡又笑了,伸手一拉拽住了他的手腕,然而实际上内心是一丝调笑意味都没有的。他只是内心空虚,横竖看看这四周光景,怎么看也是了无生趣,他半生过惯了声色犬马的生活,一下子落入狗窝,便只得学会在这了无生趣里自己找点乐子。
没想到那人也不气,就只是愣了愣,抬头看他:“你……”
薛文锡也愣了。
那伤兵虽是浑身褴褛乌黑,腿也坏了,可一张脸却是年轻正好,是靳云鹤的年纪,甚至还要再小一些。
脑海中恍然间出现了靳云鹤的名字,他竟绞尽脑汁也记不起靳云鹤的样子了,他模模糊糊地想,模模糊糊地忘记。至于靳云鹤的爹,那更是上辈子的事情,早与自己没干系啦!
这时伤兵似乎是反应过来了,怒道:“你他娘的给老子撒手!”
薛文锡这才撒手。
“想什么呢?”伤兵拿不干净的袖子擦脸,反倒是越擦越脏,“老子的脸好看?好看也别看,早他妈的该烂了!早晚你也该烂了!”
薛文锡笑不出来了,他只盯着那伤兵,莫名地开始了讲话,声音是有些轻的:“别这么说,你这不是还没烂么。你看城里死了这么多人,他们都烂了,可你……”他顿了顿,方又重复一遍,“这不是还没烂么?”
“行啦!没烂!都没烂!”伤兵怒极反笑,一张黝黑的脸上也看不出什么明晰的表情,“还没烂的老子要从死人嘴里抢烟屁股啦!”
言罢甩手要走。
薛文锡却是把手里那最后一口递了过去。
“你这又是干嘛?”伤兵笑,继续笑,看他,“耍我?”
薛文锡苦笑着摇头,扯了个谎:“你长得……真像我儿子。”
伤兵这回是真正地愣住了,喉咙里哽了一声,含含糊糊地问:“你说什么?”
薛文锡却是摇头,不再说话了。
伤兵其实是听得很清楚的,不知为何还是要问。但见薛文锡不言不语了,他便也怪里怪气地哼笑一声,没魂没魄地继续往前走,继续弯着腰扒拉死尸。
“喂,你叫什么啊?”薛文锡在他背后喊道。
“我?”伤兵终于不再生气了,竟然有些心平气和,“不记得了。谁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