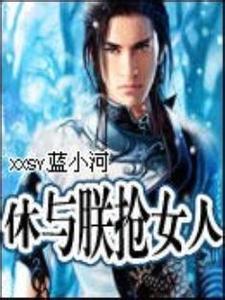悲情女人的灵肉流亡:此情无法投递-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我真怀疑!爸爸太了解你了,你怎么可能是个坏蛋,是个罪犯?你从小都是规规矩矩的,特别地善解人意,路上碰到个瞎子瘸子要饭花子都会停下来替人家伤心。你性格里从来没有卑劣的成分,从幼儿园到高中,每与同学有争执,你都是文弱说理派;最多你喜欢看书,玩一些艺术青年的东西,诗朗诵、画画之类,但你从来不玩什么递纸条的小把戏,回家来从未听你提过任何女生的名字……总之我多么信赖你、倚重你,我哪里相信你会犯下这令人不齿的流氓罪!你才十九岁对吗,我总觉得你那么小,什么都不懂,而性,多么复杂、敏感,带着原罪的肮脏,你怎么可能会跟它发生关联……
所以,说实话,我真的不确定,孩子,你懂不懂那些事情?那个晚上,你真的“做”成了什么吗?这是个关键的问题,超过了眼下我这尊严扫地、唾面自干的境地,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我真愿意用我全部的已知去换取这一个未知,让你活转过来,只要你当面儿跟我说说清楚: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丹青呀,可怕的怀疑像虫子一样,在我心里越长越大,并在各个角落爬来爬去,让我坐立不安,如百爪挠心!!我怀疑你根本就没有“做”!
再说,丹青,你可能都不信,等你真正走了,我倒不知道伤心了——
3月27日上午10点40,你的游街处决之时,那道罪孽深重的门槛跨过之前,你虽还是活着,却活得让人煎熬,似乎坐着不动就是放弃就是背叛,得随时想着你将至的死。于是,夜不能寐、日不能作,带着不近世情、难以解释的焦灼,好像巴不得这一切早点结束似的。
真正迈过去,倒也罢了,一颗心反而彻底放下来,就范于现实、委身于现实,再没有想头,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踏实了。有一个晚上,我甚至还睡了个囫囵觉。醒来后,我羞愧得热泪长流,你都死了,我却还在一枕黑甜——你可以理解吗,是否认为我冷漠无情?这是多么古怪的情感! 。。
肉体与美(3)
但是,孩子,真正到今天,你彻底地死了,我的理智倒又全部复苏了:伤心悲痛有什么用,那都是些无谓的情感、无谓的浪费。接下来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惜一切手段,弄清真相,尽管这真相于事无补。所有那些同情我怜悯我的人们,随便你们说什么吧,尽管去说吧,我陆仲生现在不要脸面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儿子你根本就是冤枉的!爸爸要替你查清,爸爸要替你*!
' 3 '
是啊,爸爸,那个夜晚,那个我没机会告诉你的夜晚,我是不是冤枉呢,我竟然说不好。但总的来说,它决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是我的骄傲与苦涩——对肉体与美的追求,就算是错,也错得对。
不过爸爸,有一点,你平常所看到的、所引以为豪的我,只是河流上循规蹈矩的平静波纹,而我真正的一部分则是潜流暗涌,你从未觉察……
你可能都不知道,从很小就开始了,不知怎么搞的,我对人的身体特别感兴趣。在老天赐给人间的所有礼物中,庄稼、花草、雨水、月光……一切当中,我最喜欢人体,皮肤、骨骼、毛发,牙的硬舌的软,关节的灵活,心脏的搏动,饥饿与排泄,亲近与笑容。世间有什么东西比人体更为精巧、复杂!我时常用很多的时间,像对待一个永远玩不腻的玩具一样研究自己的身体,每一个凸处与凹处,每一点小反应与小变化,一天中的不同状态……
长大一点,我开始注意到更多的身体,城里人与乡下人,老人与儿童,健康的人与残疾的人,男人与女人,东方人与西方人,这一个人与那一个人。我有了个不自觉的小习惯,走在马路上、坐在公共汽车上,最喜欢盯着别人看,无穷无尽的身体呀让我心满意足!我远比研究蝴蝶的人、研究星辰的人都要幸福得多,都说蝴蝶与星辰的种类繁多,可是,多得过人的身体吗!
特别是……特别是女生。这是有限的范围内,我能观察到的最普遍的身体。我承认,我喜欢看她们,我极想知道,她们到底哪里跟我不一样……记得在初中,那屈指可数的几节生理卫生课上,每当老师让我们看挂图,看胃,看心脏,看大动脉,我都会在抓紧机会在下方的三角区上迅速而仔细地溜上好几眼,试图去想象,那图上,经过抽象处理、没有画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我会在男厕所里偷听女生小便的声音。夏天做广播体操时盯着前排女生衣服的后襟,等着露出一小截腰。我还喜欢看刚刚洗过头的女生,她们的头发把衬衫后面打湿,贴在肩胛骨上,那若有若无的滑动!初夏到来,她们会说好了在某一天穿裙子,细细的小腿,在漫长冬春的遮蔽之后,那样纤弱,似乎都经不起我眼光长时间的停留……
啊,不仅仅是女生,我们高中还会有一些年轻的女老师。我记得,有一位丰满的音乐老师,有一次,上课中间,她的内衣带子突然滑落了,透过淡色衬衣,我清楚地看到她的乳晕……
有时候,趁你们都没有下班,我会倚在阳台上,用家里的那个单筒望远镜看楼下的人……主要是女人,这角度不算理想,但在夏天,还算不错,她们的乳房,从上面看下去,多么浑圆而天真,最完整的小波浪线,最自然的小*……在热气弥漫的大街上,在树影的浓淡里,真是美妙极了……我常常构想着,能从这个角度,画一群身体,女人体,看不到她们的脸,只有身体,百分百的肉体,连绵起伏,永无尽头,布满整个庞大的画布,足够所有像我一样饥渴的眼光在上面迷途忘返、乐不思蜀…… 。 想看书来
肉体与美(4)
别的我想不起来了,差不多就是这些,这就是我在青春期所看到过的一切了。仅仅就是这些,可怜得都经不起回味与咀嚼。十五岁之后,每晚睡觉之前,我都感到莫大的空虚,体味到那难以形容的饥饿与绝望。
索性跟你全说了吧,反正我从不以此为耻——还记得我在高中坚持要学画画的事吗?为什么要学画?也许我并没有这方面的秉赋,但那样,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从老师那里看到很多的人体——画册里,那许多的雕塑与油画,不论女神还是厨娘,大卫或是拉奥孔,都是那样,把身体尽情地展现出来,*的胸腹,耸起的肌肉,我太喜欢了!我愿意为那些健美的人体付出一切!我喜欢看到那些松垮下来的衣裙,完全暴露在视线下的肉体,结实、柔软、无辜!
呀,生活中绝不可能看到这种坦然而舒展的景象,生活中从来不会有人这样涉及最伟大的身体——真实的世界,肉体好像永远缺席,除了表情与声音,除了吃饭与睡眠,除了学雷锋做好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好像我们都没有身体。如此鲜活多变的身体啊,人人熟视无睹!
包括你,爸爸,我一向信服你,但你也跟大部分人一样,总对肉体带着居高临下的蔑视,偶尔妈妈到商店试穿新衣,你会在旁边强调:再宽松一些,不能太紧。哦,这裙子,太短,你不能穿……有一阵子,当我吊在门框上训练肌肉,你没有明显表示反对,却另找机会跟我说什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你从来都轻视一切身体上的能力,我短跑全年级第一、跳高得满分、冬天不穿棉袄,这些我认为很了不起很值得自豪的一切,你连个微笑都不给,那潜台词是明显的……
好在,你不反对我学画画,似乎这是特别正当特别高雅的业余爱好。你甚至很喜悦,以为发现了我的大才能与大潜力,高兴地请美术系的年轻助教辅导我,并替我买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和《艺术哲学》。这两本书也不坏,特别是后面一本,我这才知道,对肉体的迷恋,不止我一人,也不是自我始,在雅典与古罗马,所有的公民都疯了一样地喜欢健硕丰满的人体。那是集体性的崇拜与把玩,他们公开地进行研究与琢磨,在公共澡堂里彼此欣赏或暗中妒忌。哦,肉体、肉感、*,那是他们所有生活的关键词!
爸爸,我这条命真是生错了,所以也真活该去死!若能重新投胎、若能时光回转,我能生在落后无知的古罗马城邦就好了,哪怕就是个一无所有的奴隶,那也是伺候漂亮肉体的奴隶!
扯得远了些,只因从未跟你说过这些。哈哈,要是我还活着,也决不会跟你谈起这些。不仅仅因为你太正经了,而是在父子之间永远都不会这样谈话。我问过我的那些同学们,任何关于性的话题,在所有的家庭都是陷阱和禁忌。多么纯洁的八十年代,活该我要因为下流而死去。
——但如今你可以知道,关于我与肉体的关系,那种一见如故、性命相抵的意思,肉体就是我的真理,我对它的追求终身不渝,直至我为它而死……
儿子的房间(1)
' 1 '
晚饭后,陆仲生决定到儿子房里去——如果关于未知的追问,算得上是一个漫长的旅程的话,这可以理解为他的第一小步。瞒着妻子蓝英,陆教授暗中决定,像对待一个机密的科研课题,他要查清楚一切的未知,先从儿子的遗物开始,寻找任何蛛丝马迹……
不过,这还是儿子走后,他头一次走进他的房间。距3月27日已经一个月有余,他天天打定主意进去,却始终打不开那道门。旁人可能永远无法感知,迈出那一步需要多少勇气,需要让心肠变得多么硬!
其实,所谓儿子的房间,那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房间,只是把一个带拐角的西晒阳台改装了一下而已。有床,有书桌,有储物柜,有可以从里面锁起来的门。总共四十五个平方的教工公寓,给儿子这么一个空间,已是不错了。
我今天晒了被子的。太阳好得不得了,不晒就可惜了。蓝英突然跟在身后说。这时,陆仲生的手正放在阳台房门口的把手上。她的话像小石子,猛然扔过来,又突然掉下来。陆仲生清楚那小石子落下的弧度,像妻子没有说出的后半句话:咱丹青从小就顶喜欢闻被窝里的太阳味儿……
是的,蓝英还是不肯直接提起“丹青”的名字。
这情形同样开始于3月27日。突然之间,从原先的悲痛欲绝、呼天抢地之中,她冷淡起来,绝口不提关于丹青的任何事情,好像她从未有过儿子,故而也谈不上失去,更谈不上伤心或绝望。生活中的每个环节,她都高超而巧妙地绕着圈子,如在起伏的风浪中驾驶着孤舟,避开可能触及儿子的一切暗礁……
这样,她的语言体系开始呈现出两种相反的状态:要么,她大音希声,谨慎地抿着双唇,除了必要的对话,她机警而严格地看守自己的声带——这种状态里的她,特别的高深莫测,连陆仲生都有些望而生畏。要么,她跳向另一个极端,语言如火山,在某一个点上破坏性地爆发,爆发点毫无规律,譬如一块油腻的抹布,譬如过咸的菜汤,譬如电视里的一个新闻节目,如同饥者找到一块面包,她都会一下子咬住不放,追古抚今地连续说上一两个钟点。不用说,那情形有些可怕,陆仲生只得围着她应答不已,浑身却感到一阵阵的寒凉。
今天,她可能刚好处于后一种体系。方才的第一句话、先扔过来的小石子,只是个引子,接着,她给陆仲生扭开了一长串关于晒被子的话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