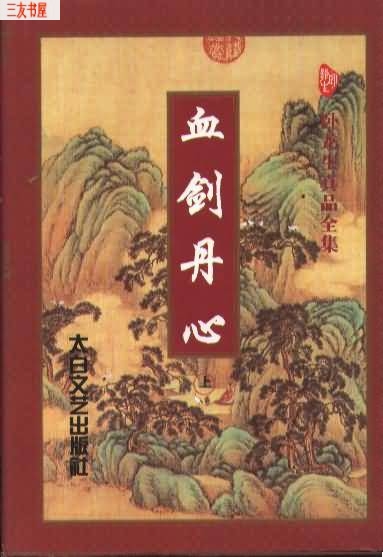赤胆丹心-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师和天雄赶去,再看那船时,却是一条载客短程航船,那妇人乃系中途搭客,连船上人也不知姓名来历,只有又回来。这时邻近各船及岸上商民已经惊醒好多,那火光已熄,毒烟也散,外面反而喧嚷起来。那妇人们入小巷之后,原本藏身在一家墙角后面,一听河下一片人声,哪敢再出来。转从那条小巷,绕向正街,在一家客栈门前停了下来,那店门半掩着,内面一个小二打扮的人,连忙将那妇人放入,将门又关上,一面道:“太师母得手吗?外面只听人声噪杂咧。”
那妇人跺了一脚摇头道:“不但没有能得手,我又受了伤咧。”
原来那妇人正是秦岭下来的孟三婆婆改扮,只因前在微山湖,水火夹攻之计未能用上,转将闻道玄变成了独臂道人,又折两代四个得力门下弟子,不由忿恨欲死。偏那任大鹏、梁五两人,因黄坤被擒,又埋怨她事前没有布置好,一定是门下弟子如殷七等人出言不慎,致将机密泄漏,才被敌人有了准备。虽然后来黄坤逃回,未曾丧命,但彼此一阵争吵之后,闹了一个不欢而散。那孟三婆婆和闻道玄只剩下二人越发把了因大师、鱼家父女和马天雄等人恨如澈骨。但和任大鹏等三人分道扬镳之后,人手愈感不足。因此虽然尾追了几天却不敢再下手。后来二人一商量,想起德州城外,河堆附近街上,孟三婆婆姘夫窦飞虎有一个侄儿窦胜和闻道玄的师弟刁良两人合开着一家客店,不妨暂住,先让闻道玄养伤,再徐图报复。
所以换了一条轻快小船,加速赶到德州住了下来。那窦胜刁良一见婶母师兄来到自是竭诚招待。孟三婆将闻道玄安顿之后,心终不死。又在当地配了一种特制火弹,化装一个村妇,从德州迎了下来,恰好才赶出三五十里,便自遇上。那官船和鱼老的船虽然易认,但她因吃过了因大师的大亏,哪敢露面。
只有搭一只开往德州的航船,尾辍着。
等到了德州以后,又因鱼老那条船,泊在内档靠着岸,那是必经之路,一直等到夜静更深才偷偷的下船,原想这一来人不知、鬼不觉,必能得手无疑。却没想到正好遇上天雄,不但未能如愿,反将自己半边身子烧伤了好几处。那小二原是窦胜徒弟,所以也叫她太师母,先在暗处还不甚显眼,等走到柜前灯下一看,只见她右腿、右臂、衣服全已烧破,灰土血污连成一片,连脸上也被灼伤,闹了好几个流浆大泡,不由叫声啊哟,一面道:“那姓鱼的娘们和了因老贼秃也会使这个吗?你这个伤可受得不轻。”
孟三婆婆把牙一咬道:“这用不着你问,你只把你师父找来便行咧。”
说着,便走向自己所居跨院,颓然躺在炕上,那窦胜刁良两人原因外面喧嚷,赶了出去查看。半晌方才回来,一见伤势,忙由窦胜替她用剪刀将破衣剪开,洗净用自己秘制好药敷上包扎好了。那闻道玄得讯也挣着走来,一问情形,不由对了因大师这一干人更恨如澈骨,依着窦胜和刁良两人,本打算齐集附近羽党,再往报仇,闻道玄忙道:“以我和你婶母尚且不行,何况你两个。如今只有等我们伤好,到京再做道理。反正我们和他武当少林两派已经势不两立,既要报仇,何争此一时一刻。这些人既到北京城去,一定全在雍王府,一时决不至他去,还愁没有法子找他们算回这本帐吗?如今你二人可暂时不必声张,也不得轻举妄动,只等我和你婶母伤势痊愈再说。”
孟三婆婆冷笑一声道:“这次我们算是栽到家了,再打算在路上动手已经无望,那只有到京再说,反正我那侄儿侯异,命丧在雍王府,那云中凤又将向成一身功夫破去,此仇也非报不可,好便好,不好,索性在北京城我们再闹一个大的。不过我们带来两代四个得力徒弟,全丧在鱼翠娘那贱人手中,闻贤弟又成了残疾,我只一人,却委实孤掌难鸣,真要说到动手,能制那了因和尚的人还不多,这还得设法才好。”
闻道玄看着那一条断臂,不由长叹一声道:“我真想不到,这丫头竟如此厉害,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我真懊悔,从前没有能多在真实功夫上下力,全仗毒药暗器取胜,一经遇上行家便全用不上。黄河渡口一败,虽然自知不济,埋头苦练,但真正内家工夫,已经无法登峰造极,所以又有此失。那鱼翠娘后辈晚出尚且如此,了因老贼秃这几十年来,决也不会把功夫放下,那便更难敌了,如要制他,除少林的哑尼道朗、铁樵老和尚、武当的独臂老尼等有限几人而外,恐怕已经寥寥无几了。”
那刁良在旁忙道:“师父不必难受,难道除了少林武当这几个人而外,这老贼秃真就无人能敌不成?你老人家不是说过雷太师叔的内家功夫已到骨软如绵,寒暑不侵的境界,便少林武当两派长老也难胜过他老人家吗?如今他便在这德州城内三仙祠修真养性,徒弟虽也去过两趟,但他老人家却托言坐关,不允相见,你如果能去请他老人家出来,这仇不也就可报了吗?”
闻道玄半晌不语,把头连摇道:“他虽是我师叔,但向来性情古怪,只恐求也无益,如今还只有由你到秦岭去一趟,禀明你三位师叔,命他们到此地聚齐再做商量,此外再无别法咧。”
孟三婆婆忙道:“刁良方才说的是雷春庭雷老前辈吗?他既然是贤弟的师叔,你为什么不去请他一下?这位老人家昔年曾有霹雳手之称,如果他真能出手却不愁了因贼秃不甘拜下风咧。”
闻道玄又长叹一声道:“他不但是我师叔,我的那点内家功夫,还大半是他教出来的,但因我和你相识以来,便断了往来。黄河一败之后,他更力加规戒,绝不许与了因贼秃为仇。
如今再找他去,只有落得一场训斥,弄巧了也许今后动手反更为难,那是何苦咧?”
孟三婆婆不由默然,只有又商量了一会,仍命刁良回秦岭去报讯约人不提。
在另一方面,天雄等一行,经过这场虚惊之后,戒备愈严。
等到通州坝起旱到京,已是年残岁底,曹连升自向雍王府投书,点交妆奁,内务府交送贡品。那鱼老父女和曾静、了因大师四人也自先向周路二人京寓前去。天雄却单独奔年宅而来,才到宅前,便见魏景耀迎着笑脸道:“马爷,您这一趟多辛苦咧,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雍王爷和羹二爷已经天天在盼望,连人全派出两三起,您遇上没有?如今二爷吉期已过,这喜酒您却没能赶上咧。”
天雄不由一怔,忙道:“那位云小姐已经过门了吗?那我真误事咧。”
魏景耀未及答言,忽从门内闪出一个二十来岁的白皙少年来笑道:“这位便是马天雄马爷吗?您别听他的,羹二奶奶虽然已经过门,云小姐的吉期,却在明年元宵,您不但一点儿没有误事,奇Qīsūu。сom书回来也正是时候,二爷和那位白大侠现在花厅外书房,正在惦记您,您快随我来吧。”
天雄一见那少年,虽是一脸机伶之色,人却没见过,忙道:“你是谁,怎么我不认识咧?”
那少年请了一个安笑道:“奴才叫喜儿,您到南边去,奴才才到府里来,您当然不会认识,如今奴才是专伺候二爷的,您快来吧。”
那魏景耀连忙笑道:“我本来说的是羹二奶奶,并没有说云小姐,也并没有错呀,你怎么这等说法?须知羹二奶奶到底是正室夫人,那云小姐便再由王爷做主,却只能说是纳妾,不能说是完婚咧。”
说罢便搭讪着走去,这里周再兴领着天雄径向花厅外书房而来,人才到花厅外面,院落当中,周再兴便高声道:“回二爷和白大侠,那位马天雄马老爷已由江南回来咧。”
羹尧和白泰官二人正在谈着天雄迟迟未到的事,深恐程子云又在中途弄鬼,一听人已到京不由均各大喜,一齐迎了出来,羹尧首先拱手笑道:“马兄此番南下,不但跋涉辛苦,而且因此又受重伤,小弟实在于心难安之至,幸喜诸事均仗大力,得以成功,小弟只有铭之心版,容我慢慢答谢了。”
白泰官也笑道:“马兄怎么迟到今日才能回京,是路上又出了什么事吗?”
说罢相携入室,一同落座,天雄道贺、寒喧之后,也笑道:“年兄未免太言重了,小弟此行虽未辱命,但也惹出若干事故来,除赶回吃你与云小姐的喜酒尚未误期而外,还有若干事须待商榷咧。”
说着,看了周再兴一眼,又道:“说来话长,少时容再细呈便了。”
泰官向室外一探首,哈哈大笑道:“马兄有话但说无妨,自小弟来此下榻之后,这花厅上年贤侄便已吩咐过,不许外人擅入,这喜儿你别看他是个书僮,其实却也是肯堂先生入室弟子,复明堂上得力人员咧。”
说着又将周再兴来历匆匆一说,天雄不由一怔,忙又向周再兴看了一眼,把手一拱道:
“原来周兄也是自己人,并且还和年兄是同门师弟兄,适才小弟不知还望恕我唐突才好。”
周再兴连忙还礼,一面笑道:“马爷,您不必如此,我既奉命在此地伺候年师兄,便应视同厮养才好,要不然被人看破反为不妥,便年师兄和白师叔也是如此。”
接着又笑道:“闻得您和鱼老将军已经认了世交,他父女小弟也极熟,有事弟子服其劳,我便伺候您不也是应该的吗?”
天雄又谦逊再三,方将中途所遭一一说明,泰官大笑道:“原来路上还有这等周折,那曹寅这老奴才,便又弄巧成拙咧。”
羹尧忙又问了因大师等人下榻何所,打算什么时候去见雍王,白泰官笑道:“此事你了因大师伯必与周路二公有所商榷,他们自有决定,倒是那鱼翠娘,对你和凤丫头的事,颇为不平。她又性子极急,一个不巧,也许今晚就要去向她大兴问罪之师,这却未免太煞风景。
便在雍王府稍露行迹也不好,马兄新归,你们不妨多谈一会,容我且携周贤侄一行,先拦住她才好。”
说罢便起身告辞,携了周再兴径去,这里羹尧一看天色已近黄昏,便命备酒与天雄洗尘,各话别后经过,羹尧慨然道:“马兄此行,所关极大,小弟固所深感,如能因此创出一个新局面来,也不负你这番辛苦。”
说着又道:“老伯大人的事,刑部已接川中来文,据称自到戍所,便自失踪,不知下落,如依小弟揣测,也许他老人家雄心犹在,或者脱身他去,另有所图亦未可知。连日雍邸均谓来年小弟或可外放学政。他的意思,本拟着我到江南去,但小弟之意却在甘陕川中。一则边陲较易布置,打算借此稍有建树。
二则江南既有长公主和诸位老前辈在彼,小弟前往,也反多顾忌。所以一再和他说明,托言秦陇川中关塞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如欲与诸王以争天下,必须先机占有不可,他已答应,事如可成,马兄还请随行,小弟必以全力代为打探下落,以全孝思。”
天雄不禁避席下拜道:“小弟得蒙知遇于泥涂之中,已是终身感戴,若再如此成全,只要能容我与老父见一面,敢惜此身以图报于万一。”
羹尧也慌忙答拜道:“如今弟与马兄除已成生死不易之交而外,还有许多大事要共,你为何又以这等大礼相加,不折杀我吗?”
天雄慨然道:“小弟素性耿直,既蒙以知己相待,决不敢再以世俗之礼相见,但既为老父如此成全便不得不尔咧。”
说着,两眼隐泛泪光道:“小弟国破家亡之后,生死皆不足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