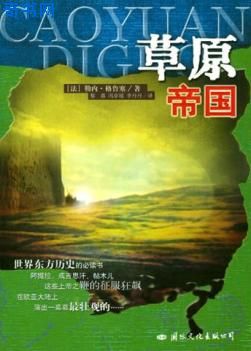��ƽԭ-��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Ϻ����Ǹ�����ãã���糿�����˸ߴ壬̤��ȥ����ɽ���ѵ�·����˵�����ӵ��¾���·����ֻҪ���ſڣ�����µ�·�����С���һ���˹��ѳǣ�����ˮ�������ǣ������ſڣ�������̲������һ�����պյĴ�ɽ����������ǰ������ǻ���ɽ�ˡ�
�����������պյĴ�ɽ����μ��ƽԭ�ľ�ͷ�����±���ԭ�Ŀ�ͷ���������ٻ������һ����ʮ���ﳤ�����������µ��Ǹ���������ɽ���ߴ��վ���Ϊԭʼɭ�������ǡ�
�����ڹ�������û����ƺӻ��������֮ǰ������ɽ��������һ����������ֻ��ס���������˼ң���һ��һ�ѵ����ˣ�������ɽ���룬�Ǹ��dz滢����û�����硣
�����������ԭ��ƽԭ������ңԶ�������˿��ܼ���Ҳ����ңԶ����ô������γ�Ϊ���������أ�����ݵ��峯ͬ�������һ��ɧ�ҡ�
�������Ǹ��������������������˳���±���ԭ��һ����������������ӣ�һ·��ɱ�����������±���ԭ������������ͳ�죬һ����������һ��������������������ķ�ˮ�����������������߱�����������£�˳���������Ӵ���һ·��ɱ���¡���Զ��ԣ����������ܵ����ֺ�����һ�㣬�����������ɧ�ҹ������ϳ�Ϊ��������
�������������˶��������Ѿ������ˣ���ʱ������������һ�����ꡣ����ƮƮ����������������������ˣ���������͵������ˡ���������һ�����ٻ��﷽Բ�ĵ��棬�ͳ��ػ�����������������ؽ��磬�˸����ֶ��ܲ���������˳�Ϊһ���첻�յز��ܵĵط���
���������������ƶ�˵����һ������С����ꡱ����һ�ֿ����ʱ������˿��У�Ȼ����������һ���䵽�˵��档��ô�Ǻ���ɫ�ġ������ʡ���ʲô�أ���Ϊ�����Զ�������Ѿ���֪���ˡ�
����������һ����棬Ϊ���ݺ����Ļ��ھ��ڵ������ṩ�����֮�ء����߷����Ϻ��Ķ��ֳ�̤�����ɽ����ʱ���ǿ�����Ѿ�����������Ļƺӻ��ڵ������ߡ���Щ�����߰�������ǰ���ᵽ���ǻ������˼ҡ�
������Щ��������һ����ʯ����ĵط��Ǽǣ�Ȼ��㱻��ɢ�����ܵ�ɽ����ȥ�������������˸��ֵ����أ���ï�ܵ�ԭʼɭ�ֺʹ����֣�˭�����Ļĵؾ���˭�ġ�����ʮ�ַ��֣�һ����������ȥ��������������������������ˡ�
�������Ϻ�����Щ�ƺӻ��ڵ������߳�ȥ�˰��ꡣ��ͬ��������ʯ����������Ǽǡ�����������Ѿ������С����ξ֡������ξ���ʲô��˼�أ���Ҷ���̫���ס����������ξֵ���Ҳû��̫���Ѹ��Ϻ�һ�ң������ǵǼ���ᣬȻ��ָ��ǽ�ϵ�һ�Ŵ��ͼ��˵������ط��С������������������ߣ��а���Ҥ�����Ǿ͵�����Ҥ���Ұɣ�
�������Ϻ��������һλ���Ϸ����Ĺ����˼ң��Ǵ��ϵ��ģ�������������ھӡ����ξֵ������˸������ῴ�˿������ͷ���˵�����Լ��Ұɣ���Լ����������һ���ġ�
�������Ϻ���˵����˵�������������ѵģ�һ�˷�������ҷѣ���֪�������Dz�����ġ����ξֵ���˵������ȥ����ϻ����ˣ�����ָij����ξ��Ժ�����Ѿ�û���ˡ�
�������������Ϻ�̾Ϣһ����ֻ�����ա�������ȫ�ң����ֳ�֨֨ѽѽ�أ�һ����һ���ʣ���ʼ���Ǹ��С��������ĵط��ϡ�
����çç�ԲԵĻ���ɽ������һ��Ѥ�õĺ�ɫ֮�У�����Щ���米����������һ����õĸо����Ǽ����������죬������˪�����ر��ϵ����е���ɫ��Ⱦ���˺�ɫ�����а��������ޣ��������ͷ��Ŀѣ����ԭ���������£���ʾ���ۺ졢�Һ졢�Ϻ졢筺졢õ��졢��ɰ����ɫ��Ρ��ߴ�������������ɽ���桢����������������������ɽ�����������ɽ���䣬������ʰ�֦������һ����Ҷ���·��¼��ﶥ��һ�����ͷ����Ȼ�����������Щ�����ڵر��ϵ�ľ�����������������ѣ�ǧ�˰�̬��˳��ɽ��ˮ�ƣ�����һ����һ������ͷ����ľ�����У���һ�ֽ�������ģ�֦ͷ�Ϸ���һ��һ����һ��һ���Ĺ�ʵ�����ӣ��һ��������Щɽ�������������µ�ׯ�ڣ������ϵ�ëë�ݡ���ݣ�Ҳ�����������������Ϳ�Ϻ�����һ�����������ʺ�ɫ��
������Ҷ�¸�����һ��һ���ʬ�塣���ǵ���Щ�����ˣ���Щ�ƺӻ��ڵ������ߣ��ڻ���ɽͻȻһ��һ����������һ��һ�ҵ�������һ��һ���������ʱ�����Dz�֪����һ�㣬������Ϊʲô����һ��õط�����Ȼ���ţ�רΪ���Ƕ�����
��������Ȼ������裬�����������ôһ���õط����ţ����������ģ��ƺ�����Ϊ��һ������ķس�����������������Ⱥһ����ѡ������һ��ط���Ϊ��Щ�����ߵ������ޣ���Ϊ��һ��������ײ�Ļȳ�һ���Ļ������Ѵ�����ս�أ�ȴҲ����ν��ǡ����
����Ҳ�������Ǽ�ȡ����ȡ֮���ߵ����ϣ���Щ��Ҷ�Ż�������ޡ��ǵģ��ն�Ļ���ɽ������һֻ����Ѫ���ڣ�����������������صȴ�����Щ�����ߡ�������ʱ���ǻ���֪������һƬѤ�õ������������Ի�
����ȷʵ����������ŵ�����������ֳɵķ��ݣ����ֳɵ�ũ�ߡ����֣�����Щ����������Ԥ���ģ�������Щ�����Ƕ������������µġ�����ɽ����Щ��ס���ǣ���ס��һ��ʱ���Ժ㿪ʼ˵һ����ҥ����仰ǰ���С�����ɽ���ˡ�������С�����ɽ��ɱ�ˡ���
����������ɽ���ˣ��������ȴ������棬������������׳�����������������ʱ�����ǻ�����˵������һ�ֽС����������ļ�����ʼ��Ű��һ��һ����һ��һ���������̼������ʱ������������ǰ���ֻ�˵��������ɽ��ɱ�ˡ���仰��
����������������ѧ�����ǻ��ҡ����ֲ�һ��������������к�����������������û���ˡ���˵���ֲ��ܹ֣���Ҫ�뿪����ɽ����Ͽ�̧���ߣ�Ҫô�������ϳ�һ�ٷ������߸�һ���صأ�ͻȻ����Ķ��Ӿ���������ͷ���麹ֱð�����ž���������к��һʱ���̣���С����û���ˡ�
����μ�Ӱ���Ư����������һ�������˼ң���ס�ڻ���ɽһ���а���Ҥ�ĵط������ǻ��������Ĺ����˼ң�ס��һ���а������ĵط���
�����⻧�����˼��������㣬�ڻ���ɽס��ʮ�ꡣ���Ǻ����ˣ��Ǹ��С����������Ĺ���һ���Ķ�����ʼ��û���䵽����ͷ�ϡ��⻧�˼�ȥ����ɽ��ʱ���Ǽ����ˣ�����ʱ���Ǽ����ˡ���ͬ���ǣ�������ʱ����Ⱥ�����˸��ж��߶������˸�ͯ��ϱ�����ӡ��Ǹ߶��Ǵӻ���ɽ�μӸ������ˡ��������������ȫ�Ҷ����ڡ���������֮����������ͯ��ϱ��
�����������˼Ҿ�û����ô�����ˣ�����һ��һ���ض�Ⱦ���ˡ�����������Ȼ�������˻���ɽ��
����������õ�txt������
��ʮ���¡�����һ�ҵ�����
�������Ĺ��ڻ���ɽ�Ĺ��£���ԼӦ������ĸ�������������������ӵ��۾�������������¡��������»����������۾���������۾�������ӣ���ò��������ۿ��ˡ���Ȼ��Ŀ����Ҫ������Ϊ�����������ͯ��ϱ��Ե�ʡ��ǵö�����������һ��С˵�У������ᵽ�������Ů��������ͯ��ϱ��Ŀ�⡱��仰�������Ķ�ʱ����仰����һ�̴������ң�����������ĸ�������������������ۿ��˵�Ŀ�⡣
��������Ҥ��һ����ɽ�ϣ����������һ���������������������һ��СС�ļ��������ұ���һ��С�ӣ��Ǻӽл����ӡ�������ҥ˵�������˻����ӣ�������ɡ���˵�ľ��������ӡ�
����һ������ɽ·���Ӱ���Ҥס����Ҥ�����ϴ���ȥ������·����һͷ������������ʯ����Ȼ��ͨ��ɽ�⡣��һͷ�����������ӣ�����������i᭣���һ�����崨�ĵط����˴�·��
������үү����һ�У��������ڰ���Ҥ��������������Ҥ�����ֳɵģ�˳��һ�����ɽ�£�����һ����ĺڿ�����ֻҪ��ɽ�Ͽ�����ľ�������Ŵ������ðҽ�ǽ��һ�ۣ��Ϳ���ס���ˡ�
����������Ҫ����������ʱ������Ҥ���ᄍȻ�й������Ѿ������ˣ������ӱ�ȥ��ʯͷ��һ�����������á�����������������������ֵ�ʱ������Ҥ���IJ��棬һ�ô������棬��Ȼ��һ�̴�������������ţ�������ר��Ϊ����Ԥ�����Ƶġ�������������ɽҰ������һƬ��Ϊƽ�������أ�������ͷ����ʱ��һ��ͷ��ȥ����Ȼ�ٳ�һ����������Ƭ����
��������Ƭ��С��װ�����ȣ������ӣ�ר������ɽ����ʹ�á�����������Ƭԭ����ͬ���ȣ���һ����ڵ���ġ����������ȵ�ľ�ʲ������ˣ�����ֻʣ����Ƭ��
�������չ֣���Щ��������ר��Ϊ���ǰ��ҹ�����Ԥ�����Ƶģ���үү��Щ�����˵��
�����������죬�⻧�˼�������������������ˡ�
����үү����ȥ�����ϼ���ʱ������λ��������żȻ����ġ������ǹ�������һ���棬�������ȣ��е���������֪�ĸо�����һ��С�ƹݣ����Ǻ��˼��ھ��Ժ�̸�������ҽ������顣
�����ҵĵ����������ϴ��Ѿ���Ȣ��������С����ˣ�������Ӿ�����ʯ�嶷���ȵ����ۣ�˵���˸߶�����λ˵�ã��ȵ�������ʮ���������ơ����˾�ÿ������ʮ�壬�������͵�����һֱ�͵�ʮ���ꡣʮ�������һ�Σ��С���ơ�����ʾ�˾˵ļ�������⺢���Ѿ����ˡ�����ơ�����ϰ�״�Լ��Դ���л��������ʱ�ڵ����֡��ɶ����Ժұ���Ȣ����������֮ǰ�������Ƚ�Ϊ�����߶������ݡ�
������������Ǹ������������������ӽ����Ǹ��а������ĵط�������ʮ���꣬Ȼ�����һ���������糿����һƥ����켸�����ţ�����ë¿��������Ҥ����Ϊ����Ҥ�⻧�˼ҵ�ϱ����
���������㲻���������㡣���������������Ӷ��������������ˡ��������Ҳ�������⻧�����˼ҡ����Ǽ���ļ����к����ˡ�����һ���������Ȳ�һ�������͵���ɽ�ϡ����ţ������ӵ�ĸ��ҲȾ�����ⲡ��
�����ӵ���Ϣ����үү�������̸ϵ��˰�����������ĸ��ĸ���ؽ��ţ��������ᣬ�������ؿ�������������ȥ��
���������ӵ�ĸ��������֮�ʣ�ͻȻ���ѡ�
��������ΡΡ��������������һ��ƽ����Ь���õ������룬Ȼ�������͵��Ƕ���״�Ļ����£�������պ졣
������������������Ҽǵ������ѵ�·�ϣ���˵������������ˣ���Ҫ���������������ۡ�����Ҫ���������������Ҳ���и���������Ļ���ģ���
���������ӵ�ĸ��˵��
���������ӿ��ţ���ͷ�չ�ȥ����ĸ������
����ֻ�����ۡ���һ�����̣������봩���˹����ӵĶ�������
�����������۵ý���һ����
���������ӽ����ֽ���һ����
����ǰһ������Ϊ�ۣ����һ������Ϊ������ĸ���Ѿ�˫��һ�գ�ͷһƫ�����ˡ�
����һ���ݽ�һ��������һ���������������������ˡ�
�������е�������������ȥ�ޡ��������������������Ϊ��ľ�ˡ�֪��Ⱦ�����������Ͳ��ܻ��ˣ����Դ�Ҷ��и�˼���������ң���ɽ����춼�����ˡ�
����ֻ���ǹ������ˣ����ڵ��ϣ�����ץ��ͷ����������̾Ϣ��һ�������Ҵ������ǻ�ȫ��һ���ˣ��벻��������һ��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