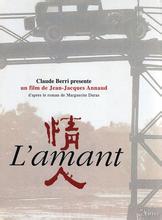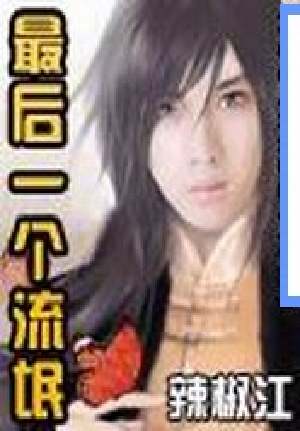一个小女人的常春藤之旅-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考试不是要我简单重复案例的既有事实,而是要考查我怎么理解潜在规则,并把这些规则运用到新情况中。这种有深度的考试是要让我自己去发现问题,从而把一学期的知识串起来,自己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可能会问我怎样综合理解一些概念(假设都是学过的),然后怎样把这些概念运用到全新的情形中,以测验我对法律和政策的掌握情况。
第四章 恐惧厌恶综合症(4)
举个例子,合同法考试中,我知道不可能要求我叙述露西诉齐默案的事实,或者让我判断“在统一商法下,承诺中增加了要约没有的条款是有效的”这句话的正误。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堆复杂的事实,然后是冗长的问题等着我回答:合同有效吗?要约的内容明确、具体,有约束力吗?承诺是否以适当的方式作出?这些条款都有约束力吗?抛开实际因素,允许禁反言或不利依赖吗?有哪些防御措施?如果合同有效,条款是什么?这些条款都应该被履行吗?先履行、同时履行、后履行的满足条件是什么,违反了怎么办?合同解除、履行、更新、情势变更、违法或违反合同目的吗?如果违约了,有哪些正当的救济措施(期望损失赔偿、相应损失赔偿、违约赔偿金或实际履行)?
这些问题大多数我都不太懂,更别提把它们记下来,并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运用到奇奇怪怪的事实中。我只要一想到接下来的五周时间,我必须全面学习并深刻理解合同法、侵权法、民事诉讼法,就不可控制地陷入恐慌。
显然不只我一个人这么难受。焦虑似乎有传染性,大家一过完感恩节就立刻返校,不管准备得怎么样了,每个人都立即进入紧急状态。作为一个团体,我们班真的好恐怖——没有人睡觉,我们都是黑眼圈。我们每天从乱糟糟的床上爬起来——床上扔有棒球帽、肮脏的衣裤,不修边幅、蓬乱着头发冲向九点钟的课堂——即使时尚人士这段时间也放弃了打理。咖啡柜前的队伍比平时长了三倍,教学楼前蜷缩的一小撮吸烟者膨化成一群名副其实的尼古丁学生(包括我——我又开始吸烟了,尽管我两年前已经戒掉了)。考试失败引起内讧或遭驱逐威胁的谣言四起,有时候你甚至能听到图书馆个人阅读座位上传来的低声抽泣声。
学期课程全部结束之前,教授会开个正式的复习会,回顾一下一学期课程里的重要概念以及向学生提问。涉及的话题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教学大纲上也没有。不变的是,总会有人举手回答这些挑剔、偏远、离奇的问题,显然其他人远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如果你对既判力还只是模糊认识时,听到前面的同学这样质问教授,你不可能不受刺激,“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互保抵押品不容反悔,在既判力下相当于私人之间的要求,这是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规则。您能回顾一下这项方针变迁背后的理论基础吗?”
这些复习会并没有减轻我们的恐慌。我坐在图书馆看书时,不时听到周围同学讨论我还没有开始复习的知识点(“那么,在UCC损害规则下,如果卖方违约并且还持有商品,那么对买方的救济,是发现违约时的市场价格减去原先的合同价格,还是替代物的价格减去合同价格)?我觉得我最好还是回家一个人复习,远离人群,唯一的竞争者就是我自己。
我收拾好东西,拖着疲惫的身体步行回家。我书桌上立刻堆满了一大沓复习资料,有商业纲要、入门书、课堂笔记、案例简介、案例书、重述以及各种颜色的荧光笔。我警告乔,如果他知道什么对他有好处就不要打扰我。为了给我留下宽敞的复习空间,他开始加班,业余时间就和我同学韦德在校园踢足球,韦德不知什么原因还没有陷入期末考试的疯狂中。乔回家后也是蹑手蹑脚地进卧室,经过我时,我冲他用力点点头,示意他保持安静,因为我还要继续学习。我极少离开公寓,除了上剩下的几节课外我都隐居在家,一上完课我就赶紧回家学习。这让我想起了追缉令,里面的赫德和福特逃到一家酒店完全隐藏起来,疯狂地准备他们的第一次考试。
第四章 恐惧厌恶综合症(5)
我基本上是从头开始,集中精力先学习侵权法,直到我把里面的知识点吃透,再也读不进去一个字时,我就开始学习合同法,然后是民事诉讼法。一门接一门,我重读每个案例简介,重读入门书和商业纲要,重读我的课堂笔记,然后再重读,直到我觉得全都理解了。我写下自己的提纲,把不同的知识点从逻辑上串起来,把案例背后的理念、规则列出来。然后把我的提纲压缩成小型提纲,只包括最核心的知识点。我还把复杂的知识点画成流程图,用箭头标记它们之间的关系,以便展示它们的相互作用。我还制作了巨大的符号列表,把分析考题的每一个步骤都列出来。最后,推开所有的资料,我拿以前的考题作模拟测试,当我做完后和教授提供的参考答案比较时,我吓得灵魂出窍。我知道还有好多东西要学,我又重新开始了。
与此同时,我几乎废寝忘食。我每天喝五大杯咖啡,像恶魔一样狂抽烟。我基本上没有食欲——咖啡因、尼古丁和压倒性的忧虑使我极度紧张、兴奋——仅仅想想食物就让我恶心。但是稍稍考虑到身体健康,我决定每天吃一两块巧克力,早上喝咖啡时加些维生素片。我的体重急速下降。当我每天凌晨两点左右,学到极限时,我就从书中抽出身来,但我发现自己无法入睡——很明显,咖啡因的后半夜作用强于前半夜——我只好喝杯酒,看看VH1台的无眠音乐剧场,放松一下。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后,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上床,还是很清醒,于是我躺在床上回忆我自己发明的记忆策略,以帮助我记住重要的法律要素。
什么样的案件是可裁判的?CRAMPS。(单词首字母缩写)诉由必须是具体的、成熟的、对抗性的,不是不相干的,不是政治问题,必须有立场。
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是什么?CARAT。(单词首字母缩写)起诉、答辩、回答反诉、回答交叉起诉,第三方起诉/答辩。
合同的抗辩有哪些?MUDIFIS。(单词首字母缩写)误解、不合情理、胁迫、非法、诈骗、丧失能力(是的,我知道“mudifis”不是一个单词,但是我不在乎啊)。
当我最终把这该死的记忆术清出脑海的时候,我开始后悔刚才看无眠音乐剧场了,因为贝克唱的“输家”歌词不停地在我脑中回旋(这是VH1台每晚必放的歌曲),最后我只好起床,开始学习。“我是一个失败的小孩……”
在我们疯狂的复习中,寒假悄然来临了。我相信即使再残酷的教授也会认为寒假后给法学院一年级学生几周的复习时间是应该的(高年级学生的课程一结束就开始考试,假期还没开始呢),可是我的个人经验证明,我整晚被纯粹的、十足的恐惧困扰,根本没有融入节日气氛中去。但是,我很早就计划,至少在新年前夜抛开书本,到韦德的公寓参加派对。我实在搞不懂他哪来的时间准备盛大派对——因为他和我在同一条船上。更糟糕的是,韦德平时就没有花多少时间学习,当我们夜以继日地学习,拼命想弄明白实际因素和近因的区别时,他和我丈夫每天一起踢足球,还吹嘘自己每天学习多少。
已经12月31号了,离我的民事诉讼法考试还有四天时间,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几乎办不到了。我算了一下,剩下还不到80小时完整的学习时间,我不敢想象我要牺牲这么宝贵的时间去参加派对,而不是用来记忆强制合并各方的相关规则。热闹的庆祝会开始前,我跟韦德打电话表示我的遗憾。这样的对话不可能愉快。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恐惧厌恶综合症(6)
“很抱歉,我今晚不能来参加聚会了。”我说。
“什么?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你的借口是什么?”他几乎叫喊起来。
“我很抱歉,韦德,我的借口是我现在已经濒临精神崩溃了,赖特和凯恩入门书上我还有350多页没有读呢,即使是在加农民事诉讼指南的帮助下,我还是不能理解附带司法管辖权的相关规则。”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停顿。他终于开口了,我很吃惊他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很同情我,而是纯粹的绝望,“但是,马莎,已经有很多人毁约了,这时我需要你来凑数。”
我至少还知道友情的珍贵。再说我也不是唯一背信弃义的人,我感到一些欣慰。我确实压力很大啊,我想没有多少法学院一年级学生会欢乐地迎接1995年的新年钟声。
“我想看会儿足球。”第二天下午乔说,他在电视机前重重地坐下,准备看大学生足球比赛。虽然不管怎么说他不能算胖人,但是我们老化的沙发在他坐下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哦,这件事……”
“不要告诉我你要学习。”
“是啊,你知道再过三天就要考第一门了。”
“我当然知道,我会忘记吗?”
“你不能去卧室看吗?”我辩解道,我的书桌、我的电脑、我的一大堆书、我的小小写字桌都在一个角落里,离起居室只有几步之遥,电视打开时我不可能集中注意力。
“马莎,卧室离你书桌只有四英尺,就算我看电视时把门关上,你也会叫我把声音调小。”
“对不起。”我说,我紧张不安地点燃一根烟,“我只是没法全神贯注。”我知道因为我在家学习使他的活动空间大大缩减,但我并不是不讲理,我只想奋起直追。说实话,想到我每天都要学习18个小时,而乔坐着啥也不干,我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公平。
“我明白,我懂。但我只是想看会儿足球,一个小时而已,也许还不到。有那么多问题吗?你就不能在图书馆学习吗?”他质问我,他的声音暴露了他压抑多时的挫折感。
“但是我在那里没有电脑啊,我的纲要都在电脑上。”我向他解释,“而且我讨厌拖着这么多书到处跑。”我朝着起居室的窗外吐出一口烟。如果我每个醒着的时刻都要学习,为什么不选择舒服一点的环境呢?
乔叹了一口气说,“不要用这种错误的方式,我发誓我最近感觉被这个家放逐出去了。我没在家里单独过——你认识到了吗?你从不离开。我一大早去工作的时候,你坐在你的书桌上。我晚上回家的时候你还在那儿,好像你没有动过一样,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还在原地。周末我都是蹑手蹑脚地经过你身边,因为你不能被打扰。我很抱歉你不能集中注意力,看到你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也很难过。我知道它的重要性,我不是不体谅你,但是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家,不是统统都归你。”
废话。虽然他说得很过分,但是有一点是对的,不管是从严格意义上,还是表面意义上,我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我把在法学院的抱负作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把我的书桌放在小小公寓的中心。乔随我几乎穿越了整个美国搬到这里,我却不让他看一个小时的足球。法学院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几乎没有关注我丈夫了。上帝,我感觉我只有两英寸高。
“乔,你说得对。”我说,我的眼泪要夺眶而出了,“对不起,我其实不是一个疯狂的人——我只是在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