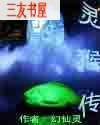达·芬奇传-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尔的修道院的修道士们那里租借的。修道院的记录显示,租借期从1449年开始,到1453年,可能就是他结婚那年中止。1469年这家石灰窑又被塞尔?皮耶罗?达?芬奇租借,他可能是代表阿卡塔布里加所借。今天,在莫卡塔利还有一处小的工业地产,但已相当破败。
阿卡塔布里加的家族,布蒂一家,祖祖辈辈几代人都在坎波泽比这片土地上耕耘生活。这片土地就位于芬奇镇以西不远的芬奇河边,属圣潘塔莱奥尼牧区管辖。布蒂家拥有自己的土地,比佃户地位高,但是其收入仅够维持生计。从地籍册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家族在15世纪经济呈下滑的趋势。卡泰丽娜和丈夫就生活在这里,可能带着达?芬奇家当时给她的一些嫁妆,并且一直在此生活了几十年。婴儿时的列奥纳多可能与她一起生活,但是这一点不能十分肯定。在1457年的地籍册中,列奥纳多被列为达?芬奇家庭中的一员,但这是出于经济原因——作为税收返还人口,他每年值200弗罗林金币——所以这可能说明不了这种情况的真实性。伯克利主教曾说过,可能性是生活中的伟大向导,尽管对于传记作者而言这不是金玉良言,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相当有说服力。它告诉我们,列奥纳多早年很多时间都在坎波泽比度过,得到母亲的照顾。河边山脊下这片蓬乱的农舍在列奥纳多孩童时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像是芬奇镇或者是传统上所说的但是不明确的出生地安奇亚诺村一样。塞尔?皮耶罗和他的妻子,公证人的女儿,阿尔比拉?迪?乔瓦尼?阿马多里,生活在佛罗伦萨。她是列奥纳多城里的继母,阿卡塔布里加就是他乡下的继父。他童年的感情轨迹已经相当复杂。
卡泰丽娜(2)
1454年左右,列奥纳多两岁时,卡泰丽娜生了一个女儿,洗礼时取名为皮耶拉,这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惊恐。难道是与塞尔?皮耶罗失恋后作出的回应?可能不是。这个女孩儿是按照传统以阿卡塔布里加的母亲的名字命名的,阿卡塔布里加的母亲在税收簿中登记为“蒙娜?皮耶拉”。1457年,第二个女儿玛丽亚降生。1459年10月15日的地籍册对这个家庭作了简短的记述:阿卡塔布里加和他的妻子“蒙娜?卡泰丽娜”;皮耶拉,5岁;玛丽亚,2岁。他们和阿卡塔布里加的父亲皮耶罗,继母安东尼娅,哥哥雅科博,嫂子菲奥里;以及侄女和侄子莉萨、西蒙和婴儿米歇尔一起生活在坎波泽比。他们居住的房子价值10弗罗林,土地值60弗罗林。土地部分耕种,部分荒弃,每年收获5浦式耳谷物,葡萄园每年产4桶葡萄酒。这些数字显示,他们在经济地位上要比达?芬奇家低很多。
紧接着又有三个孩子降生:莉萨贝特、弗朗西斯科和桑德拉。1463年桑德拉出生,在至此为止的11年里,卡泰丽娜总共生了六个孩子,五个婚生子无疑都是在坎波泽比村河对岸的圣潘塔莱奥尼牧区的小教堂里举行的洗礼仪式。现在这个小教堂已经年久失修,不再使用,只有鸽子们偶尔停在门廊的屋顶上抓来抓去玩耍嬉戏。卡泰丽娜惟一一个婚生儿子弗朗西斯科出生于1461年。他没有飞黄腾达起来:参了军,后来在比萨被弩炮射中而亡,时值30岁左右。
我们看一下在阿卡塔布里加身上发生的故事,那是1470年夏末的一天,这段经历或许正和他的绰号相符。那天他正在阿尔巴诺山和比萨群山之间的沼泽地马萨皮斯卡托亚玩耍娱乐。这一天是一个宗教假日——9月8日是圣母玛丽亚的生日——但是村子里的庆祝活动被一场战斗或是暴乱破坏了,几周后阿卡塔布里加作为目击证人之一参加了法庭质询。那天与他一起的有乔瓦尼?甘加兰迪,据记述是安奇亚诺村的一个橄榄压榨机的所有者和操作工人。这又一次让我们想到芬奇镇真是个小地方。
卡泰丽娜与安东尼奥?布蒂,又名阿卡塔布里加的婚姻开始就是一场功利性婚姻——对达?芬奇家来说是一场有利的婚姻,因为卡泰丽娜已经在社会上令他们家颇为尴尬;而对卡泰丽娜本人,这名失身又遭抛弃且正滑向赤贫的女子来说更是一场有利的婚姻。阿卡塔布里加与卡泰丽娜结婚可能有一定的金钱诱惑,也可能有与上流社会中的达?芬奇家有了某种联系而带来的潜在诱惑。阿卡塔布里加继续在达?芬奇家一些小商业贸易中扮演角色。1472年在芬奇镇,他作为证人见证了皮耶罗和弗朗西斯科?达?芬奇之间土地合同的签署。几年后他在佛罗伦萨又见证了由塞尔?皮耶罗公证的一次遗嘱案。反过来,弗朗西斯科?达?芬奇在1480年8月也给阿卡塔布里加作了一次见证人。当时阿卡塔布里加出售一小块与圣潘塔莱奥尼教堂毗邻的名为卡法乔的空地。购买者是李德尔斐家族,该家族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侵吞了布蒂家的很多土地。但是如果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是一场功利性婚姻,一个芬奇家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这场婚姻至少维持了很长时间并且收效甚好。在1487年的地籍册里,我们看到阿卡塔布里加和卡泰丽娜还生活在一起,还有他们五个孩子中的四个(玛丽亚要么结了婚到别处生活去了,要么可能已经死了)。据记载当时“蒙娜?卡泰丽娜”60岁:这是惟一一篇涉及到她出生日期的文献。布蒂家在坎波泽比的产业也由阿卡塔布里加和他的哥哥瓜分,每人分得一半房产,价值6弗罗林金币,还有5斗见方的土地。
我们对列奥纳多的继父,阿卡塔布里加了解不多,他在列奥纳多早年的生活中只是个朦胧的影子——可能比他自己的生身父亲和祖父还要模糊。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乡村的贫穷、手工劳作,还有“硬汉子”的粗鲁——等待着这位自己无法逃脱此命运的私生子降生。
阿卡塔布里加大约死于1490年,60岁出头。他死之后,卡泰丽娜的生活又出现了最后一场冒险——这是后面章节的内容。
“最初的记忆”(1)
列奥纳多最早的记忆明显不是他母亲,也不是他父亲,也不是其他什么人,而是一只鸟。几十年后,列奥纳多五十岁出头时,他写了一些有关鸟儿飞翔的说明——他著名的永恒的主题——特别是对尾部分叉的红鸢飞翔样式的说明。不知是什么东西触发了他的记忆,在页面的顶端,他写下了这样一段简短的话:
像这样特别写到鸢好像是我命中注定的,因为我儿时最早的记忆就好像是它。当我还在摇篮里时,一只鸢向我飞了过来,用它的尾巴敲开我的口,在我嘴唇之间拍打了多次。
这段奇怪的短文所写的是一段记忆还是一个幻想,长期以来人们争论不休。如果是一个幻想,那还将有争论——至少是列奥纳多精神问题研究的方面——看这到底属于他生命中的哪一部分。这真是来自他的童年吗?还是早些时候的一个梦或是噩梦,如此真切以至于现在看来像是一个真实的回忆?或是他成年时的一个幻想,投射在了他的童年时代?而这幻想与写这段短文时的列奥纳多(中年时的列奥纳多,大约1505年)的关系比与在摇篮时的婴儿关系更紧密吗?
芬奇镇上空,阿尔巴诺山上升气流中鸢展翅翱翔是常见的景象。今天如果运气好的话也可以看到。你绝不会把它们认错——长长的分叉的尾巴,优雅舒展而又略微拱起的翼展,翅末尾羽上浓密柔和的黄褐色在天空的映射下闪闪发光。这种鸟的轮廓和旋转飞行到英国转化成了人造的风筝,而在意大利它们被称为鹰。在所有猛禽中,鸢是最适应人类社会的:它们是食腐动物,野营的追随者。它们曾出现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这在莎翁的作品中可以证实。今天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城镇和乡村人们仍能觅其踪迹。在印度的英国军队称它们为“该死的鹰”。据英国放鹰捕猎者杰迈玛?帕里?琼斯所言,鸢“利用任何可能的时机捕捉食物”,“它们以俯冲下来从盘中偷取食物的习惯而著名。”最后这段评论表明,列奥纳多记忆中的事情完全有可能是真实经历。一只饥饿的鸢俯身猛冲下来以寻找小猎物,结果惊吓了摇篮中的婴儿。但是,这段记述中最奇怪和值得注意的部分——那只鸟把尾巴伸进了他的口中,而且还敲击他的嘴唇——这一点不太可能发生,因此这是幻想的一部分,是记忆中无意识的一个细节。
列奥纳多自己的话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虽然他把这段称为记忆,但是它本身就包含一种模糊的特质,表达了人们对早期记忆的一种不确定性,而且其不确定程度足以让人们认为这是杜撰出来的故事,而不是重拾起来的记忆。他最早的记忆是“好像是”一只鸢飞了下来,语气中带着点犹豫不决。他描述的是他头脑中十分强烈的东西,但是从理性方面而言却不是很清晰。他认为这发生了,但是又可能没有发生。在开头他已经用了“好像”这个词:研究鸢“好像是我命中注定的”。这里“命中注定”一词也颇有些意味,因为根据上下文判断它表明其含义有我们称之为“强迫”或“固定”的意思。他说是什么东西驱策他去研究这鸟,不断地去“特别”描写它。“命中注定”表明,这不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而是一些隐性的东西在起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列奥纳多关于鸢的想法正与他在1505年左右重新燃起的对人类飞行的兴趣紧密相连。现在珍藏于都灵的《飞鸟手抄本》的小抄本就是在那个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一句著名的声明:“这只大鸟将会从大切切诺山开始它的处女之行,世界会为此惊讶不已,它的芳名也将永垂历史,并给其诞生之地带去无上荣耀。”这大概是表明,列奥纳多当时正在计划让他的飞行器或“大鸟”从位于佛罗伦萨以北靠近菲耶索莱的切切雷山顶做一次尝试性飞行。抄本同一页还有一段话,记录匆匆,表明1505年列奥纳多正在菲耶索莱。所以当他全神贯注地思考人类飞翔的可能性时,这段有关鸢的记忆就涌进头脑,使得他正在思考的飞行有了个性化的渊源。当他还在摇篮里时,这只鸢飞翔而下,告诉他“命中注定”的东西。
第一次对列奥纳多鸢的幻想进行心理研究的是弗洛伊德1910年出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记忆》。弗洛伊德把这个故事当作是梦进行研究的,分析了其中的无意识含义,以及隐含其中的记忆。他认为,其关键在于列奥纳多婴儿时期同他母亲的关系。其言论在这一点上有些站不住脚,因为他是以与兀鹫的联系为基础来讨论他与母亲的联系(弗洛伊德用的是一个有错误的德语版本,该版本将那只鸟错译成了兀鹫)。这里我们有必要剔除弗洛伊德所作的有关埃及兀鹫符号学方面的研究附录,扔掉其他一些对传记作者来说过于“弗洛伊德式”的东西。但是除此之外保留下来的基本理解——即列奥纳多的这个发生在摇篮中的十分特别的梦或者说是幻想与他对母亲的感情有关联——是从心理分析学上做出的深刻见解,非常有价值。
据弗洛伊德理解,鸢把尾巴放进婴儿的嘴中就是列奥纳多埋藏在内心的对哺乳的记忆:“这个幻想所揭示的正是吸奶的记忆——或者是喂奶的记忆。这是人类最美丽的场景。像很多美术家一样,他要用画笔来描绘。”(这里弗洛伊德指的是列奥纳多15世纪80年代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