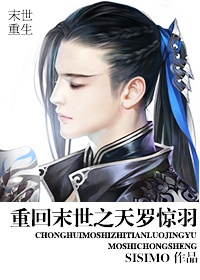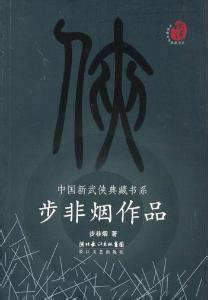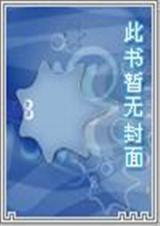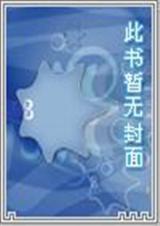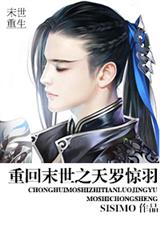天罗山徒-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晚回来,就见一褐衣少女在庭院洒扫,寒凌心道他爹动作神速。
他刚欲上前,少女沉默地过来接过了他手中的书本纸墨。
寒凌有些尴尬,低声道:“你……是我家请的使女?你叫什么名字?”
少女轻轻抬头,容貌周正,双眼盈盈。只是寒凌莫名其妙觉得她脸色并不太对。
“小婢独身一人,自起姓名……少主家,叫奴婢清心便可。”
寒肃站在屋门口,神色难辨。
正文 第二十章 州试
就剩父子二人的时候寒凌悄悄地问他爹道:“别的还好,你不觉得清心脸色有些青,头发也感觉很枯槁么?”
寒肃挥了挥手,浑不在意道:“买来使女是干活的又不是放那好看的,兴许人家以前过的苦日子,在咱家养两天自然就好了。”
在这个家里寒凌一向没什么话语权,听寒肃此言也只好默默放在心里。只是贾明胜这小子长大些后虽然整天一副精神萎靡的样子,与这小使女倒是相处融洽,整日里也不知聚在一堆鼓鼓求求些什么。
很快就到了时日,文武试都在夏末,也自有考虑。文试夏天砚台的墨不会结冰,武试穿的衣服少些方便动作,夏末又天气凉爽,不至于搞得像汗衫老头聚会。
寒肃所处为神州,神州在北疆,但樊阳县却是在神州与青州的交界,划归神州,实际是靠里的。而边塞战事虽频繁,但整个州非常大,樊阳县的居民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见过朝廷的驻边军。大齐的君主和中国历史上的大明朱棣皇帝相似,都采取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思想策略。取“沐浴清化”之意,皇城起名为沐清,位于青州南部。而它虽以城为名,但实际各种规格与大县相同,甚至更高。
所以这样说来,路途相对于流浪者的跨域旅行并不遥远,但整个大齐王朝人口近百亿,管辖范围非常广阔。按照白天行路,三餐和夜晚休息的速度,从樊阳到沐清皇城,至少要在夏中就启程。
柳亭别离,县尉相送。
盛夏温暖的晨曦柔柔地穿花拂柳而过,落在船尾的粼粼波光里。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相互凝望着,越来越远。县尉的翠绿袍服融在身后的一片柳荫中,只有寒肃的蓝布衣还笔挺着,依稀可见。
寒凌转过头来,在船上落座,紧了紧袖口。
船上大多数人都是赶考的学生。孟氏私学除了他自己,士德和孟驹之外,还有四人将要一起前往一州首府金丝城进行州试。整个文武试四年一次,这是男子的。而女子则是七年一次,瑶光和美慧都是明年参加。
士德已经从当年的高胖孩子摇身一变为魁梧白面书生,为此次县里赶考的学子中年岁最长。而孟驹则是比寒凌眉眼清秀些,不似其冷峻,二人站在一处,倒有些兄弟相。
周围人都说孟驹是风流纨绔,但孟氏管教甚严,都只不过是小打小闹。在寒凌看来,最多也就是个富家少爷有些不良习性罢了。然而不得不说其家教将他培养成了一个极适合官场迎来送往的小油条,这或许也就是孟氏一族本来的目的。
而对于少爷周围的这些小伙伴,人们也有不同的评价。孟倪被视作小尾巴,而寒凌则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天才儿童,只是性格有些冷淡阴沉,让人觉得虽然这孩子待人接物脸上带着笑但这笑如春风,只从面上拂过。一时间体贴温暖人心,其实笑未达眼底。
尽管如此,依旧有很多人环绕在这名叫寒凌的孩子身旁,只为了那一点点未曾被察觉的虚伪的温柔――――这是孟驹的原话,甚至包括夫子。
在寒凌看来,夫子状似关心,实则也是利用。孟氏一向在外姓下功夫颇重,外姓和依附的寒门之间有所竞争。在老夫子看来,年少无知之时美慧和他建立的友谊无疑是牵制与缓和的绝佳契机。因此寒凌一开始对这老人满含心机的栽培只能说怀着一种相互利用的态度。随着时间推移,夫子竟也被他感染,有些许真意,寒凌也便半真半假待他。
沿发源于山脉的璐江顺流而北,正好将众生由樊阳带至华天,这一路风帆片片,楼船座座,来往繁忙。一众少年在江上是又吃又喝,眼花缭乱,好不快活。
待至华天府,寒凌首先就和孟驹去拜见了州牧。当年的干瘦老人如今依旧没什么变化,连衣服都是那天同一件。
州牧在官衙后堂接待了二人,寒凌此时按规矩跟在孟驹之后。
后堂布置一看就是武人的风格,陈设清雅却能从细节上嗅出一股子刀光剑影的味儿来。一张晶木几,刻的是出征图;一对白瓷杯,画的是名将美人。
州牧又拿了一个杯子为三人各斟一杯茶,雾气缭绕。孟驹上前一步道:“小子拜见州牧大人,战功赫赫,久闻英名,今日得见。”
老者微微耷拉着眼,并不作表态,只说不敢,笑言道少主文武才具,孟氏未来一片光明前景。
寒凌也拱手恭敬道:“大人风华不减当年。”
州牧长眉微动,笑道:“老了,老了。只能看着你们一个个奋勇争先了。”
寒暄几句,交个底儿,州牧又语重心长几句,便就此告别。一来孟驹还没到作代言人的程度,二来这两方实在没什么交集,各有各的一套。
州试前有县试,考得不是才华而是身份,更像是一道门槛。寒凌背靠孟氏,直接免试。而州试中就是世家子弟中佼佼者胜出参加国试。但就算是州试也有空子可钻,各州由中央发题,虽说泄露严惩,但并没有人蠢到说出去。像孟氏这种庞然大物,并不是哪个州牧都可以平辈论交的。
没过几天就是州试。一共五天,第一天和第五天为文试,第三天为武试,每考一天休息一天。
数以万计的考生从大院门口鱼贯而入。州学被临时征用作为考点之一,年年如此。
今天的天色阴沉,半空中一直有一种灰蒙蒙的云气。两个面目严厉的州学夫子就站在门口作为指引。寒凌和另外几人就站在长长的队列当中,周围的学子也是成群结伙交头接耳。
院里还有人指引,分别往不同房间去。一个房间只有十五人,监考甚严。好容易排到了,众人都被分去了不同的房间,这也是安排上有意为之。
长长的走廊里光影斑驳,应考前的学子步履匆匆,向各自考场而去。
寒凌进入自己的七十一考场,正好靠窗坐着,百无聊赖,只好一遍又一遍回忆可能考的经典书目。第一场为经典释义,第二场也就是四天后是为文。
等了许久,众生皆尽落座,考试正式开始。州学夫子分发试卷。
卷子发下来,是长长的一条,寒凌看到题头小小的几个字,心里就是一阵意料之中的“惊喜”。
正文 第二十一章 放榜
当日拜见州牧,有意无意提及过民生方面的问题,相关著名的作品猜也猜得到有哪些。
寒凌当日回去就觉有所深意,便将民生的文章,尤其是前朝华丽风格的那篇《安民策》重看了一遍,还参考了许多名家对其的批注。
大齐王朝的文试第一场并不像中国古代的科考那么变态,往往考的是著名篇章,而且背诵的内容也不长,甚至忘了也可以自由发挥……当然,这种实力的人也不用指望自己瞎写能有什么好文采。
而文试放榜极快,日以继夜的阅卷,十天之后的早上由州牧公布名单。过了的就去参加皇城的宫试,没过的就可以各回各家几年之后不服再战。
“民生以稼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是勤可以免饥寒也。”
卷子上只有这短短一句,实则原文是一个小段,在《安民策》中间转承部分,由说明转议论的地方。那么大张纸,除了这几个蝇头小字儿,其他全是白的,看的寒凌就脑袋大。
他定了定神,心中剽窃,不,是参考各位大神之后,已经有了大概的构思,在眯着眼磨墨之时,又往里加入一些蛮不错的名句……之后闷头奋笔疾书。众生手快的已经下手写了一会,稳重的还在用各种撑下巴挠耳朵捋头发的姿势进行深度思考。
寒凌想了想,由于大齐王朝经典释义类文章并没有固定样子,所以他就采用了已知的中国古代八股文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这种看上去漂亮,读上去有条理的格式。
他写道:
“……天下之患无常处也……君也垂裳而治,贻协和风动之休;民也画象而理,成击壤从欲之俗……底成古今所未有之功,乾坤开而再辟,日月涤而重朗。盖以实心行实政,因此实政致弘勋……”
太阳快要爬上中天,他的一篇已近尾声。涂改甚少,字迹甚好。
他停下歇了会儿,张望张望四周,发现自己已是写得极快的,速度要排在前三。
寒凌落笔,刷刷点点写完最后几个议论抒情的字眼,长吁一口气,不由暗想其实孟老夫子平时说自己理论不行还真是不大对,前世孔孟老庄墨韩孙,个个金句百出,哪一个拿出来不惊世骇俗?只是用一句少一句,自己记得也不多,都得攒到关键时刻。
瘸腿的在这方面可以补上,只可惜这里不流行诗,否则诗仙一首一出,恐怕吃喝从此不愁……或许他当个推手让诗时兴起来?不好办……不好办……
横竖无事,他的思绪就开始浪了。
要是穿个历史,当个大官儿还不错,他却是来到这样一个古怪之地,倒不如借着官身搞点发明创造或是经商,倒也能名利双收……有太阳,就意味着化石燃料都会有,尤其是煤,他就见过相似之物……只不过一些特殊的物质,真是不好找,这的人或许都不知道把它们叫成什么鬼样子……
“叮当……叮当……”前方监考官手中的摇铃响了,惊醒了白日梦中的寒凌,他直起身来,在周围一群如释重负的人中大大地伸了个懒腰,一摇三晃起来,折好卷子交卷离场,自回旅店。
而四天后的为文,占得分少些,大约四成,问的是个老套的政治立场问题,寒凌当然是怎么正常怎么来,又剽窃了点名句好让文章首尾亮眼些,第二场也就那么飞快过去。
写作文嘛,就像学生时代的考试,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哭天抹泪答不完的,他耸耸肩,无视了身后绝望的大叫,去寻找小伙伴们吃饭喝酒唱k……不,错了,没得k唱……醉生梦死的十天就这么过去了,这几人都很有信心,因为孟氏私学几乎就是除皇宫外当时教育的最高水准。
按规矩,放榜的那天,你既可以挤到州牧那去听唱名,也可以待在事先填好的驻地等待小吏按名次往下通知,他们也不管人在不在,在旅馆门前喊完就走。经过商议,大家一致决定在旅馆等。
与他们一样的人有不少,大清早大堂就坐了一半人,全是年纪轻轻的学子。众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都在高声交谈。
他们这一伙儿各自落座,寒凌边喝茶边想,这儿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