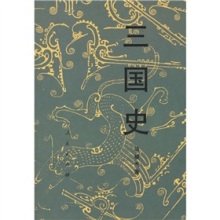武侠.历史-第8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扳指,想吃肉了罢?”
扳指一只手托着爷爷手里沉甸甸的篮子底,一只手死死攥着那只破损的鼻烟壶,点点头,又摇摇头:
“扳指想呢,勿过,肉是爷靠手艺挣的呢,爷啊,日后扳指有了铜钿,好买交关寸金糖、松子糕孝敬爷呢。”
水昌伯呵呵笑了:
“你啊,你有这份孝心爷就知足了,爷老了,这些东西,吃不得了。”
他忽地咳了两声,叹了口气:
“要说好吃,三十年前,常州府那个参爷送我的两盒枣泥饼,那味道真是……”
没过多久,扳指就尝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寸金糖、松子糕。
“我家佐领大人劳烦王师父再做一百支好箭,这是酬金,先付足了。”
水昌伯眯着昏花老眼,瞥一眼桌上的十贯足钱:
“这回也只要七天就够了,不过,你家老爷怎么自己不来?”
那来人眼珠瞪得溜圆:
“王师父,您还没听说么?洋鬼子已占了宁波府、慈溪县,我家大人前日就奉了将令,抬炮上了东城外的金鸡岭呢。?
………【(四)】………
大炮,刚刚铸成的三千斤大铜炮,果然已被抬上了城东廿五里外金鸡岭。23Us.com驻防兵,绿营兵,团练,也正一队队从西门开进来,又打东门开出去。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五百里火急的报马,昨夜遭西洋鬼子已到哉吴淞口,府台老爷吩咐哉,今朝夜厢起,我伲衙役也要分班上城守铺呢!”在衙门里当皂役的阿大,一壁厢收拾铺盖,一壁厢言之凿凿地对家人和邻居们说道。
洋鬼子,西洋鬼子,在这城里是从没看见过的。
“西洋鬼子,我伲白相过,伊有火梭子,一日一夜织的布,我伲乡下巧媳妇要没日没夜织一个月哉!伊还有火轮船,上水跑海比风好快交关……”城西,航船十二家那些专跑日本国长崎码头的伙计们,吐着唾沫,绘声绘色地这样说着。
“嗤,西洋鬼子,我伲白相过,伊长得两条毛茸茸长腿,倒没得膝盖骨头,没奈何弄些布条条包包哉,勿要讲交兵打仗,走旱路腿都勿好打弯,侬好怕伊做啥伲?伊又好吃大黄,一日没得大黄就没得性命……”城北,五番考不上举人,只得靠往来广州贩南货为业的白七相公,撇着鼠须,不屑一顾地这样说着。
谁知道呢?他们说的这些,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
对也好,不对也罢,菩萨保佑,最好让这些该死的洋鬼子远远避开,不要打这城里过。水昌伯、续竹巷的老少爷们,以及这座城里或穷或富的所有人,这些日子里,心里都这样默默地祷祝着。
可洋人终于还是来了,据说,他们不信菩萨的。
那一天,天刚蒙蒙亮,金鸡岭上的大炮就轰地发出一声巨响,惊醒了城中每一个人。紧接着,枪炮声乒乒乓乓响作一片,再不肯平息下来。不到一袋烟的功夫,这乒乒乓乓的枪炮声,就从城东廿五里的金鸡岭,直响到东门外,又响到东门里。
城里的百姓登时乱作一团,有哭的,有慌的,有寻死的,更多的当然是想跑的。可是,四座城门,早已被府台大人下令,封了个严严实实。
于是这些走不出四门的老百姓只好没头苍蝇般在城里乱躲乱撞,胆小的闭门念佛,胆大的,便眼睁睁看着那些红头发蓝眼睛,穿红衣服打裹腿的西洋鬼子,端着枪,拉着炮,从东门一路冲到西门,然后轰轰几炮便轰开那百十条汉子推了许久也推不开的城门,一阵风似地又向西开远了。
当最后一个洋鬼子火红的身影,终于在惊魂甫定、鼓足勇气登上西门城楼看动静的巡丁视野中消逝的时候,同样火红的太阳,才刚刚爬上了金鸡岭山巅宝塔的塔尖。
洋鬼子来了,又很快走了,似乎也并没有马上就再回来的意思。
据说,在这一个半时辰里,驻防兵、绿营兵、团练们的鸟枪、抬枪、大炮,从城东廿五里的金鸡岭,一路丢到护城河的吊桥上,那岭上炮台,新铸的三千斤大铜炮,也早化成了一堆废铜。
据说,在这一个半时辰里,城里城外,连官吏、兵丁、衙役带百姓,共死了四百四十三口,其中跳河、跳井、上吊寻死的老百姓便有一百七十七口,多是大姑娘小媳妇和大户人家的女眷。
佟佐领中了十几枪,死在金鸡岭的炮台上,死的时候脸向着东方,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弓,那张长五尺八寸,阔二尺二寸的双角缠丝大弓。
阿大死在东城城楼上,天灵盖被弹片削去了半边,一双眼睛大睁着,怎么也不肯闭上。
知府大人也捐躯了,跳的府衙后院里的荷花池,尽管洋鬼子根本没打府衙前经过,尽管据长随们说,知府大人自始至终,连一个洋鬼子的面也没照过。
洋鬼子们也并没有从续竹巷里穿过,只有巷口第一家的王家老铺,被几颗从大街上飞来的流弹,在那块剥落了金字的老招牌上,又穿了三五个不大不小的窟窿。
看到的人都说,当子弹从匾上穿过的时间,水昌伯仍稳稳当当地坐在铺子里拾掇一张旧弓,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看到的人都说,阿大出殡时,阿大媳妇和扳指哭得泪人似的,水昌伯却呆呆的,没有掉一滴眼泪。
这些日子,城里到处是孝服,到处是哭声。阿大媳妇也见天搂着儿子,哭得死一阵活一阵的。
水昌伯却不哭,只是常常一个人望着招牌上的弹孔发呆。
没过多久,城里的孝服依旧,哭声却一天天地稀少了。水昌伯却还是老样子,常常一个人呆呆地望着招牌上的弹孔。
不过,自打洋鬼子来过之后,续竹王家老铺的生意却突然一下子好了起来,好了很多。
古怪的是,这些主顾大多是生面孔,而且全是要买弓的。
更古怪的是,这些大多穿着长衫或绸褂的主顾们,似乎并十分不在乎弓的好坏,也不十分在乎花多少铜钱。
“侬晓得勿?官军跟西洋鬼子开仗,自家死了交关,好歹才打死伊一个,我伲看见死鬼胸口,插了根泡桐尾巴的箭杆……”
终于有一天,参爷府的中军喝到醉醺醺时,把这个惊天的大秘密,嚷嚷得整个续竹巷,不,整个城都知道了。
不过,这个大秘密随着新府台的走马上任,很快就算不得什么秘密了。
因为从官绅到百姓,人人都看得见,城隍庙里的土地爷退了位,天子爷的圣旨,把为国捐躯的佟佐领封了做本城的新城隍。
那张长五尺八寸,阔二尺二寸的双角缠丝大弓,和那一壶镞长二寸九分,杆长四尺一寸的桐羽长箭,也披红挂彩的,被高供在佟佐领、不、佟城隍老爷新塑的金身前。
“听讲勿?城隍老爷托梦,勿管土鬼洋鬼,大鬼小鬼,有得续竹王家老铺格弓箭在此,百无禁忌哉!侬好也好歹也好,好歹买伊张弓,挂在堂屋里厢好得辟邪哉……”
“胡说,子不语力乱怪神,敬鬼神而远之,你们这些不学愚民,实在荒唐!实在荒唐!不过呢,这弓箭乃我堂堂中华上国世代相传的宝物,射术更为我圣人所传六艺之一,宝弓一开,洋人立毙,大挫彼西洋番鬼奇巧淫技之气焰,大长我圣人之邦之声威,吾辈谁非圣人门徒,自当祭而拜之,鼓而呼之,大书而特书之……”
于是买弓的人家越来越多了,有拿来挂在灶王爷边上辟邪的,有买去挂在门神边上镇鬼的,还有娶媳妇的人家,迎花轿时让新郎拈弓搭箭,说要崩崩煞神的。
望着每日忙不完的活计,和花不完的铜钱银两,阿大媳妇那哭得红肿的眼睛,也仿佛多了一丝神采;扳指那整日哭丧着的小脸,也仿佛多了一点生气。
水昌伯却显得并不怎么高兴,甚至似乎还有些惶恐:
“不不,不是我,不是我,那弓是聂五做的,我只做了箭……”
他整日反反复复地唠叨着,对着铺里铺外、挤得满满腾腾的主顾们。可是,没有人听他的,人家只要弓,只要他做的弓。
后来,他终于不再唠叨了。
阿大断七那天,阿大媳妇扯着扳指跪在公公面前,当着满堂吃豆腐饭的远亲近邻们:
“阿爷,侬行行好,把侬手艺传把侬孙孙好勿?”
扳指的两腮还挂着眼泪,人却跪得笔直:跟爷学手艺,他一直想的,求了好多次了,爷肯,阿娘不肯。
可这一回,直到散席,爷一直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坐着,没说肯,也没说不肯。
当巡抚大人亲书的《金鸡岭大捷碑》,在金鸡岭宝塔边高高竖起的那一天,城里府学的老爷们前呼后拥地领着一班从人,吹吹打打地来到续竹巷,春风满面地给那块破旧的老招牌披红挂彩,好一番折腾热闹。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夕阳下的石板路上,扳指穿着一身孝,挤在那些捧着饭碗看热闹的乡邻中间,一面好奇地望着那些爬在梯子上、正忙碌着给自家铺子那块斑驳的老招牌重刷金漆的府学老爷从人们,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随口哼着那支不知听爷爷哼了多少遍的老调儿。
水昌伯还是那样呆呆地站在铺子前,呆呆地望着自家招牌上,那即将被新漆补上的几个弹孔。
招牌底下,府学老爷们自顾自地议论着,感慨着,谈笑着,浑不去理会就站在自己身边、那系着犊鼻裙的老铺主人,仿佛这铺子是谁的,这铺子主人究竟如何,统统于他们毫不相干一样。
………【(五)】………
“这鬼天,怕又要下雨了罢!”
小孙篾匠漠然地望了望阴沉沉的天,和晌午后显得有些空旷、有些冷落的石板路,轻轻摇了摇头。wWw.23uS.coM
铺子里冷冷清清的,只有他自己。
自打城隍庙里换了城隍,王家老铺的招牌上了新漆,原本热闹的孙家蔑坊就一直这样冷清着,冷清得连门外的幌子都懒得多飘一会儿,冷清得两个小徒弟隔三差五就找由头回乡下家里去,连拿不拿的着月规铜钿都似乎不怎么在乎了。
小孙篾匠自己倒还是和往常一样地勤快,有生意没生意,手里总放不下篾匠活计。
虽说是这样罢,可天气不好、徒弟不在的时候,他也免不了望望天,望望地,望望巷口,幽幽地叹上那么一口气:
“唉,侬讲,格算啥事体哉?”
铺外那面懒洋洋的幌子,没来由地,忽然轻轻掀了一下。
一老,一少,不知何时闪了进来,迎着小孙篾匠愕然的目光:
“格……水昌伯……扳指……侬、侬、侬晌午吃好勿?”
水昌伯似乎比小孙篾匠还要局促,还要尴尬,他搓着布满皱纹的双手,看几眼墙上挂的编好的笼屉,又瞥一眼小孙篾匠手里编了一半的活计,动了动嘴唇,似乎想说些什么,却终于一个字也没吐出口来。
“格物事,我伲叫伊茶壶窼,热茶壶放进伊,交关好热两个时辰哉……格、水昌伯,侬吃茶勿……”
水昌伯的老脸忽地红了,仿佛早已饮下小孙篾匠手里新沏的热茶。
他一把拽过扳指:
“来,跪下,给孙师父磕头。”
扳指正好奇地摆弄着地上那个编了一半的茶壶窼,忽听此言,一下便呆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