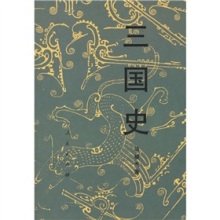����.��ʷ-��8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褼��ˣ������֣���ͳ�ȫ�Ұգ���һ�����Ϸ��µĸ������㣬�ѵó���ôһ���Ӻú���ֵ�ˣ�����Ҳֵ�ˡ���
�����������������Ҵ��������ֶ��һ�����ƣ�����ɽʯ����������ǰ�У�
�����������������ϣ��н����ˣ���
��������ʯͷ����ͷ������ʯͷ��û��û�˵�ʯͷ��
��������������������ȳ��գ���Ȼ������
�����������Ÿ����ڵء�����Ѫ�۵ĸ����ң��������������䣬����Ҳ������Щ�����ˡ�
����������������
����������������ͬʱ�����һ���ǵ���һֻ�۵ĸ����ң���һ�����뷢���ŵĸ��溲��
�����������˶�ĬȻ�ˣ��̴�����ݶ��ϣ��Ѿ��˲���ֵ�벻ֵ�������˲������벻���ˣ�ֻ���ϣ�ֻ���ϡ�
����������Ω����������������������ǧ�˸��ϣ������溲����һ�٣�����ι��ʣ�����G�����Ǵ���ǧ�˴Ӵ�·������ǣ��һ����ެ���䣬��������ʱ�����Ӧ���������ǿھ���˭Ҳ�����նӣ���
����������Ω���ͱ������������������Ҫ�ߣ�������һ��µ����������
������������ģ����ӻ�û���أ��ϣ�һ���ϣ���
��������ʯͷ����ͷ������ʯͷ��û��û�˵�ʯͷ��
��������Ϧ�����εذ����һ�����ͣ�����������ʯ����ɽ�ۡ�ɽ����ɽ�ȡ�
������������ɽ��ȵ���죬��Ϧ�������ǽ�ʿ�ǵ�Ѫ��
�����������溲������ǰ����ʪ��ģ����˫�ۣ���������ǰ��һȺ�ˣ�һȺ�ϱ۲�֫����ͷ�ö�ĺ��ӡ�
�����������Ż�Ω���������Һ������������ģ������˰ٶ��ˣ���ǧ�����ʻ����������Զû����ʯ���Ļƻ��
���������ƾ��վ�����û�ܶ����ǿھ���û���������ò������Ƶ�ʯ������ס�Ÿ���
�����������ǿھ����ǿھ�ˮ��ɬ�������ʣ�ȴ��ʯ������������ϵ�Ŀ�ˮ����ȴҲ�ѱ�����ʯ�飬��˫����ʿ������ʬ�壬����ʵʵ�������һƬƽ�ء�
�������������Ҳ�������ǿھ��£�������ɱ����ʣ�µ�һֻ�ۣ�Ҳֻ��������һ���ϱۡ�ÿһ�����Ż������˶�˵��������ǵ�һ�����ʯ����Ҳ�ǵ�һ�����Ͼ����Ĵ����ˡ�
������������ӻƻ�ֱ�����������溲��û�п���˵������һ�䶼û�С�
������������ӻƻ�ֱ��������ɽ�µ���Ӫ����ɽ�ϵ�ʯ���ǣ���������˷���һֱ��û��ͣЪ��
�����������ڣ�һ�ж��ž������������ౣ���������������
�����������𣡻𣡡�
��������һ�̶�������Ӫը���������Ż������ž���͵�����ײ������
������������ެ��͵Ӫ����
����������Ӣ�V���Žţ�ֻ��һ�����£�����������һͷײ�����溲�����ʣ�
��������������ұ�һ�ܣ������ǡ�����
�����������溲���¶��𣬶���������
�������������ʣ��������ެ������ʣ���٣���ʲô���Ҿ�������������ǽ����
����������Ӣ�Vһ��ţ�ͦ��������⡣
�������������ɱѽ���������һ���ˣ���
��������ԶԶ�ģ�³����������
�����������溲����Ц�ˣ������������ͱ�ʱ�����������˵�Ļ�����
�����������飡��
���������ʽǺ�Ȼһ�������溲��æ��ס������
��������ȴ�������͵�һ��˺�ѣ�һ����ެ�����ص�ˤ�˽����������������飬����ʮ��֧���������Ǹ����ڵأ��������ϵķ�����Թ��ȴ�ܿ����������С�
�����������溲�������𣬻���������⡣
�������������ˣ������ˣ�һ�ж������ˡ�
���������ڽ���£�������ϴ���ƣ����Ц�⣬�ƺ��������˵Щʲô��
�����������𣡻𣡡�
��������ʯ�����ϳ���Ļ�⣬ӳ������������ʣ�ӳ����ʯ��ɽ�ϵĻ�ѩ��
�����������ܻ���У����������ĺ���������ެ���Ӹ߿��ĸ�����
������������ެ�˵���裬�����ں�����ӥ�����Լ����������������ԡ�����Ω����Ȼ����
�����������Ƶĺ��죬���ڲ�����ʯ����ͷ��
������������ʵҲ����νʲô��ͷ�ˣ������ˣ����˷��棬������ʲôҲû��������������
������������G��Ħ����ˣ��Ȼ���ѡ�
����������������������д��ʲô������ι����ƺ����²�������������Ų�֪���������һ����ެ�䵶��
������������ҡҡͷ��̾�˿�����
���������������ң���д������д�������������վ���д�ģ��վ���ġ���
��������ɽ�۵Ļ�ѩ���ɣ���ֻ��ӥ����Х���ӹ�ͷ����
����������Ω�����㡢���ܲ��ܴӷ��������ެ������ʬ�Ǽ���������롭����
����������Ω����������ʣ��������ˣ���ެ�˲�����Щ���������ⰿ��IJ�ӥ��������ǵĻ��Ǵ��ؼ��磬�������õġ���
����������ʮ�ģ���������
�����������������ˣ��ຣ�����죬���������ر��硣����С˵�����㡣����
������������ɽͷ�IJб����ѱ���������һ����˪����Զ����ʯ������һ�µij�ԫ�ϣ����Ƶĺ��죬�������������չ�����
����������Ȼ����һ�У����Ե��ϵ��������ǿ������еģ��������ܿ����ģ������ⵯ��С���ϵ��﹡����ֻ��տ��տ�����ຣˮ��������̺�������ǵص���Ⱥ�ˡ�
�����������죬�ջ�ļ��ڣ���������ˢˢ�ͺ�ˮ�δ�ģ�Ω������Զ��������Щ�⼹���������ģ������ٵĹ��ºʹ�˵�գ�
������������˵�������ʯ���ǵ�ʱ�������ެ�������İ��ˣ���
������������ô������Ϊ�������ǣ����ǿ��ǡ�����˵��ɽ�ı���������ת���Ϳѵı������˺ü�ǧ�˰գ���
�����������ˣ�����Щ��������������ү�����ˣ�����үһ���ˣ���Щ�����ӵ���ү��Ҳ�Ͷ��ܸ����ˡ���
�����������ɲ���ô�������۾ʹ��˲�֪�����أ�������˵����ν���������죬�������ۣ����Ÿ�ͷ�������ڴ�Ӫ������һȦ��һȦ�����ǿޣ�����Ц��������ҹ��û��ð�����������������
����������������Ҳ��˵���������쵽���ۺ�һֱû�д���Ҳһֱû��Ц�ء���
�������������ô������˵������ү��Ҳ������ô���˰�����
�����������ͣ���������У���������������������࣬����Ϊ����������ô�������ˣ������˵Ļ����������ּ�������α�ǰ����ӵ������������ų�����IJ�˵������������ױ���ÿ��һ������գ�������ף�ɡ�����ۣ�һ·�Ǹ����簡������
����������ž����
������������ж�Ȼը����һ����ޣ���������Ļ�ͷӲ�������˻�ȥ��һ������ͷ��������æ����ȥ��ʰ��ǰ�Ǽ�¢����ˡ�
�����������ꡫ������
���������۽ǵ�������ټ�������˫�ش��Ƥѥ�������ǵĵ����ִ�������
�����������ҵ���ѽ�����ۻ��ˣ���������������ӣ���
��������һ����������Ʋһ����Ȧ����������ѵ��촽��
����������Ҫ���ܰ��ǿ���ɱ�˳��⣬�ö���������Ԫ��������ʱ�����Ǵ�������ԳԵ�Ѫ����������Ȧ�һͷͷ��ī�ڣ�����ѩ�ķ������ߺ������ҹ���
������������Ҳ���룡��һ����������ش����������������������㶫��������ʱ���������磬������˵������ӣ���Ҳ�룬�ߣ���
���������������䲻м��ƲƲ�죺������ˣ��ޣ�����һ�����õĸ����۳���ˣ���ʯ����ʱ����û����һ��ָͷ�����ڵ�������������Щ�������϶����磬ʲô���������
����������С���㣬���ǰ����������㲻����ô����
��������˵�����������˶�������˵�ˣ������������ͷ��������������С��ֻĬĬ�Ӷ��������������
���������������Ω��������������̾���ģ���˵������ֹ����������˫ţ����Щ��Ȼ�ӿ��ϣ�����ƾ����ʹ���DZ���ʮһ�����鳣�Ҳ������Ӫ����׳��׳������������Ŀ��ˡ�
����������������������Խ�ˣ�ȴ���������ɶ�������ʮΧ����Ŀ��ף�����������Ϥ����Ӫ�б���������������Ӫ�ĺ����ϧ����ֻ�Ǹ����ϵĸ����۳���ѡ�
����������Щ�����������ˣ��ܲ����ˡ�
���������������ڱ��˿��������������Ҳû�����ɲ����˵ġ���Ȼ���˴�Ӫ֮���һֱ�Բ�������Ȼ��ʯ����ʱ������һ��Ҳû�Ź������۹�����ʱ����ȴҲ�õ���ѫ��ת���ʹͣ������������٣����������ս����ij��ӡ�������٣������ﰵ��߷߲����˺ܾá�
��������������IJ����ˣ�ͬ���ĸ�������ǹ�ϲ����Ȱο������ֻ�ǵ���ͷ�����Ƶ�һ�����ԡ�����������ͣ�ˣ�����Ļ���Ƕ������ˣ�������۳�Уξȴ�����������������Ե�����Щ�����ͷͷ����Ҷ�˵������һ���������٣������Ƿdz��dz��ر�ļ����ˡ�
���������������Dz����ˡ�
��������������������⣬ů������������ļ����ϣ�������������Ȼ����һ˿��������������
����������ͻȻ������Դ������װ�����һ�����Ѳ�Զ���ļ����������˸�����æ�����ز�Զ�˼�����
��������������Ծ���¸��Ż�����ʮһ��Ĵ������ú������磬ֻƬ�̹���Ȧ��Ω��һ�ž������һƬ�Ӱ��ȴ�벻������ԭ������׳˶�����Ρ�������ƽ���������λ�����ӵ��۵���������з��ԣ��˿�ȴҲ�̲�ס���������
����������Ω���������ƣ�������������ɫȴ�����������ع��ţ��������㿴���ң��ҿ����㣬��Ȼ˭Ҳ���Ҵչ�ȥ��������
����������һ���˴���վ�˺þã�����̾�˿���������������鳣��ܵ��Ը���������ȡ������ƺ�«��һ�ߺȣ�һ�����������ɽ��ȥ��
����������֪���˶�ã���Ω������Ѭ�졢�����˲�����ں�ɽһ����ڣ�ϣ�һ����žƣ�һ�治ס��������������ʲô��
��������������������ͬ������褵ģ�һϮ���ۣ�������Ѫ���ܵĶϱۡ�
����������������ΪʲôҪ����ΪʲôҪ��ʱ���ҡ�����
����������ֻ����ڷ�ڣ�Ͽվþ��̻��ţ�ȴ�ƺ�Ҳ������������˵Щʲô�����������ų����ã��ĺ��ķ�Զ�ˡ�
����������������ΪʲôҪ����ΪʲôҪ��ʱ���ҡ�����
����������Ω����������������ţ�����������˯���ˡ�
��������������������
��������һ�������IJҺ����һ�㣬��������Ω�����ξ���
�������������������ʲô���������μ���ʯ���ǣ�
��������������������ѽ��������
����������һ��������ķ���
����������Ω��һ���飬�Ƶ�ʱ���˴�룬���ڵ������������������������Һ��ĵط�ƴ����ȥ��
���������ʲŻ�������������ﲻ�ϵij��ϣ��˿�����һƬ��ҡ����ص���Ѫ�����ص���ͷ�����ʬ������������˵�Ÿոշ�����һ�С�
����������Ȧ�İ����ǽ�ϣ����Ÿ��������䣬Ѫ��ģ�������壬أ�Խ�һ����һ��ij鴤�ţ���Զ����ʮ������ެ��������Х�ţ�Ц���ţ�������ͷ�����ұ��ķ�����է����Ω�����������ɵض���һ㶡�
����������Ω��������ϣ��������Ѵ������ˡ�
����������ެ��������һӵ���ϣ���Ω�������ӭ��ս�����ϣ�����һ����һ����ެ���Һ��ź�ɳ�ȥ���ɶ�Զ����������Ҳ����һ����������Ϊ���ء�
����������Ω��ɱ������һ���ֽУ�����ץ��һ����ެ�������ְ����������������ƹ�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