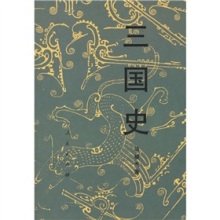武侠.历史-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段矜刚才背著大家早已哭了几场,此刻却拼命忍住眼泪,想安慰慕容垂几句,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姐姐一定不想看见你这样……”
她的脸突然红了。
“我……我不行了,孩子、孩子和你都需要人照顾,我的、我的妹妹年纪虽小,却、却很懂事,你们、你们一定要……”
这是段氏的遗言。
不但如此,她还挣扎著坐起,看著自己的丈夫和妹妹在窗前交拜,喝令著一双儿子跪在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段矜面前叫了“母亲”,才安祥地合上了双眼。
慕容垂不知在想什麽,神情忽阴忽晴。
慕容令已换上了孝服,快步近前:
“吴王府属官们都来吊唁,父王要不要……”
慕容垂点点头,擦干眼泪,大步走了出去。
“……母亲、母亲也先去歇一歇吧。”
段矜陡地回头,一双泪眼中,望见慕容令悲伤而真诚的脸庞。
悲伤是最沈重的,葬礼却是最简略的,当然,这是对於吴王这样的大人物而言。
不是不想隆重,只不过段氏自出诏狱,病死家中,总不便大事铺张,引来後患。
来吊唁朝官和诸王都吃了闭门羹,他们知道,吴王是不想连累同僚和族人。
送葬归来,紧接著便是慕容垂和段矜的婚礼。
虽然鲜卑人家没有汉人那麽多规矩,可是丧中成婚,总是有些别扭。然而,这也是故去的段氏的遗命。
这样的婚礼当然不会有多少喜气,多少笑声;当然更不便邀请什麽宾客。因此坐中除了两家在邺城的血亲,就只有兰家兄弟和高泰这些心腹部属了,因为反正不事宾朋,所以家人们索性连大门都关得紧紧的。
高泰是赞礼,他尽量做出一脸喜气,努力履行赞礼应该履行的一应程式。
虽然气氛压抑了些,但望著这一对新人,厅上的每个人都默默地想:“以後一定会很好的。”
新人已经交拜了站起,高泰清了清嗓子,正要喊出最後一句台词:“礼成!”
“圣旨下!”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鼓乐声。
高泰本能地跳了出去:那传诏的声音,是他久系诏狱的哥哥高弼的。
圣旨是两道,一道是吊唁故吴王妃段氏的,巫蛊等事,一概未提;
另一道,却是天子赐婚,以可足浑後妹长安君,嫁与吴王为妃。
厅中人众登时一片骚然,高泰几乎气得昏过去:
“哥哥,你怎麽能……”
高弼苦笑一声:
“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可是此次祸事这麽大,天子如此行事,至少……”
他没有说下去,也没必要说下去,大家都明白,巫蛊的麻烦,不是那麽容易了结的。
再说,也来不及说下去了,天街遥遥,大队仪仗鼓乐而来,引得路人纷纷围观。
队伍中人个个披红挂彩,腰间却系著白带,对对宫仪,簇拥著一乘花车,队伍前二人肩舆,端坐一个满面病容的朝服老者,却是久不出府的东海王慕容恪。他的身後,或马或车,尽是王公高官。
围观的百姓看见东海王,纷纷欢呼起来:“东海王无恙!”
吴王紧前几步,拉住东海王的手:“兄长,我……”
慕容恪轻轻叹了口气:
“贤弟莫怪我,愚兄主此婚,非是与贤弟和故去的弟妹为难,实在是为社稷惜吴王啊。若贤弟不能释可足浑之憾,解主公之疑,终不得为大用,贤弟纵不为身惜,愚兄怎能不为燕国江山爱惜贤良啊!”
慕容垂默然,左右官宦属员,无不暗暗点头,却又个个忍不住回头,看著厅里兀自婚装、背门而立的段矜,眼中都有不忍之色。
段矜突然转过身,慢慢地走到花车前,慢慢地跪下:
“贱妾段氏,恭迎新人下车。”
皇帝赐婚,当然不同。王府上下里外,都披上一层喜色。
可家人们的神色都有些黯然,慕容令不待礼成,便打马出城,说是射猎去了;慕容宝虽然还坐著,却只是默无一言,只管吃喝;段纭更是早早地被姐姐段矜拉去了自己的房间。
慕容垂也想跟去,但被段矜拦住了:
“姐姐和我都为的是殿下的前程……”她似乎想笑给慕容垂看,却终究哭了出来,但她一边哭,一边还是坚决地把慕容垂推开,推向正房的方向。
长安君正坐在正房中出神。她是不是正在想著那一天,自己怯生生地去皇宫听罪,却得到这样的喜讯时,那又喜又羞的情景?
房中很素净,刚才她已经吩咐陪嫁的侍女们把屋里的花红都去掉了,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性情中人,有些感情,不会这麽快淡去的。
门开了,慕容垂慢慢走了进来。
长安君心中澎湃,却强自按捺,只微动了一下身子。
可是半晌,慕容垂并没有过来,偷眼望去,他正伏几拄臂,凝神看书,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更没有向床头的她望上哪怕一眼。
她心中不免有些气恼,又有些发酸:她刚才已经大致听说了段家姐妹的事情。
她忽地站起来,却又很快坐了下去。
“只要他不出去,也不让我出去,就……”想到这里,她居然笑出声来。
这一夜,他们谁也没有走出屋门。
数月後,吴王进号为使持节,却被远派辽东,都督龙城诸军事,兼摄平州刺史。
………【第一部 吴王 第四章 职责】………
建康,东府城。(看小说到顶点。。)
荀羡病了,病得很重。
几万大军北上,却只回来数千人。虽然按照门阀旧例,对他的惩戒不过贬号罚俸而已,但孤儿寡母,怨泪盈天,却令他日夜不安,终於一病不起,被从下邳抬回了京城。
朱序和沈劲坐在榻边,心情起伏,却不知说什麽是好。
荀羡强打精神,吃力地张口道:
“淮北、淮北军情……”
“郗昙大人已命诸葛攸率两万出石门入河渚,进展甚速。”朱序赶紧言道。
“慕容垂,慕容垂……”说起这个名字,荀羡的脸色不觉变得更加惨淡。
“燕主已调慕容垂往辽东,山东一境,已无此人旗号。”
荀羡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伴著更多的疲色。
朱序和沈劲对望一眼,一齐轻声告退。
“此次北中郎将用兵,胜算几何?”朱序回头看著沈劲。朱雀航边,野花正开得茂盛。
“诸葛攸为人谨懦,行军不敢离河道30里,逆水讨贼,转饷千里,实在胜算不大。”沈劲苦笑著,用甘蔗敲打著马鞍。“再说,那位北中郎将郗昙大人门望倒是高的,可是比起荀羡大人,也不过半斤八两罢了。”
朱序默然点头,长叹了一声:“桓征西表请大举出兵,分取河南山东,所派督军,却是西中郎将。”
西中郎将谢万,是个傲慢自高、不娴军务的高门书生,他的哥哥,自己的好友谢安曾经亲自写信给桓温和谢万,劝阻这项任命,却根本无人理会。
桓温自从征秦败归後,举措乖张不测,他隐隐觉得,朝中会有什麽大事发生。
太阳渐渐地西沈,燕子归巢,炊烟嫋嫋,不知何处的女孩儿,伊呀唱起俚歌来。
沈劲入神地听著,不觉叹道:“如此河山,忍教胡人饮马至此!”
朱序是北人,不明唱词,只见沈劲神色凛然,不觉心头一热:
“在下明日便赴襄阳任上,只是将军此番立功最多,却不得升赏,不免……”望著沈劲一点点低下的头,朱序再也说不下去了:家门,又是家门所累,朝廷用人看家门,不用人也看家门,唉!
“燕主猜忌慕容垂,让他远赴辽东,中原燕兵,并无大将主持,东边我军虽不能取胜,却还不至有丧土之虞,倒是西边的秦人,狼子野心,志不在小,大人守襄阳,倒要小心了。”沈劲望著木棚上的旌旗,口中喃喃不止。
朱序点了点头:“刘牢之受命招募北方流亡,在京口建北府军,将军何不……”
“多谢,不过不必了,在下倒要让朝廷里的大人们看看,吴下男儿,也自有破虏杀敌的好汉!”沈劲使劲把甘蔗抛入河中,砰地一声,激起一大朵水花来。
平州。吴王官署後宅。
慕容垂坐在正中,面色凝重。王妃长安君、侧妃段矜,神色都很不自然。
慕容德刚刚从京城回来,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
皇帝慕容俊无缘无故地杀了段家的嗣子段勤,段勤之弟段思单骑南投晋国。
“主上因为兄长的先妃是段家的人,所以心中疑忌,恰在此时,王兄的谢罪表又到了京中。”
慕容垂并没有写什麽谢罪表,这个表是长安君代写的。
慕容垂恼怒地望了长安君一眼。长安君满脸委屈,却说不出话来。
“姐姐是好意,她也是怕此事连累了大王……”
“唉!”慕容垂长叹一声,脸色温和了一些:“主上和皇後对我猜忌很深,刚刚任命了王子泓为济北王,王子冲为中山王,各拥重兵屯於平州境上以防我生变,这样一表递上去,不是此地无银,欲盖弥彰吗!”
长安君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段矜急忙上去帮著劝慰,为她擦眼泪,慕容垂自觉说得重了,也安慰道:
“不妨事不妨事,东海王已扣下此表,天子并没有看见;再说南寇又已入境,此时还不至於对我如何。”
慕容德一旁呆著,正有些尴尬,不料慕容垂却转向他问道:
“晋军败了多久了?”
慕容德敬服地望了兄长一眼:
“3天。诸葛攸沿鸿沟北进,日行不过50里,我军从容集步骑5万,在东阿大破晋军,诸葛攸仅以身免。”
“不过据报晋人已命西中郎将谢万为大都督,北中郎将郗昙为副都督,起兵十余万,分两路直逼河南、山东,我太傅上庸王慕容评已亲临前敌督师,并加权都督中外诸军事。”
长安君此时已止住抽泣,忍不住道:“太傅哪里是打仗的材料!这下……”
慕容垂淡然一笑:“好在谢万更不是材料,而且此人为人轻狂自负,既不娴兵务,又不接将卒,恐怕难以如意指挥调遣部将;郗昙的山东军久败於我,行军必定谨慎持重,两路晋军一疾一缓,无法救应,太傅虽是常才,必能各个击破。我们就等著听捷报吧!”他突然笑了:“捷报一来,主上心情必定大好,对我的事情也就不会深究了,呵呵。”
半月之後。
吴王官署後园,侍婢雉儿正绘声绘色地向长安君叙述著听来的新闻:
“大王真是料事如神,晋兵果然大败而归,而且败得实在邪门。”
原来谢万以高门自居,疏於军务,却又对众将十分傲慢,曾经在出兵前招集众将开会,却不知该如何部属军务,只用如意遍指众将说道:“大家都是劲卒”,手下将领个个泱泱不服。谢安闻知此事,唯恐谢万有失,便携带厚礼,亲自逐一拜访众将,谦辞厚托了一番。
等到进兵时,西路谢万长驱直入,东路郗昙却持重缓行,果如慕容垂所料。燕军趁机以主力正面阻击谢万,以长乐太守傅颜率轻骑切断东西两路晋军的联系,郗昙闻知,借口生病,退往彭城,而谢万闻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