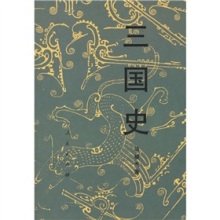武侠.历史-第19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明主求贤兮,却不知吾……”
那中年人仿佛没看见听见他们的争议一般,继续唱着他那首莫名其妙的歌。大约他们所争执的什么云中雪,什么天父诗,对于那人而言,其晦涩难解的程度,决不亚于这两个天兵天将之听歌罢?
两个天兵天将又一头雾水地听了几句,虽还是没听懂,但终于断定这歌和《天父诗》没什么关系,既没什么关系,自然一定是“妖魔习气”了。
两人目光相对,都点了点头,一齐举起了刀枪:
“兀那匪人,竟敢唱邪歌,论天法当诛!”
他们嘴上嚷得凶恶,手里却着实慢得很,忠王有令,不得妄杀,这等怪人,吓唬跑了也便交得差使了。
那中年人却似被吓得傻了,张着嘴僵在木卡前,一动也不动,一声也不吭。
翔子有些不耐烦起来,对老耿不住使着眼色,老耿明白,这是让他朝天放一枪,把这呆子惊走。
“子弹可没几粒,放一粒少一粒,不好补上呢。”老耿满心不情愿,却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只好磨磨蹭蹭抬起枪口,作一个开枪的姿势:“那呆子,再不走远些,本长毛就要、就要朝天开枪了!”
那人如梦方觉地“唔唔”了两声,却哪里挪得动脚步?
老耿暗叹口气,枪口指天,便待要扣动扳机。
“休得开枪!”
一个声音从城楼上直飘到卡前,应声跑来的,是个锦袍花帽的大汉。翔子和老耿急忙丢下刀枪跪下:
“钻天侯大人万福。”
这钻天侯一面搀起两人,一面埋怨着:
“你二人也着实不解事,天王诏旨,说淫戏邪歌不让唱不让看,好戏正歌,自然是让唱让看的么?你们不晓得?前日在虎丘讲道理,认天安陆大人(11)自己便扮了行头,上台唱了出《孙庞斗智》呢!”
翔子和老耿面面相觑:这好戏正歌的说法从没听说过,似乎未必很妥当,但陆大人粉墨登场的事情却半点不假,那天看见的弟兄没有三千,也有两千的。
钻天侯见二人不语,登时满面堆笑,伸出宽厚的双掌,使劲拍了拍二人肩头,然后大步流星,抢到那中年汉子面前:
“这位先生歌唱得甚好,虽然兄弟我一句也没听明白,却是咿咿呀呀,受用得紧,先生如果愿意,就请进兄弟的馆里,早晚三顿,有鱼有肉,只需给馆内弟兄们唱唱曲,说说书,也便行了。”
中年人的神态似平复了大半,捏着手中白纸扇,目不转瞬地望着钻天侯,仿佛没听懂他的话一般。
钻天侯挠了半天头皮,陡地仿佛想明白了什么似地,放声大笑起来:
“哦,对,对,先生千祈莫忧,兄弟这馆子是文馆子,只管公文案牍,不管打仗的,先生若怕辛苦,文书也不用抄,担儿也不用挑,只需唱曲说书,随众吃饭便了。”
那中年人下意识退了半步,急忙连连摆手:
“不不,多谢将军厚爱,学生兴之所至,胡乱唱了几句,以致打搅诸位雅兴,着实过意不去,学生家中尚有老母病妻,无人照料,这便告辞,这便告辞!”
他合扇拱手,一转身,逃也般飞奔而去。
“大人,这人唱的什么?”
中年人的背影已消逝无踪,翔子和老耿一面嚼着送来的常州麻饼,一面含含糊糊地问道。
钻天侯怅然若失地摇了摇头:
“唉,不管唱的什么,终究比听天父诗有意思啊!可惜啊,没福份!不说了不说了,你二人好生把守,我奉了将令,这便要出城,去四乡八镇贴招贤榜去呢。”
注释:
1、挥子:太平军对纸条的称呼,这里是通行证一类的东西;
2、长龙红粉本是太平军对抬枪和火药的称呼,但后期被有鸦片烟瘾的官兵用于暗指烟枪和鸦片;
3、太平军以黄红为尊贵之色,黄又尊于红;
4、壬子八年即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
5、云中雪是天国对大刀的代称,过云中雪意即斩首;
6、太平天国避讳“上”字(只许称呼上帝用),所以用“尚”字代;
7、太平军官员对官兵和百姓做公开集会宣传,称为“讲道理”;
8、天父天兄是天国对上帝和耶稣的称呼;
9、贞人:天国对官员妻子的称呼;
10、《天父诗》是一本书,收录了杨秀清、萧朝贵假冒天父天兄所作诗句,和洪秀全本人的一些诗,大多数是用来教训后宫妻妾女官的;
11、认天安是陆顺德,当时封殿后军大佐将认天安,后来升殿前南破忾军主将认天义、来王,曾攻克绍兴,攻打上海,天京陷后从侍王李世贤转战福建、广东,1865年夏在广东镇平被叛徒出卖,执送广州处死;他确曾登台唱戏,因此被人误会为戏班子演员出身,实则他是广西藤县富户子弟,忠王年少时还做过他们家的长工;
………【(十)】………
“你说,你说,这算怎么回事情?”
王利宾一手掐腰,一手指着自家大门上粘着的,那张簇新的门牌,满脸愤怒的颜色。(看小说到顶点。。)
那门牌是黄纸做的,盖着通红的大印,笔迹颇为拙劣,一笔一划倒看得真切:黄利宾,年卅七岁,妻林大妹。
那老仆佝偻着脊背,一叠声叫着屈:
“勿是小人办勿来事体,长毛大人下钧令,勿让姓王姓洪哉,老爷勿相信,好去寻曹地保、勿是、寻曹师帅问清爽好勿?”
“是啊是啊王、不,黄年兄,”他们的西邻,一个留着短须的秀才闻声露出了半拉脑袋:“小弟听说,不但寻常百姓,便是洪天王自家亲戚姓王的,也改了姓黄(1),这改朝换代,避讳难免,想当年大名鼎鼎的蒯彻,不也给改了蒯通么?”
王利宾闷立了半晌,眼珠一转,忽地反怒为喜:
“是我的不是了,老顾,你办得好,办得很好!”
被叫做老顾的老仆被主人这一冷一热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问又不敢问:
“老爷勿见怪便好,小人弄晌午去哉。”
“哎,我说老顾,你这老爷老爷的也得改改,要不还得闯祸,”短须秀才追着老仆的驼背喊了一嗓子,又回头对王利宾苦笑道:“早上有长毛骑马敲锣,一路喊过去,说只有什么上帝才是爷,其他人如果叫爷,一概要杀头的,这杀头是真是吓唬不好说,可能不惹事,咱还是不惹事来得好,您说是不是?”
王利宾正待答话,却听得虹桥方向,一片锣声响亮:
“钻天侯顾大人奉了文将帅钧令(2),来此张榜招贤,本乡俊杰速来看榜投效!”
“这长毛办事,终是有些……小弟且去瞧个热闹,王年兄,你去也不去?”
王利宾微微一笑:
“热闹无好看,年兄自便,小弟便不掺和了。”
人群喧嚣着往虹桥而去,塘河边一下安静下来。王利宾立在门前,深吸一口气,默默凝望着被檐角墙头割裂的天空。
四月天,孩儿脸,天色水色,都显得有些阴晴莫测的样子。
“真天命太平天国苏福省文将帅李,为奉旨招贤出力报销事,”
入更后的虹桥一片静寂,偶尔远远传来几声犬吠,回荡在塘河拍打堤岸的水声之间。王利宾笼着盏小灯笼,凑在茶亭柱上白天新粘的招贤榜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读着:
“……照得江南文物之地,久罹胡寇剥削之惨,财赋为之侵渔,士女为之屈辱,谁非上帝子孙,不思抱怨?皆是农桑之客,能奋刀兵!遁隐潜藏,富贵岂求诸胡口;黜革责降,铨叙尽操夫满洲。喁喁相冤,好诫文狱之祸;嗷嗷相顾,皆俟脱颖之记。缘我主天王肇基粤左,定鼎金陵,旌旄所指,王道底平,本职奉旨专阃,镇抚一方,诛满夷之僭窃,整中夏之纲常,怜英雄以事胡为羞,甘屈志于泉石;豪杰因勤王不遇,犹隐逸于蓬门。未获吐气扬眉,不能攀龙附凤……这几句写得倒也过得去,只是忒也罗嗦了。”
许是夜半河边,春寒料峭,王利宾觉得有些冷,一面跳着脚,一面挪动灯笼,跳过长长的铺垫,迳去寻最左边的榜文条款:
“……今列规条,凡民间有才力可任使者,来衙禀明录用:一、通晓天文星象算学者;一、习知地理山川形势扼塞者;一、善书札笔记者;一、民间豪杰能习拳棒武艺骑射者;一、医士之能内外眼小儿妇科者……”
王利宾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逐字把这招贤条款看了好几遍,眼神渐渐有些凝滞了。
一阵风吹过,灯笼忽地熄了,他怔了怔,从身上摸出包洋火来,手颤了几颤,却终于没有再燃起那灯笼。
二更天了罢,月亮在乌云中时隐时现,又一阵清风吹彻,王利宾浑身冰冷,不由地猛打一个寒噤,手中洋火灯笼,险些都掉进了塘河里。
“唉,我还是回去睡,睡醒了到镇外塘河边钓鱼好了。”
清风把他寂寥的叹息,吹散在塘河廊街之际。
注释:
1、天王认为只有自己和所封各王才能称王,不但把历代帝王都贬称“侯、相”,而且不许人姓王,姓王者需要改姓汪或者黄,就连自己的表哥王盛均也不得不改叫黄盛均。除了自己的亲戚,其他姓洪的也要改,如名将洪容海就改姓童;
2、天国后期主管一省民事的官员叫做“文将帅”,但往往有名无实,需要听地位高得多的驻军将领指挥。当时已有苏福省,却以降将李文炳作为“江南省文将帅”,这里迳改作苏福省文将帅
………【(十一)】………
蚕豆花开了,塘河边的柳荫,也一天天浓密起来。WEnXUeMi。CoM
这些日子,四乡八镇的斯文人颇变得有些不那么斯文起来,虽说长毛没有如早先流民唱传的那样,要来个“焚书坑儒”,但他们却整天惴惴不安地样子,经史子集懒得多看,就连平素最喜欢的雅集唱答,也是半点提不起精神。
“着佃交粮(1),呸,这是那个不学之辈,失心疯子,给毛公(2)出得馊点子?贷田交租,取租办赋,这可是自古相沿的铁规矩,现在这样,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体统大约还是小事,毕竟这着佃交粮不是把绅士们的地径直拿了去分给佃户,说到底,佃户还是佃户,东家还是东家,佃东相见,这安还是照请,头也还是照磕的,只是送来的租米,却眼见着糠麸越来越多,米谷越来越少,甚或分不清到底是马料还是租谷了。
照往常的规矩,佃户不听招呼,只许两寸名帖,塞给胥吏保甲,便什么都办妥的;无如如今改朝换代,乡官如曹师帅一干人一夜见骤富乍贵,捞了个盆满钵盈,志得意满之余,自懒得帮这些背时货色寻别人晦气,对绅士们的软磨硬扛一概搪塞,搪塞不过去了,免不得抹下面皮,吼上这么一嗓子:
“侬勿要闹好勿?长毛大人有令,万事皆有天排定,不遵天法,论理当过云中雪哉,过云中雪懂勿?就是砍脑壳哉!”
绅士们还是很怕“过云中雪”的,于是不免缩脖回家,关起门来腹诽一番。
然而腹诽虽然解闷,却实在不能解惑,更不能解饿,于是有些绅士开始牵挂起“我大清皇